教辅市场:“黄冈神话”不再?
作者:吴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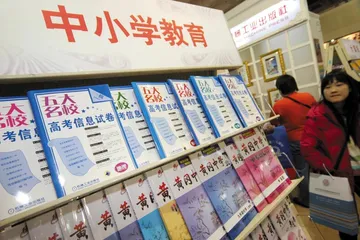
( 1月12日,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展示的中小学生教辅书 )
“南有王后雄”
45岁的王后雄这几天正忙着学生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这位从黄冈县一中“起家”的化学老师,如今已是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的教授。王后雄经常带着硕士生到武汉的一些重点高中实习,“那些中学生们还拿着当年我出的教辅书,围上来让我签名”,中学校长也会把王后雄留下做一场教学方面的讲座。由于教学质量的出众,全国中学流行着“北海淀、南黄冈”的说法,而在教辅书的名师里边,则有“北有任志鸿,南有王后雄”的讲究。
出第一本书的时候,王后雄在黄冈县一中担任了四五年的化学老师,“我从十八九岁开始教书,沉淀了一些教学经验后,写了一本《初等化学教育系统分析》”,这是一本教育类的专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末,教辅类书籍几乎全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几家指定的出版社统一发行,还鲜有人看到教辅市场的商机。后来王后雄接连写了《高中化学竞赛基础教程》和《初中化学竞赛名师指导》,“这两本书一年的销量在一二十万本,而当时一般竞赛书的销量只有一两万本”。
有了几次愉快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酝酿出一套中学教辅材料时,找到了王后雄。1990年,28岁的王后雄在黄冈县一中拿着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家境贫穷,千字16元的稿酬已经让他很满足。华师出版社编辑部组织了一批各个学科的特级教师,而还是普通教师的王后雄一人负责化学方面初中一册和高中三册的编写。早期出版社的教辅书籍策划编写都相当用心,经过一年多筹划后上市的《重难点手册》,很快在市场上热卖。
王后雄的个人名声,随着《初中重难点手册》和《高中重难点手册》的单册60万销量闻名。同一套教辅书里边,语文、数学、外语是所有文理科学生必考科目,它们的销量从两三万册到十几万册不等,而理科生才需要的化学重难点手册,销量却遥遥领先。在这本被众多考生奉为经典的化学书里边,附上了王后雄的一张小照片,简单的个人介绍里边,王后雄和“黄冈名师”的称谓一起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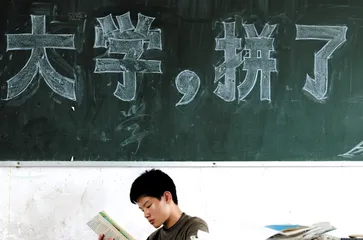 ( 黑板上的话就是高中生们的心境 )
( 黑板上的话就是高中生们的心境 )
在1999年之前,全国高考实行3+2模式,强调知识点的覆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时间成为高考的代名词,高考竞争异常激烈。从1984年起,教育部规定,高考按照基本教材命题,此后每年高考还会由国家考试中心下发高考大纲。这种命题原则决定了高考成为一种有规律可循的考试,它有一定的考试技巧和解题模式,学生只要记住教材的基本知识,通过题海战术就可以得高分。押题成为神奇的传说,一些根据高考规律和教学经验而编写的教辅图书开始出现在市场上。
黄冈中学因众多高考状元和奥赛冠军而闻名全国,黄冈在高考前的内部试题也被外边看得相当神秘。王后雄说,“黄冈模式”的特点是夯实基础,对高考大纲的研究相当细化。“高考大纲的考点是很抽象的,比如化学中的‘氧化还原反应’,数学的‘二次函数’。黄冈的学校会把每个考点的‘子考点’列出来,细化到这些子考点会遇到怎样的题型。”黄冈的内部试卷里曾出现的一些题目,当年高考就“碰”到了,这更是让黄冈中学给外界留下了“猜题很准”的印象。王后雄独创的“中学化学学习目标控制教学法”得到认可,他的学生3年内获15个全国和湖北省中学化学竞赛大奖,64人夺得黄冈地区化学竞赛冠军,王后雄的“神奇”也在中学传开了。学生间流行的说法是,“只要有了《化学重难点手册》,化学考试永远不败”。王后雄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后,曾在2003年和2004年做过抽样调查,“被调查的三四百名学生里,85%的学生中学时用过我的教辅书”。从1991年出版到现在,王后雄的《化学重难点手册》8次更新再版,销量超过1000万册,“盗版书估计有正版书的10倍之多”。
在黄冈高中教辅被全国考生热捧的年代,王后雄一年会接到1000多所中学的感谢信,“中学教师都有升学压力,那些写感谢信的老师说,用了我的书之后化学成为优势学科”。一心围着考生转的家长也把王后雄当做“考试神仙”来拜,“有一个新疆的石油开采工人,我的书在新疆那边脱销了,他儿子急着要买。这个工人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武汉,又打听到我在黄冈的家里,半夜找到我家敲开门,我也很感动”。在教辅热销的推动下,王后雄也成为中国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北省第九届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教育专家,破格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成为化学教育领域的名师。
黄冈招牌的含金量
在王后雄与黄冈中学的名声互相推动后,“其他出版社也突然意识到,黄冈蕴藏了一批没有被开发的老师”。王后雄当时是黄冈地区下属的黄冈一中的老师,黄冈中学与下属9个县的一中,比如浠水、罗田、红安、麻城、蕲春等,教学质量都相当好,“黄冈教育这个金字招牌不仅仅指黄冈中学,它是一个集团作战,出了一批闻名全国的特级教师”。
黄冈市教委研究室的特级教师刘汉文编写的《初中数学竞赛》相当畅销,《黄冈兵法》、《黄冈密卷》也一时畅行全国的教辅市场。武汉新知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周健记得,书商们早期与老师联系出书时,“不少老师是‘书痴’,视金钱如粪土,可是一旦意识到教辅里的商机,也就发现了这‘粪土’里暗含黄金”。教辅市场吸引出版社和书商的最大优势是——市场巨大,“对全国学生们都有普适性”。
“黄冈”二字很快成为书商的摇钱树。这个在大别山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出现的教育盛况,在教辅市场被迅速批量生产,成为外界试图复制黄冈神话的载体。在头几年,对于黄冈地区的一个高级或特级教师而言,每月工资收入两三千元,如果参与教辅编写,一年下来的外快有四五万元。刚刚接触出版界的教师们还没有什么版税概念,为了一次性拿到可靠的稿费,大多按照千字稿费取酬。学校因为怕影响教学质量,对老师编书原则上是不提倡。老师可以用个人名义,但不得打着黄冈中学的“旗号”。但市场上黄冈品牌的书籍基本都是冲着黄冈中学的,封面上就只有“黄冈”两字,而在扉页或封底上注明编者是黄冈中学教师,让学校也无可奈何。黄冈中学曾经对编过书的老师做过统计,牵头编书者不超过10个人,参加过编撰工作的不超过60人。多数是打着黄冈旗号的非法出版物充斥街头。
湖北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经理胡新分析,对于普通图书来说,每本书针对的群体不一样,“我们出版社的图书A卖得好,图书B可能卖得不好,因为大家不会完全冲着出版社去买书”。可是只要教辅贴上了“黄冈”的标签,“就成了全国考生抓住的一剂猛药,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考生特别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黄冈教辅’就被赋予了改变考生命运的希望”。“黄冈教辅”也出现了“从下到上”的特点,越是在县乡等基层学校,需求量越大。
黄冈中学正式与出版社签订出书合同,已经是2002年的事情了。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雷雨(化名)向记者回忆到,早在2000年10月出版社就派人去黄冈高中沟通,被学校拒绝了。2001年出版社找到黄冈高中的几位老师,出了一套《金牌黄冈》的教辅,销量不错,一直到2002年黄冈中学当时的校长终于同意合作,“说服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上冒充黄冈中学的书太多了,学校还不如正式出一套教辅来正本清源”。湖南人民出版社给了他们很优惠的条件,包括在黄冈中学百年校庆时为其出书,以及出版有关老师的学术论文集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冈中学》丛书两个系列为《黄冈中学·高中分科导学》、《黄冈中学·高考名师点击》。在2002年西安的二渠道图书定销会上,此书刚刚出现一个封面,内容还没有做出来,雷雨记得各地经销商在展台前拿着现金来“砸”,“很多不认识的书商来抢购,当时光是现金就收了几十万元”。这套丛书为了表现自己是被授予了知识产权的,封面特意印上与校门一样的字迹“黄冈中学”。
而这时的教辅市场,已经因为1999年的高考改革出现了分化。“1999年是教辅书市场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高考是实行3+2考试,在此之后则是3+X,考试的命题意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教辅书市场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黄冈兵法》丛书主创人员周益新是黄冈中学地理高级教师,他曾提到《黄冈兵法》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是因为瞄准了考试改革的方向。“在1999年之前,全国影响最大的高考辅导类书籍是龙门书局出版的《三点一册》。因为那时实行的3+2高考模式强调的是知识点的覆盖率。而1999年实行3+X模式后,考试注重测试各学科基础的、核心的、可再生的知识内容,以及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新科技的发明应用,最重要的是,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雷雨在推广《黄冈中学》系列丛书时,发现2002年这套书已经有些“生不逢时”了。2000年前是教辅市场的黄金年代,200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希望借着“黄冈中学官方授权”来夺取这块市场时,发现教辅市场“已经非常混乱了”。而“黄冈教辅”的最大特点是“难”,以雷雨的估计,长沙市只有15%的顶尖学校可以适应“黄冈教辅”的难度,学校里边又只有部分尖子生可以做得出“黄冈教辅”的题目,“普通学校的很多教师也做不出黄高的难题,这就决定了它的市场份额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黄冈中学也不满意这次合作的结果,认为收益太小。
教辅市场下坡路
《黄冈中学》教辅书从2002年推向市场,经历了一个热销期后,迅速衰败,成为教辅市场发展曲线的代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雷雨发现,正规出版社做教辅,属于“市场大,但是利润低、‘保质期’短”。教辅的退货量与报废量相当大,“秋季教辅的热卖期在五六月,学生放暑假后还有一部分销量,一到秋季开学,教辅就卖不出去了”。而每年高考的考试大纲又有变动,“所以如果在五六月卖不出去的教辅,这一年用处都不大,最后只能把它们当废纸卖掉”。
正规出版社受到更大的冲击,来自若干合法或非法的二渠道书商。二渠道书商出书成本低,销售折扣“低到内行人都难以相信”。湖北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经理胡新说,有没有市场对于教辅尤其重要。而要推销教辅,“每个人发家的渠道不一样”。一种书商“走上层路线”,在某地教育部门或学校有关系,“只要攻关了主管图书采购的校长或者教务主任,他们一句话,几百上千本书就卖出去了”。另一种完全走“下层路线”,甚至有书商专门雇用农民工,“扛着一袋袋的书去跑学校,给校长或老师谈回扣”。当一些不正规的书商发现“守法的成本比违法还高时,教辅市场就更乱了”。
按照胡新的说法,图书市场的门槛非常低。早期一个想做教辅的书商,只用花8000元从正规出版社购买到一个书号,然后将市面上已有的教辅抄写拼凑,“比如每本书抄30%,作者的名字都是编出来的,谁来告他们侵犯知识产权?”有的书商找几个老师来拼凑内容,有些找大学生到网上摘抄,给他们的稿费相当少,“应景的教辅,说穿了就是题海战术,拼凑起来非常简单”。于是一个书商投入5万元就能印教辅,利润却相当高,“正规出版社都是五五折扣,非法书商三五折或二五折卖给经销商,让人难以置信”。一旦非法出版物被发现,不过是没收焚毁,“没有太大打击力”。而这些非法教辅,绝大多数都打上了“黄冈中学”、“黄冈名师”的噱头。有人估计,2006年中国“教辅”有400亿元到600亿元的市场,全国570家出版社有530家出版教辅,民营的策划和发行机构涉及此领域的占60%。
在大的政策面上,国家高考制度的一再改革,也使得教辅市场很难“一书遍天下”。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决定实施分省命题,到2006年全国有16个省实施了分省命题的考试方式,中国高考开始了统一招生、分省命题的时代。分省命题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各省市之间发展不平衡、考试群体差异很大的问题。除此之外,2004年开始试行的新课程改革使高中前所未有地采用了学分制和选修课,分省命题也是新课标的要求。
教辅图书市场也发生了变化,新教辅品种的推出在理性收缩,靠行政手段征订发行教辅图书的方式日渐式微,不少的教辅出版社和民营教辅出版商减少新教辅品种的出版。一度火爆的“学王一拖三”、“黄冈密卷”、“一课三练”等等相继退出了图书市场。区域性教辅市场需求在逐步扩大。现在各地自主选择教材版本,加之各省都力推本省的地方教材和配套教辅用书,使得教辅图书一个版本全国通用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黄冈教辅”从上世纪90年代的火爆,到如今乏人问津,雷雨说,“现在出版教辅就像冬天里卖冰棒,买卖不好做啊”。 神话高考教辅黄冈兵法王后雄湖南人民出版社黄冈市场黄冈中学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