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作者:苌苌
( 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奠定了他作为欧洲核心作家的地位 )
欧洲有那么几个——由于当地某位优秀作家的作用——让你一看到名字就和“忧郁”这种情绪产生通感的城市,比如巴黎,比如布拉格,比如圣彼得堡,如今,又多了一个伊斯坦布尔。在自传《伊斯坦布尔》中,帕慕克费心尽力,向读者传达他在住了一辈子的城市所感受到的忧伤。一座城市拥有一位能够读写她灵魂的作家是多么幸运。去年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中谈到为什么写作,其中就说到:“我写作是因为我想让其他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我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而在这个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叶子的4月,终于可以读到此书的中文简体版,想到它的作者,正因本国民族主义者的疯狂威胁,迫不得已选择流亡美国,不免又添了一层忧伤。
2003年,帕慕克在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中奠定了他作为欧洲核心作家的地位后,出版了他的自传。书的畅销说明它好看,文字优美,图文并茂,可以满足你对一个成功作家的窥私欲和对他成长之路的好奇。他谈到那个孕育了他的因修建土耳其铁路而暴富但又日渐衰落的家族,有族长般威严的祖母、和哥哥之间为了争宠的战争、性意识的启蒙,多少成为他的《新人生》蓝本的美丽而伤感的初恋;还有黑白照片中长得好像40年代影星艾娃·嘉德纳的优雅却抑郁的母亲、喜欢文艺有些风流的父亲,他的理想在1972年的冬天如何从当画家变为当作家(10年后他在30岁的时候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不过书结束于他确定理想的时刻)。帕慕克用绘画者一般的目光,刻画了美丽如画且神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写到那场几乎烧毁了岸边所有帕夏留下来的木制别墅的大火。不过你也许更喜欢看到像宫崎骏动画片场面的效果——半夜巨大的苏联军舰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像浮动碉堡一样静静地飘过他的窗前。一个好作家是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这本书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回答。但并不仅仅如此,对于厌倦了那种过于自恋的自传的读书人来说,书也是好看的,它是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命运之书,而且敢于正视一个国家文明衰落所带来的精神苦难 。
照片和细密画上的老伊斯坦布尔如此优美,令非本地读者也能感受到她从繁荣滑向衰落的凄凉。有些感觉中国读者应该是心有戚戚的,帕慕克把那种我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从写作技术上讲)的深刻而忧伤的生存体验描述了出来。20世纪初,在我国辛亥革命时候,也正是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之时。在此之前,老大帝国的地位早就随着政权的衰败和因此导致的国家实力和国民素质整体下降而失去了。摆在落后国家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现代化或者灭亡。只能选择现代化,在现代化竞争中占据了优势的西方成为世界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由中心向边缘渗透的悄无声息的文化战争,由此带来了冲突与迷失。在我们国家比较封闭的那段时间,土耳其一直在被西方文化半殖民进程中,一个历史悠久曾经吸引无数东方学家前往的城市逐渐变得孤独与零落。1952年,帕慕克就出生在这种尴尬之中。
“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在书中写道,“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那时的土耳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印记:“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老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和当地的东西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相当于抹去过往。”文化上相应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土耳其曾经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但在帕慕克童年,清真寺是家里的保姆需要找人聊天时才会去的地方,西化的中产家庭中流行模仿西方生活方式,客厅布置得不伦不类好像博物馆一样。帕慕克在这些家庭中看到的是缄默,人人都在公开谈论足球、孩子的好成绩、音乐,但内心里却不断与最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宗教、生命的意义,颤抖而迷茫,痛苦而孤单。
在国家摸索着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的生存状态都处在不稳定状态中,价值观也很朦胧。青年帕慕克颇为“注定在破旧、落魄、平庸、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注定过着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外界注意”而痛苦,并准备慢慢地接受命运。他对西化的矛盾还来自于,本来以为他们拥有的控制权是由于具有现代的西化眼光,但在父亲和伯父的商业失败下,他难堪地看着他们家境被类似家里的厨子和司机们的暴发户超过。“如果教育让我们有资格享有特权和财富,那该如何解释这些虔诚的暴发户?”他自问。当时土耳其西化的中产阶级对军事介入政治的宽容,并不是由于担心左派分子,而是担心哪一天暴发户们联合起来,打着宗教旗号,以西化的生活方式为由消灭他们。但帕慕克没有在军事和政治上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不想“破坏本书隐藏的对称性”。在不断的成长与审视的过程中,帕慕克没有把自己固定为某种形态某个阶层的坚决保护者,避免了狭隘与偏执,唯一可以确认的一条线是,伊斯坦布尔是个非常优雅的城市,而这种优雅的消逝让他非常忧伤,所有细节围绕这条线对称铺开。
 ( 《我的名字叫红》 )
( 《我的名字叫红》 )
直到20 世纪,所有在土耳其之外流传的涉及土耳其的文学作品,都是由西方人写就的,比如梅里美、奈瓦尔、纪德、瓦莱里、戈蒂耶,但都因为不具备“家”的感受,而散发不出那种由内到外的感染力,直到《伊斯坦布尔》出版。帕慕克敏锐地挑选了他们的游记中最智慧的部分,还选用了勒·柯布西耶在《东方游记 》中的素描,以此来讲“西方人的眼光”。讲到福楼拜身染梅毒后在土耳其妓院的遭遇,他说如果萨义德的《东方学》提到这一段,也许就能避免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者拿他的书当武器。还引述不少土耳其作家和当年新闻记者的文章,趣谈中不乏深刻。帕慕克很少到一街之隔的贫民区去,但他用土耳其作家坦皮纳的描述来讲述土耳其的贫民区就好似土耳其在世界的位置。帕慕克提醒我们说,对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东西的真实性,而是形状。对小说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事件的过程,而是安排。对回忆录作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叙述准确与否,而是前后呼应,三个因素都在这本书中有所体现。
帕慕克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伊斯坦布尔,以全人类文明进步的眼光审视自己出生的城市的帕慕克,因为说话不留情面,直指痛处,而惹恼了一些人。去年,他在公开谈论20世纪早期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屠杀后,被国内的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叛国者,生命因此受威胁,不得不远走他乡。然而书中的伊斯坦布尔,远比土耳其旅游局官方网站上璀璨照片中的要迷人,你可以感觉到作者是带着真挚的爱来写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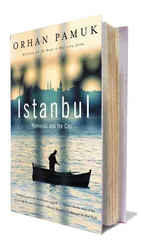 ( 《伊斯坦布尔》 )
( 《伊斯坦布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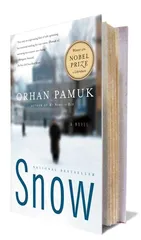 ( 《雪》 ) 读书文学作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旅游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
( 《雪》 ) 读书文学作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旅游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