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读过可以假装读过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52岁的巴黎大学文学教授、心理分析专家皮埃尔·巴亚尔(Pierre Bayard)写了一本书《怎样谈论你没读过的书》,在法国颇为畅销,并迅速被英美国家引进出版。
他身为文学教授,却在书中承认有些文学名著他读了但没有读完,比如德国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些书他只是听别人谈论过,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有些书他读过但是已经忘记它讲了些什么,比如弗洛伊德的《释梦》。还有一些书他一无所知,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有意思的是英国和美国读书界对法国人这种坦然的反应。美国一位文学教授说:“我敢肯定巴亚尔这本书会令大西洋这一边的很多学者感到愤怒,他们不像法兰西民族那样喜欢公开作秀、自命不凡。”《每日电讯报》的书评编辑说,跟英国人谈论你没读过的书是自讨苦吃,“英国人喜欢揭穿作假行为。看到别人失态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见闻广博”。
《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也很不喜欢这本书追求的目标,他在博客中说:“我们英国人不喜欢无所不知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亲近、谦逊,喜欢去酒吧里喝一杯。不会洋洋自得地希望人人都知道他读过但丁的《神曲》——不但读过几乎人人都读过的《地狱篇》,还读过非常乏味的《天堂篇》(因为描写的是天堂,完全缺少《地狱篇》绘声绘色地描写的各种折磨)。我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的是这样的书:如何避免谈论你本不该看却看了的书,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达·芬奇密码》。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不会承认自己读过这些书,但他们中间肯定有人在撒谎。”
巴亚尔试图为自己辩白,他说他的意图是通过挑战文学在法国的展现方式,来帮助人们克服对文化的畏惧。“人们找到我,描述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文化创伤。学生在课堂上被告知要读某本书,然后在表格里详细列出他们的收获。这种直来直去的方法就像是把书供奉起来。我想告诉学生,只对一本书有所了解但没读过并不丢人。连那些最有教养的人也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蒙田记不住他读过的东西,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对萨义德说,他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文核心课程有一个好处,能让哥大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阅读基础,假使他们以后忘记了这些书,至少他们忘掉的也是同样的书。瓦雷里没读过一些作家的书,但照样能够赞美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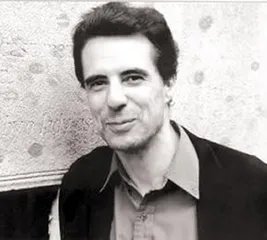
家长和学校要求孩子尽善尽美,但是接受教育并不是要读这本或者那本书,而是知道如何挑书,知道每本书在文化史上的位置。“学生们把文化看成一面高墙,是令人害怕的知识怪物。但是我们这些读起书来废寝忘食的知识分子,知道读一本书的方法很多,你可以略读,可以从头读,却不把它读完,也可以只看目录。你学习和一本书共处。”美国教授有类似的说法:“阅读习惯就像睡眠习惯,因人而异。我喜欢同时读四到五本书。就像赛马,只有一两本书会赢。”
关于怎样谈论你没读过的书,巴亚尔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技巧:不要谈论细节。把理性放在一边,让你的潜意识表达你跟书的私人关系。换言之,不要被自己的无知吓住,不要担心会穿帮。如何评论一本你没读过的书:“把它放在你面前,闭上眼睛尽力想象会让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写你自己的想法。”如何跟作者讨论他的书:“坚持只讨论一般化的东西,含糊其辞,说你是多么喜欢那本书。”
其实很多学生都擅长对他们没看过的书发表意见。书的封面、书评、有关作者的八卦,甚至正在进行的谈话都能提供素材,帮他们装成很懂的样子。
《时代》周刊开玩笑说:“对我们来说,也许只要能在跟人谈话时相机说出一些漂亮的花絮就足够了:1904年6月16日(那是乔伊斯迷们的布鲁姆日,或者说,是《尤里西斯》所记述的那一天);玛德琳的香味(勾起小说家普鲁斯特记忆的蛋糕),或者乔治·艾略特(记住,她是个女的)。” 读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