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县铅中毒调查:一个失去信任的城市
作者:王恺(文 / 王恺)

媒体纷纷报道的334个铅中毒的徽县孩子中,血铅含量最高的是14个月大的白旭,达619微克/升,属于重度中毒。只有一点大的他显然不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母亲说他脾气不好,“爱咬人”,到现在还不会走路,但是此刻病床上的他正对人咧着嘴笑,7岁的牙掉了就长不起来的姐姐在旁边逗他——他们俩是300多名病孩子中的幸运儿,因为只有最早来医院检测的,血铅含量超过350微克/升的11个孩子留在了西京医院儿科病房治疗,白旭和他姐姐都在其中——他们微笑的画面让人难以忍受。
父亲白志强是“案发源头”冶炼厂的临时工,只在那里工作了9个月,医生说铅有80%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的,而村庄里的饮食显然受了铅污染,他却茫然地一直向所有人解释:“我回家都是先洗手的。”更焦虑的是,14个月的白旭已经被查出了心脏病,需要花几万元动手术,这病究竟和血铅含量过高有没有关系,谁都说不准确,即使是他最信任的西京医院的儿科大夫也含糊其辞,他急着要和县政府交涉。
成胜权,第四军医大学直属西京医院儿科副主任,在整个徽县铅中毒事件中,他的位置非常重要。是他,首先确定了徽县水阳乡的大量孩子的中毒来自于旁边的冶炼厂,也是他,在数个专家被乡民赶走后,前两天从西安到甘肃徽县的水阳乡里做了讲座——他是村民们唯一相信的专家。“他是西安来的大夫,不会骗我们。”徽县的1000多个听讲座的人这么说。
具有专业人士外表的他摇头苦笑自己的处境:“当时也就是偶然确诊的,可能是我们军队医院的传统,比较认真吧。”今年3月,水田乡的孩子周浩被电击中手臂后来西京医院治疗,在调查以往病史的时候,家长说5岁的孩子总是肚子疼,结果查到了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血铅含量,属于中度中毒,“一般说起来是城市的孩子会高一些,因为汽车尾气排放的缘故”。可是农村非常稀少,当了解到离他们家只有几百米有家铅锌冶炼厂的时候,“基本上就确诊了”。
周浩治疗结束回家,陆续有甘肃口音的村民挤满了西京医院的儿科急诊室,全部是徽县的水阳乡农民。可是,成胜权和整个医院的医生开始不愿意继续触及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说:医院限于能力已经不能再接收孩子了,成人铅中毒的情况他们不了解。新来的孩子们不得不转到别的医院检测。谁都不知道他们受到了何种压力。

整个事件最让人惊奇之处,在于这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从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建厂以来,就开始污染周围的环境,11年来当地的农民一直在为庄稼坚持向工厂索取微小的赔偿,直到当大批孩子中毒的消息传出来后,这一可怕的工厂才全国闻名。耳熟能详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能准确地解释这家工厂一直挺立的原因,当地的权力结构也许是更好的解释,作为甘肃省排名第48位的洛坝集团企业,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的大老板的奔驰车要明显好过徽县领导们的汽车,这也许是他们真实地位的象征。
在这样的权力布局下,徽县的铅中毒者开始不再相信当地的一切有关人士。他们寻找外地的医院治疗,他们驱逐县里派来的专家,他们制止县政府开的拍卖工厂财产的会议,整个徽县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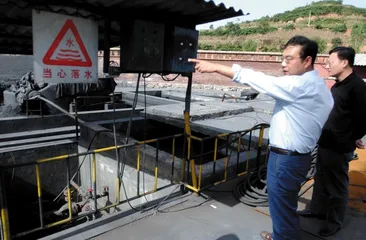
漫长的10年铅中毒:从黄豆到孩子
大多数村民,是在8月初从贴在村里各处的复印文件上知道,和他们近在咫尺的冶炼厂可能造成了村民的集体铅中毒。一共是5张纸,一张是11个村民在西京医院的化验报告,另外4张全是从一本儿童医学书里复印下来的儿童铅中毒的标准和症状。细节看不明白,但是中毒后智力下降和身高不足的症状,正好和家家户户的孩子对上号,当时张贴者显然还顾不上搜集大人铅中毒的材料,“刚看见的时候,人人心里都咣当一声响”。当时还正为黄豆中毒找工厂交涉未果的村民们,心里更像着火一样。
后来召集了许多农民去厂里要个说法的张鹏伟说:“还真不知道是谁贴的。”村民们不愿意说出谁最先干的这件事,但是他们都能详尽地述说整个过程,周浩的诊断结果引发了11个村民的自费检测,而11个村民检测回来后,人人都愤怒地发现血铅含量超过了国家标准。孩子们一般为300以上,属于中度中毒。
这11个人中的张军民是在外边做小生意的人,每年回村里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能免于遭殃。他的愤怒也就格外真实:“看了调查组报告才知道,冶炼厂用的是早被禁止的炼铅工艺。”
县城的新华书店里只有两本关于儿童的医学书,被买了回来,然后被广为复印、张贴。8月初,刚刚为黄豆受污染和冶炼厂交涉完的村民陷于集体性的恐惧中。张鹏伟记得,去西安的村民成批成批的,每天都去十几个人,村里不算富裕,去西安,一个人至少要花300元,所以最先去的全部是带着孩子去的。“家里没有孩子的,还真舍不得去。”那时候,家家晚上议论的,是自己家去不去,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有些家境不好的人家开始借钱前往。
据成胜权介绍,共有877个人来西京医院做了血铅检测,成年人的数字他不清晰,但是334个孩子无一例外,全部超过标准。
1995年,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厂贪图离公路近,建在了离县城2公里的地方,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布局在山里的铅锌矿的边上,而周围的水阳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区域,靠近县城的农民们,比山里的农民更见过世面,但是漫长的10年里,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厂里的毒气能让庄稼中毒,从来不知道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反复闹过,但从来没赢过。
王敞亮是水田乡新寺村的普通农民,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去西安自费检查去了,60多岁的他不肯去,今年8月爆发的孩子铅中毒事件之前,他是少有的曾经去过厂里要求赔偿的农民之一,他家的菜地就在冶炼厂附近,一墙之隔,1995年,冶炼厂刚刚建到这里,他还很嫉妒所谓“厂范围内”的几家人家,那时候,冶炼厂就和这些人家签订了协议,每年补偿他们所有的庄稼损失费1万元,几家均分。而他差一点距离就没能算在其中。“6年前,刚买来半年的牛就走不动了,那时我就开始犯寻思,想这个厂是不是不光对庄稼有毒,对人也有毒,可是我找谁去呢?”
几年前,从北京来工厂的一对技术员夫妻从来不喝村里的水,总是到远处去运水,王敞亮瞅着这对技术员,心里发慌:“为什么他们不喝我们附近的水呢?是不是有毒?”
到了去年,紧挨着厂墙根的他家水井发浑,浇什么死什么。人家都笑话他,做了一辈子庄稼人了,怎么到老了连庄稼都种不好了?“农村人,就爱个面子了。”在这种笑话声中,晕头转向的王敞亮去找冶炼厂的王小奎要求解决。他也不知道能解决什么。但是他知道,近几年,总有零星的村民找到厂里,要求赔偿各种庄稼损失,“大家说不出原因,但就知道那个总是冒碳酸气味的工厂肯定逃不了责任”。
王小奎是这厂的法人,40出头的他生得很高大肥胖,身型比一般人都大,这几天开宝马车照常在冶炼厂出没。看见他的时候,尽管工厂刚被县政府没收,但是他还是很镇定,和大家解释:“我运气不好,出事在我任职的阶段。”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王小奎极其聪明,能够找到自己的上升之路。早年,他只是“灶上的”,属于当地最大的工厂洛坝铅锌矿的一名炊事员,因为这个岗位而和领导发生了直接联系,在2005年洛坝集团改制之前,他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中层干部了,改制后,他很容易就承包了这个冶炼厂,成为法人。“他是最知道冶炼厂铅粉有毒的人,厂里的工人们每年都要送到医院去排铅,他从基层干起来的,能不清楚?”这也是村民们现在最怀疑的一点:工厂明明知情,却从来不向村民说明情况。
而王小奎解释说:他们前年整改过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经达标,但是由于工艺原因,铅粉无组织排放没法解决,“但是我肯定不知道有这种结果”。
王敞亮记忆中去年的他,也是一样的镇定。王小奎很干脆地把盖了县环保局的若干章的文件扔在他面前,喊他自己细细去看,工厂的一切都是达标排放的。“找了他9次,就碰见他两次。”其他时候都是办公室的人接待他的,全部都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告诉他家的庄稼损失和他们厂没一点关系。告诉他要是工厂污染的,他必须拿出证据来。
王敞亮还真去找了县环保局,环保局的人告诉他庄稼受污染要找农技中心的人拿证据,他去了那里,可是那里人告诉他必须要环保共同出面,他们才能去做检查。“去了县上8次,都没什么结果。”后来是厂里批给他150元钱淘井费,因为那水已经明显泛白了。对数字,他记得无比清晰。
2006年7月,是王敞亮有了大批同道的一个月,那个月,正是黄豆成熟的时候,可是这次不仅仅是他家,整个水田乡有上万亩地的黄豆都开始掉叶子,“往年雨水多,即使是落些铅灰,也被冲走了。可是今年雨水少”。徽县是甘肃的农业大县,生产的黄豆被四川那边的客商抢着要。这下闹的人多起来。王敞亮还记得村里的路上总有人满脸焦虑地跑着,说今年的黄豆完蛋了。7月底,有200多个农民去乡政府要求解决,后来还是县里出面,将黄豆田分成两个等级,一等每亩赔偿30元,二等15元,“连本钱都不够”。但是能拿到赔偿就已经算不错的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更严重的打击在后面等着他们。黄豆赔偿刚拿到手,就传来铅中毒的消息。
一个城市是怎样失去信任的: 医院和“强人们”的失信
11个村民最初并没有去西安市检测,毕竟,那需要每人300元的费用,“谁家舍得那闲钱?”陈军民说。周浩治疗回来后,他的父亲和陈军民关系好,悄悄跑来和他商量,自己准备去工厂讨还公道,当时还没有想向村民公开,“医生报告很清楚了,告诉我肯定是工厂排放引起的”。当时周浩父亲的重点还在索赔上,他最后嘱咐陈军民,你也带孩子去看看吧,事情可能不好。
一直在县城做小生意,且上过高中的陈民军直觉事情不妙,第二天他就带两个孩子去了县中心医院,“先是说不能查,见我坚持要检查后,给查了血,等了半天结果,说一切正常”。
陈军民有亲戚在铅锌矿上工作,记得他说起过,矿上每年要组织工人们去陕西凤县的矿山医院排铅。而在冶炼厂工作的王坚最清楚整个“排铅”过程,每隔两年,厂里会把一线员工分批送到陕西凤山县的矿山医院去休养一周,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并且喝些牛奶,“说是牛奶可以排除铅”。可是去年检查后,还是有5个一线工人病退了,“他们自己没看见病历,就听说是铅超标很严重,已经不适合再工作了”。所以村里一直说,不到没办法,不要去冶炼厂工作,要得职业病。
而非一线的工人则每年在县城医院检查,王坚说:“总是说没事,一切正常。”王坚现在才明白,那纯粹是走过场,因为身为工厂电工的他这次在西京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严重超标,家里的孩子和他一样。
陈军民想去凤山矿区医院,毕竟那医院离家近,而且矿区医院有专业的检测设备,但是他根本没有去的机会,另外一个村民告诉他,他带着孩子去了凤山医院,人家说要有矿上开的证明才能检测,专业设备不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况之下,陈军民牙一咬,和村里另外10个人去了西京医院。他们是整个徽县最早主动去检查的那批人。“当时也没多想,就想老农民也不能总受骗。”
关于县中心医院和冶炼厂“勾结”的传闻,在11个人确诊后,开始迅速传开了。加上一些工人们开始站出来现身说法,这消息越来越严重。而医院的一位医生说,所谓勾结是村民的想象,医院和洛坝集团的唯一来往,是每年为其非一线员工检测身体,收费10万元。“我们设备不全,很多项目查不出来,像血铅含量就需要专业设备。”但是冶炼厂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查这项指标。但不管怎样解释,县中心医院迅速成为村民不再相信的地方。
而新寺村领导和乡领导,也沦为不被相信的人。村长陈希勇是村里少数几个没去检查的人,也没有参与到村民们上访、谈赔偿的行动中。他自2000年上任以来就和村民关系不融洽,他和哥哥分别担任该村的村长和村支书。“人家惦记着在外边赚钱呢,哪里关心村里人死活?”村民说别的乡的村长都带头找污染工厂索赔,可是他们村却正好相反,村民们闹到哪里,村长都不出现。
陈军民是这样描述乡长的作为的,看了报告先是告诉他们西京医院的检查不能算数,后来见他们去得次数多了,说他一个乡长,根本管不了这事,“人家洛坝集团是县里的企业,你们要闹上县里去。我看县里也未必能管得了”。陈军民说:“到了最后,没有任何人再去村里和乡里,有什么事直接去找县长。”乡长放言的“谁闹把谁抓起来”的名言也快速传播,成为乡长和冶炼厂互相“勾结”的证据。
即使去找县长,大家心里也是没谱的。王小奎并不算真正的县“强人”,“他不过是靠拍领导马屁爬上这个位置的”。而所谓领导,就是连县长都害怕的“张老板”,张国梁从前是县经贸委主任,后来到洛坝矿做党委书记,2005年,洛坝矿改制,张国梁成为洛坝集团的董事长,控股51%,原材料的猛涨价格肯定是张国梁致富的重要原因,他成为县城的“二富”,首富是另外一个矿的老板。
熟悉张国梁的人描述他不是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开着陕西牌照的奔驰,在西安有房子,平时半个月回县城一次,看看他的工厂”。洛坝集团在甘肃属于50强企业,牌子挂在集团的墙上,“张国梁每次都面无表情地喊我们把牌子擦亮一些”。其实县里的老板们基本都开豪华汽车,而且均为外地牌照,也有北京牌照,“那样到大城市办事方便”。
刚开始的时候,张国梁和县领导来往很密切,“后来换了新领导,关系就一般了”。他们还记得张国梁的奔驰车在县城风驰电掣,有次还真碰见了县领导的车给他让道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人们从经济原因上找解释:“他是控股51%的大老板,县里的人当然要看他脸色。”
省里的重点企业很多事情是在省城解决的,他并不用去找县领导解决问题。“反倒是县领导主动去配合他们。”洛坝集团下属的冶炼厂的“县重点保护企业”的招牌就是县经贸局主动送上门的,县经贸局的副局长李玉解释说,有了这个牌子的企业,可以免除乱摊派、乱收费,其实这个牌子更像一层保护膜:县里曾经有过文件规定,凡是有这种牌子的企业,未经县政府许可,任何单位和团体不能去检查,包括环保局。也就是说,不仅洛坝集团在县里傲慢一世,下属的冶炼厂也是县一般部门不能碰的企业。
“环保局在徽县有啥地位?明的、暗的都没地位。”县环保局一位官员抱怨。所谓明的,指的是环保局对企业并没有约束能力,尤其是大企业,暗的则是,在环保局当官的领导,总想着往别的局调——这个局属于收入低的非实权局。“省领导来徽县,就强调要发展工业,我们能管得了这么大的企业?”
曾经在首钢工作过的村民李建中比较有环保意识,在铅中毒尚未被发现的2004年,他就为冶炼厂造成的污染上访过,省环保局批复县环保局处理,而县环保局就拿着“该厂有多少环保设施”的文件来给他看,“答非所问”。他去县“信访办”要求解决,“信访办”的人说:“你是美国人?环境保护和你有什么关系?”李建中说:“他们的觉悟比我还要低。”李建中把他的故事说给村民,每听一遍,大家就发一次牢骚,“找他们那些人管什么用”。
这也是村民们这次抛弃了环保、“信访办”等部门,一开始就找到县长的原因,另外,他们觉得唯一能制止“张老板”的大概就是县长了,于是8月10日,他们连续集体去县政府找领导申诉,在大量的病历前,徽县政府决定于8月22日关闭冶炼厂,可是工厂并没有停工。张鹏伟说:“谁都不能指望,只能靠自己。”8月28日,村民们把冶炼厂大门前的路挖断了,工厂运输中断,结果工厂才正式停产。整个徽县开始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
没能制止的不信任
9月2日开始,县政府派车把强烈要求检查的村民成批送往西京医院,这是村民们唯一相信的医院,当时有方案是把专家请到县城来诊断的,可是张鹏伟在和卫生局长对话时问:“县医院不是说自己没设备,检查不出来吗?怎么才两天又能检测啦?想糊弄谁啊?”大家一片鼓噪,结果卫生局长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因为超标人数太多,而西京医院采取了只收治最早检测出来的、血铅含量超过350微克/升的11个孩子,结果大多数人还是在家里等待。第一个医学专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请到村里做报告的。“他讲了些什么啊?讲怎么预防铅中毒,又讲要我们喝牛奶,说喝牛奶可以排铅毒。”王敞亮还记得那专家是怎么被大家赶走的,专家说到预防中毒的时候就有人质问,病都得了,还谈怎么预防?后来“我们冲上去问他是哪里来的专家,又找他要证件”。来自白银矿业集团的医学专家被围在人群中间,脸色都变了。
当时听讲的有水阳乡的800多农民,大家逐渐形成一种观念,凡是和“矿”沾边的医院和医学专家都不能相信,所以当第二个来自矿业医院的专家来的时候,照样也被赶走了。只有成胜权才完成了演讲任务。“我也是被当地政府硬拉去的,说是我再不去,就找不到人了。”但是小儿科专业的成大夫只对儿童血铅超标提出了种种意见。“成人的我不懂,不敢乱说。”不过村民们也满足了,他们觉得成是外省的,是和徽县无关的专家,又是最早诊断出孩子生病的人,“我们相信他”。
可是成胜权同样无法解决问题,县城只有两个医院,中心医院和中医院,都没有专门设备,也没有专业医生,“我们做了个培训讲座,不过没什么实际作用。排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用专业设备从血液里排到骨头里,再慢慢排除,而且有反复,县医院很难完成这一任务”。县里目前的办法是安排了若干医生常驻村里,每天给孩子发放维生素和钙片,等待省城派遣的专家医疗队的到来。
9月14日,县政府决定将关闭的冶炼厂的部分库存产品拍卖,用拍卖来的钱给村民治病,得到消息的50多个村民聚集在冶炼厂门口,慢慢地挤进拍卖室,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县拍卖局工作人员已把拍卖会安排好,有来自湖南、河南的几家厂矿来参加竞拍,室内的空气十分安静。
可是有两个村民突然高声喊:“没有解决问题,谁都别想把东西拉走。”拍卖局长上前解释,拍卖是为了大家好,“国家不给钱,省里不给钱,全靠县财政支出给大家治病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拍卖掉才能给大家治病”。但是什么都不肯相信的村民开始集体鼓噪,“谁都别想拉走任何东西”。几个外地客商匆忙走掉,退回了他们参加拍卖的费用。
村民们还是每天聚集在路上,任何陌生人都会受到他们的盘问,在他们看来,只有来自徽县以外的人才能够相信。
张国梁很庆幸的是,冶炼厂只是洛坝集团的一家小厂,即使是关闭了,对于整个集团并没有重大影响,而王小奎也很镇定,他始终坚持自己完全不知情。■
(文中部分人名采用化名) 信任失去徽县城市调查铅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