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们重述中国神话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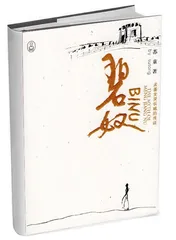
再过50年,也许我们会感谢那个叫做吉米·拜恩的英国老头和他的Canongate出版社。1999年,这个老头儿出版了一套关于《圣经》的口袋书:把《圣经》的每一部分独立成书,并从现代观念予以解读。书卖得并不好,但这些口袋书的灵感来自于他儿时最喜欢的书罗伯特·L.格林的《古希腊英雄的传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在全球寻找合适的作家,让他们挑选自己最喜欢的神话故事,从全新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解读。这个项目没有年限,将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重述神话”系列。
“重述神话”实际上是一道“命题作文”,然而它给作家的自由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加盟的作者已经包括了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及畅销书作家,如大江健三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齐诺瓦·阿切比、托妮·莫里森、罗伯特·艾柯等。其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凯伦·阿姆斯特朗的《神话简史》、简妮特·温特森的《重量》已于2005年10月全球发行,并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加盟“全球计划”的作家是苏童,他选择的故事是中国古老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书名叫《碧奴》。
“这个全球计划对作家是有要求的,要求有三点:第一,在本国家有知名度;第二,在全球有一定知名度;第三,善于描写历史。”卓越网副总裁、“重述神话”项目中国总策划石涛说。石涛向全球编委会推荐了4位作家:余华、苏童、格非、阿来。最终第一个拿到合同的是苏童,因为在编委会讨论期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刚好正在美国上市,摆在各大书店相当显眼位置。再一想,这位作家的小说还改编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在许多中国同行看来,苏童这次接下的是个“肥活儿”:签约作家拿到的版税在5万英镑到7.5万英镑之间。于是苏童的“百万版税”一度成为热点话题。然而无论对于中国出版界还是对于苏童甚至中国作家群体,这都远不止一个“肥活儿”那么简单。
9月1日在北大举行的《碧奴》研讨会上,瑞典皇家文学院成员马悦然赫然在座。但在“重述神话”项目的代理商最开始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时,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机遇。“代理商找到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找过几家大出版社。”石涛说,“我想他们都没有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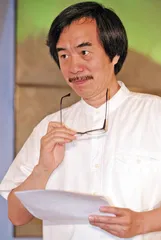
接到代理商发来的长长的邮件时,石涛的第一个念头是:“重述神话”是一个出版业的创举。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苏童的《碧奴》还没写完,就已经有26个国家表示要买下它的版权。
在凯伦·阿姆斯特朗第一个交卷的《神话简史》中,这位英国女作家无限感慨地写道:“这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年代,人类已经离弃了神话。”这句话在中国依然适用。在拿到这个题目后,苏童忽然发现,曾经拥有那么多神话传说的中国人居然已经一个多世纪没有理会这个古老的创作源头了。苏童说:“但当我拿到这个题目而去回想的时候,我忽然发现20世纪以来与神话有关的创作几乎是空白,能想起来的只有鲁迅的《故事新编》。这是一种浪费。”
作家李锐还没有进入“重述神话”的全球卷,而是暂时先进入“中国卷”:先在中国出版,如果反响和质量不错再进入全球计划。他也认为中国神话在最近的一个世纪进入了“空当期”:“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个大的文化气氛就是全盘西化,彻底反传统,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联想到愚昧、落后这些错误的观念,很难有人会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这就造成了自我价值的虚无主义以及自我人格的取消。”
“我觉得重述神话至少可以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看看历史,看看几千年前我们书写历史的方式,看看先人,看看他们在那个时候对世界的想象。以往,我们看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以一种平视的姿态。在《碧奴》这部小说中,我是仰视的,看的是它最草莽、最原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回头看姿态就是我重述神话的意义。”停顿了一下,苏童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一定需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但可以把被我们忽略的传统文化重拾回来。”
苏童说,在《碧奴》中,他想写的,其实依然是他一贯的主题:“在写过那么多一根筋的故事以后,我一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题材,但是孟姜女的故事让我觉得合适。”苏童说他特别怀念写作《碧奴》的8个月,因为:“我从来没有写作一篇东西,感觉到写完是一种愉快。”他说,在写《碧奴》的过程中,他屡屡觉得,自己“飞起来了”。他说:“《碧奴》是个活儿,但更是我自己要写的东西。所以我要给她起一个新的名字。”
李锐将要重述的是《白蛇传》,他说,他要讲的是一个异类被排斥、被驱逐的故事。而在石涛找到叶兆言的时候,他的《嫦娥后羿》已经写了三分之一。“我不是接了订单才写的,它本身就是我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叶兆言说。《嫦娥后羿》将分为两部分,在下半部分中,后羿爱上了一个向他复仇的女人。■
苏童: 《碧奴》 是一步反棋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想知道,你对神话的最终印象来自哪里?拿到“重述神话”这个命题,你又是怎么想的?
苏童:我小时候接触神话从来不是从文本上来接触的,当时写神话的书籍都属于封、资、修,我们听到的神话都是在街头流传的。夏天大家都在外面乘凉,没事时候就去看月亮,依稀看得到光影里树和人的形状,就会说,那是吴刚在砍树。我是在苏州长大的,苏州的广播里都是评弹,评弹里会讲《封神榜》,讲才子佳人。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听见了很多和生活很远的东西。
拿到“重述神话”的命题时,我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计划里包含了很多我喜欢的作家。这个计划对神话的传承方式是文本性的,与我小时候习惯的口头叙述方式非常不一样。因此很多人的思路是从现代角度去阐释,有的甚至就把环境改变了,改变到现代社会的环境里,只是保存了那个神话的外壳,甚至只是人物名字,颠覆或者解构。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琢磨这个故事,想到的是“眼泪哭断长城”。我喜欢这个,这是一根筋的东西,我越琢磨越好。因为不能舍弃这个,我不能把它移植到现代,如果我写一个现代的农妇到长城上去把长城哭断了,就怎么都不对。因为这样,我就不考虑了,而是要真正地讲好一个“哭断长城”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重述孟姜女的故事,难点在哪里?你是怎么做的?
苏童:难点在于能不能有大量充满想象力的细节变成你的填充物,旅程能不能变成小说的重点所在。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看小说看的是情节,但是孟姜女的故事和结局大家都知道了,难度就在这里。我最终用的一切都非常简单,故事完全是直线性的。我觉得这样的小说,离人的生活已经很远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终你写了很多关于“哭”的细节,“哭”有9种方式,比如用胸部哭,用头发哭等等。这个灵感来自哪里?你为什么选择“哭”做你的写作的出发点?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生活中,“哭”有什么样的位置?
苏童:关于哭和眼泪,我无限扩张了,夸大了,仪式化了。
在小说的旅程中,对我最大的刺激来自锡剧。我妈妈是个锡剧迷。“文革”以后其实锡剧播得最多的就是孟姜女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孟姜女一路上要过很多城门,每一次都是哭开的,她一路上哭四季,哭12个月。我没有完全按照过城门的细节,但是关卡这一点保留了,她一路上要过很多关。我把眼泪神化了,有意的。哭的前提是眼泪的禁忌,秦始皇时期的确有人因为哭而被杀,这也是史实。其实我认为孟姜女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哭”与“墙”的故事。孟姜女的传说其实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生存状态:中国百姓有太多的墙无法突破,面对强权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用“哭”来表达一种悲愤的姿态。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没有这次的“命题作文”,你还会把目光转向孟姜女么?
苏童:其实一直以来,我最想写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孟姜女,一个是大禹治水。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你的写作方式很西化,比如你用的是秦始皇的故事,但你不会用“皇帝”的称呼,而是“国王”。你还有很多看上去很“西方”的细节,比如出现了“马人”、“鹿人”等等。这是出于对西方市场的考虑么?
苏童:我不用“皇帝”用“国王”,是因为想模糊时代和背景,让它成为一个意象。我的这次写作彻底是反着来的,跟我自己之前的写作也是反着来的。在碧奴的形象中,我没有背叛什么,而是夸大了什么,也是和一般想法反着来的。这本书其实是一着反棋。■ 神话重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