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村上春树》的译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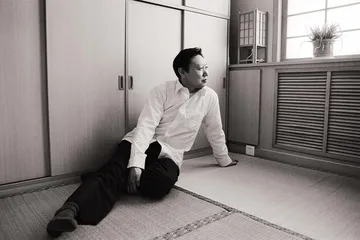
《倾听村上春树》2002年在美国出版,今年6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译者冯涛),作者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杰·鲁宾,他是村上三个主要的英译者之一。之前,鲁宾研究的方向是日本近代文学,专攻夏目漱石。村上在日本算是“纯文学”,不巧很畅销,就被鲁宾打入冷宫,说自己“懒得屈尊去翻翻肯定是描写青少年喝醉了酒在床上乱搞的货色”。直到1989年,一家美国出版社请他审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否值得翻译,不料被“独角兽头骨的氤氲之气”迷倒,此后至今,鲁宾读的、课上讲的,都围着村上春树转了。
美国学者研究村上春树,有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村上受美国的文学和音乐影响至深,比如文字的节奏性是受爵士乐的启发,而简约风格则受几位美国短篇名家的影响。而这些文化元素早已存在于鲁宾的“本能”意识中,所以他既可以利用他对它们的熟悉,又可以当它们是透明,而避免一叶障目,直接看到村上作品的核心;其二,村上客居美国时,在大学的讲演里谈过创作思路和作家的责任,这些他很少撰文提及,鲁宾地利之便,找来了他的演讲稿作为辅助材料;其三,纽约是世界出版界的中心,鲁宾的评述给了我们一个与其说是第三方,不如说是全球化的视角。
对村上几乎所有的小说,鲁宾逐部做了分析。讲到其艺术魅力,集中在他的想象力、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人之生存的思考上(后一点,作者的观察从西方哲学角度出发,与林少华东方视角的阐释相映成趣);讲到翻译的全球化(从英译本转译的德译本曾引发激烈争论);多次提到村上对中国的态度,这个村上春树的中译者难以深谈的问题。鲁宾分析村上作品,认为他对中国一直心怀歉疚(尽管那些伤害不是他造成的,但村上在一次讲演中提到,这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责任)。也正是这种持续性的反省精神,后来导致村上结束国外的旅居回到日本,关注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给平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并写了《地下》,这本对沙林毒气受害者的采访实录。“9·11”后,《纽约时报》的记者还跑到东京找村上,因为他们注意到村上对奥姆真理教徒的分析同样适用袭击纽约的恐怖分子。
看完书,特别想重读村上的小说,好像以前因为行云流水的叙述,阅读时追赶结局忽略了很多东西。鲁宾让我们注意村上小说中所运用的大量隐喻,比如《挪威的森林》等作品中的阴阳两界;比如《海边的卡夫卡》的结束语,“一觉醒来时,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正是村上欲图返回现实世界的信号。除了村上早期的几部作品,后来的几部小说,鲁宾或多或少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他评价《海边的卡夫卡》:“在利用这类策略(超现实手法)时显得相当武断和随意,而且人物经常更多地以作者的便利为前提行动。”但你也可以从他长达20页的评述中,觉察到这本书为什么能成为去年美国的十大畅销书(虽然鲁宾写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呢)。尽管开宗明义说自己是村上的“粉丝”,但鲁宾以平视的角度透析村上的作品,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对村上春树一味追捧或者嘲讽为“小资读物”的二元态度之间,开启了一个阅读的新视角。
书中也讲到村上的生活,并无新鲜事。从华盛顿大学调到哈佛后,鲁宾和在哈佛做客座教授的村上春树做过一段邻居,但从这本书中看不出他们有密切交往的痕迹。关于村上生活状况的描述大多取材于村上春树的“朝日堂”系列,这个系列翻译过来是6本薄薄的小书,就篇幅和主题,完全可以当作村上春树的博客来看:讲的都是生活中的事儿,轻松诙谐,透着他一贯信奉的毛姆的“剃刀里也有哲学”的原则,就是时效性差点儿,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锤的,鲁宾不辞辛苦都给理顺了,适时插入村上作品的评论中,作为写作背景,好像一本未经作者授权的传记。

分析村上春树小说的文章林少华也写过不少,去年结集出版,叫《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书是出版社一手促成的,忙于翻译和教学的林教授在序中坦承没有足够的时间,文章不成系统,好几篇都是几年来他为村上各个新书所做的序以及他本人答记者问,所以说《倾听村上春树》是国内目前最严肃的村上春树的评传也不过分。林少华说自己也一直想写这样一本研究村上的著作,我就替他担心一点,因为一味持欣赏态度写出的书是缺乏吸引力的,林少华是艾柯定义的那种“模范读者”,这也是他与鲁宾的最大不同。不是水平高低的问题,受中日礼教影响的林教授,总显得太客气啦。而美国学者最后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骨子里的那种自信——这在他们张嘴评论东方艺术时还会被放大。你能从涉及客观事实的评述中捕捉到鲁宾的某个小漏洞,而谈及作品中这个意义那个意义,本身并没有准确答案。问村上,从他回读者来信的态度看,我猜他很愿意回你一句琼尼·沃克的话:“是不是呢……如果那样让你容易理解,那样认为就是。怎么都无所谓,是不是都是。”■
译者三问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有什么翻译和出版计划?
林少华:刚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村上新作《东京奇谭集》。另有两本即将出版,一本是片山恭一的《最后开的花》,一本是自己写的散文随笔集《落花之美》,分别由青岛出版社和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现在正在翻译村上的游记《近境·边境》,以便同已交稿的另外两本游记《雨天·炎天》和《远方的鼓声》一起推出。村上的作品,包括随笔、游记在内,一共引进了38种,交稿34种,已出32种,没译的4种——这么着,确确实实成了“村上专业户”,也有人戏称为“林家铺子”。
三联生活周刊:翻译村上春树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林少华:鲁宾教授是《挪威的森林》、《奇鸟行状录》和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的译者,他在《倾听村上春树》中,曾经就将村上翻译成英文时所遇到的难题做过一些总结。同为译者,我和他所遇到翻译难题却不同。他遇到的难题是无法将村上接近英文的风格译“回”英文,因为这类“新鲜、愉快的重要特质正是将在翻译中损失的东西”。而对于我,这个就不成其为难题。我的难题和苦恼在于对村上作品中络绎不绝的西方流行音乐等方面的语汇和知识的一窍不通——一看见那类玩意儿就险些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当然共同之处也是有的,例如我和鲁宾都比较注意重塑村上文体中“干净的节奏感”。这方面,我得益于自己一向喜爱的中国古典诗词。至于鲁宾得益于什么,我就不晓得了。
三联生活周刊:翻译村上10多年来,人生观是否受他作品的影响而改变?
林少华:不管怎样,同一个人相伴走了一二十年而全然不受其影响怕是不可能的。但主要不表现在人生观方面,何况这方面我和村上本来就有相似的质地——我们都看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人家甚至比我还地道和先进。影响主要是在文笔上。我也多少涂抹几块豆腐块文章,我发觉同以前相比,行文好像多了些幽默。比如最近我在博客上说到大学老师如何自在时这样写道:“上完课了基本无人看管,开着空调蒙头大睡也好、和情人(如果有)蹲在路边吃烤地瓜也好,悉听尊便。”若在过去,我的表述就可能是这个样子:上完课就自由了,看电视也好下棋也好钓鱼也好……怎么样,实质一样而感觉不一样吧?■ 文学译者林少华村上春树倾听文化倾听村上春树日本作家语言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