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想更快乐专家就发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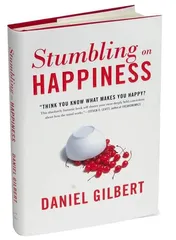
《金融时报》7月21日的一篇报道说,英语世界关于快乐的“新科学”现在成了显学,BBC做了6期专题节目,哈佛大学现在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关于快乐的,或者叫“积极心理学”,剑桥大学和惠灵顿寄宿学校也提供类似的指导。
英美国家出版了一批关于快乐科学的著作,这些著述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者已有的研究,同时也引发了争论。学术研究能对这个人人都熟悉又难以捉摸的问题给出什么新说法呢?
首先,到底有没有一种客观的、可以做科学观察和测量的快乐状态?弗洛伊德说:“快乐从本质上说是主观的。不管那样的境遇会令我们多么恐惧——古代的奴隶、30年战争中的农民、宗教裁判的受害者、面临屠杀的犹太人,我们都无法切实地体会他们的感受。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将是徒劳的。”现在的快乐思想家抛弃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们说对人的大脑做电子扫描可以发现,快乐的人左脑活动比较多,不快乐的人动的是右脑。
但是目前的快乐运动招致了很多人的嘲讽,《独立报》说惠灵顿学院的课程是“为庸才开的处方”,《每日邮报》说那是装模作样,《泰晤士报》说那是“理想的牲畜饲养方法”。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说,新的“快乐征伐”只会让《美丽新世界》中的控制者开怀。富里迪认为,快乐的秘诀是一个悖论:只有在追求别的东西的时候(即古希腊哲人所说的德性),你才能找到快乐。
研究快乐的专家,无论是古代的哲人还是今天的心理学家,他们的意见能让我们更快乐吗?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教授尼古拉斯·怀特写了一本《快乐简史》,概述了西方从古希腊到实用主义之间快乐观念的变化。他说对于如何才能得到快乐,哲学家的具体建议不比普通人的高明。而且,古希腊哲人对快乐的描述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开私塾的,为了说服雅典的富人送他们的孩子拜他们为师,他们需要摆出看透了人生的样子,其实现实生活比他们的理论要复杂得多。

专家们的研究无非是给常识添加了科学性的注解。他们说自愿干的事儿能令人很快乐,莎剧《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尔说:“一当刽子手,衣囊就得肥了。他妈的,我简直像一只老雄猫或是一头给人硬拖着走的熊一般闷闷不乐。”他闷闷不乐是因为他不情愿。专家们又说我们应该加强跟他人的联系,这样才不会动辄陷入绝望。对此很多人都有体会,马尔克斯很赞同福克纳的这一说法:“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创作需要安静,也需要跟人交流,即使要写的只是一篇特别报道。清少纳言《枕草子》第68段说:“快心的事是:献卯杖时的祝词,神乐的舞人长,池里的荷叶遇着骤雨,御灵会里的马长,祭礼里拿着旗帜的人。”我们不知献卯杖、御灵会都是些什么名堂,但可以肯定是社交活动。
哈佛教授丹尼尔·希尔伯特著有《撞上快乐》一书,他说不要以为古代人对快乐之道特别有心得,他们的生活与今人完全不同。现代人都面临三个选择:住在哪里、干哪一行、跟谁结婚。我们是第一批需要做这些选择的人,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没离开他们的出生地,并且子承父业(叫米勒的就开磨坊,叫史密斯的就打铁),古代人跟谁成婚是受到他们的宗教信仰、阶层和地理位置限制。农业、工业和技术革命使我们有了选择自由,“破天荒地我们的快乐可以由自己来掌握了”。
希尔伯特说,不巧的是大脑的结构让我们无法决定做最快乐的事。我们是唯一一种大脑可以想象未来的动物。“只要黑猩猩还不会因为孤苦伶仃地变老、不会因为想到暑假而微笑、不会因为发胖了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苹果动怒,能够想象就仍然是人类的特征。”当思考未来的快乐时,我们又不好好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学习如何使用马桶时,我们可以采纳别人的建议和经验,但是一轮到快乐我们就不愿意仿效别人了,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过得更好。因此我们总是想买更大的车、找更好的对象,虽然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将很快适应新鲜的东西,它们不会让我们更快乐。“心理学家称之为适应、经济学家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婚姻。”■ 发笑快乐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