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10亿元诈骗案里的三角关系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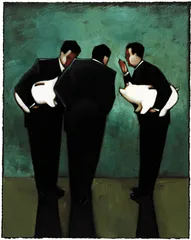
我们对李培国几乎一无所知。这正是他的可怕之处。直到李培国近日在法庭上得知自己被判无期徒刑后奇怪地露出了他此前从未展现于公众面前的笑容的那一刻,我们仍然只知道他是个“港商”。
李培国一直在扮演他的幕后角色,他分文不用就从一家“问题公司”那里取得了价值近10亿元的股权。就像一名技巧高超的足球前锋,轻巧地绕开了地方经贸委、银行等一系列“后卫”构成的屏障。这是一个标准的欺诈和投机的故事。问题是,在涉案到获罪的近10年时间里,这个能量巨大却又默默无闻的商人到底摆布了什么?
被“摆布”的9.52亿元股权
6月9日站在被告席上的李培国已经不名一文,而两年前他还是坐拥10亿资产的富人。47岁的李培国曾是原香港富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同时兼任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德国际金融中心)副董事长、总经理,在权力和财富上都飞黄腾达。和所有投机客的故事一样,李培国在几年间大起大落。他获取财富看起来得心应手的势头在2004年走到了尽头。办案人员称:“这一年的3月24日,他在通过深圳市罗湖边防检查站时被阻留,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市检一分院的办案人员前往该边防检查站,李培国被刑事拘留,4月2日予以逮捕。”
让李培国触犯“诈骗罪”的主要罪条,是他非法占有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70%、价值9.52亿元的股权。而这笔被李培国轻易获取的巨额资产,在他之前已经几易其手。办案人员称:“该股权名义上原属霍海音,实际所有人是北京市商业银行。”
事情起因:7年前轰动一时的原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霍海音挪用公款、非法发放贷款等30亿元大案。该办案人员介绍:“霍海音在任城市合作银行中关村支行行长时,1993年对大连奔德的房地产项目产生了兴趣。”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是由奔德集团于1993年1月成立的,原股东为奔德集团,后于1994年8月增资扩股为两股东,奔德集团持股70%,香港新世纪发展(中国)有限公司持股30%。1995年4月,奔德集团在大连又设立了大连新世纪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酒店),股东为奔德集团、香港新世纪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和大连市中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设立上面两个公司的目的系于大连开发房地产业务。
“但由于中关村支行无权异地放贷,遂转而通过奔德集团在北京设立的北京双兰德化工有限公司和奔德集团北京办事处放贷,并进而由奔德集团投入奔德大厦的方式运作该项目。”1996年底,奔德集团资金出现问题,项目运作困难。于是,经洽商,奔德集团将其持有的奔德国际金融中心和新世纪酒店的股份作价9.52亿元转让给霍海音及其弟霍海波为董事的香港银富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富公司)。1998年1月,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霍海音正式成为奔德国际金融中心和新世纪酒店的董事长。这笔来自银行的9.52亿元,第一次被偷换出来,成了霍海音家族的财产。
这一年,中央开始清查整顿国有银行违规贷款。霍海音被免去行长职务,改任清欠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清收大约50多个亿的账外资金和逾期贷款。东北的三个项目占了20亿元,其中,这单9.52亿元的“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又最大,此时成了霍海音急于脱手减罪的最大包袱。“霍海音已经到了毫无退路的地步,他的补救办法和一线希望,只有三条路:‘一是再从其他银行融资;二是项目股权转让;三是引资参股。’”
霍海音于是开始四处寻找9.52亿元的下家。
黑吃黑
霍海音托人先找到时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但中行因为霍海音已被拘捕不愿再融资。在银行融资和引资参股两个“赎罪”之门被关闭的时候,港商李培国出现了。
据了解,有一次该案的预审员曾岩在审问霍海音时,向其透露,有一个姓杨的台商通过台办找到北京市城市合作银行和北京市公安局,打算买下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项目。据说这个台商曾经向这个项目投资过500万。如果交易成功,那么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违规贷款一事就从霍的案子中删去了,霍海音的罪行也就会减轻很多。
这起收购背后的操盘手正是李培国。他找到了曾岩这个突破口,而他出现时的台商背景和曾经的投资者身份,实在是霍海音心目中再好不过的9.52亿元的接手对象。“二人一拍即合,”知情人说,霍海音随后找到了受聘为他辩护的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建中作为中间人。他和后者“在1995年相识,并在1996、1997年的一起‘担保责任纠纷案’和一起‘农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建行北京信托投资公司收购’中合作而相熟”。
正是这一段事实的出入让张建中卷入了后来的伪证案。张建中说是在霍海音出事前,他就已经接到了授权委托,1998年2、3月份,他手写的委托书草稿传真给霍海音处,过了一段时间,霍海音派人将打好的填有霍海音名字和日期(1998年3月18日)的委托书送至张建中的办公室。而法庭最后认定的结果是,空白委托书是霍海音出事后,曾岩在审问霍海音期间让霍海音签发的。
根据法院审理后公布的事实,曾岩曾对张建中说转让大连奔德是霍海音的意思,富国公司也想收购,但因霍海音被抓,手续不好办。于是,李培国、曾岩、张建中等人在京广中心的咖啡厅见面,详谈收购细节。曾岩提出可以让霍海音在看守所里面给张建中写一份关于大连奔德转让的委托书。1998年10月中旬,曾岩拿来两份霍海音给他的授权委托书,内容是大连奔德董事长霍海音,委托张建中全权处理大连奔德项目,日期是倒签的1998年3月18日,霍海音被抓以前的日期。1998年12月10日,李培国来到张建中的办公室,张建中给了李培国一份转委托书,依照其权限将上述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有明确意向全面收购该项目,并承受委托方在该项目上的开发权及相关债务”的富国公司执行董事李培国。
据此法院当时认定,霍海音和曾岩、张建中等合谋,意欲通过采用伪造虚假授权委托书的手段,转让涉案的大连奔德,以期在名义上形成霍海音违法发放贷款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已被挽回的事实,为霍海音减轻罪责。
正是霍海音“急于减轻罪责”,李培国毫不费力接到了这9.52亿元的第二棒。“尽管李培国承诺只是和北京市商业银行谈判时使用,不做其他用途。他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股权的真正所有人。在他看来,霍海音挪用银行巨款得来的一公司价值9.52亿元的股权,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李培国绕开了“后卫”
并非只有霍海音一个人心急。霍海音案案卷显示:“霍海音在当时说,‘曾岩在预审中跟我说,我在非法放贷犯罪,大连奔德这个项目给银行带来的损失最大,银行和办案机关都希望把这钱追回来’。”李培国同样是银行清收违规贷款的一次难得机会。这也成了李培国对9.52亿元看上去势在必得的第二个砝码。
李培国拿到全权处理大连奔德的转委托书后,在北京市商业银行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起他操纵下的收购迅速而顺利地达成。
1999年2月12日,富国公司和银富公司在香港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同意,由于该股权的实际拥有人是北京市商业银行,奔德集团和转让方银富公司投入奔德国际金融中心及新世纪酒店的资金系中关村支行借贷形成,故转让方同意由承让方直接向北京市商业银行偿还贷款,以此作为承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方式。此外,转让价款所发生的利息由承让方与北京市商业银行协商解决。《转让协议书》还特别规定了“承让方在与北京市商业银行签署偿付债务合同后,转让方应无条件协助承让方在大连办理完成国内之一切有关转让报批手续”。
但李培国的富国公司成为奔德国际金融中心及新世纪酒店的股东后,与北京市商业银行约定解决的奔德大厦债务利息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起诉材料称:“李明知富国公司没有与北京市商业银行签署偿付债务合同,仍于1999年3月8日向大连市外经贸委递交了转让申请书,在其递交的《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中,特别规定的条款被删除,从而掩盖了该转让未征得北京市商业银行同意这一事实。”
这篡改后的转让协议书没有被审查和发现,李培国又一次毫无阻碍地从大连经贸委那里取得了“大连奔德”项目再次转让的批复。李培国依据批复,在工商局等部门变更了“大连奔德”项目的股权。这样,这个从未出资一分的港商,成了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70%股权的新主人。
李培国一路绿灯的局势在他试图接管奔德公司时却遇到了意外。起诉材料称,1999年3月,李培国在拿到大连市外经贸委的批复后,立即要求大连奔德总经理王元群进行交接。王元群表示,他不是奔德公司的所有人,协助交接必须有合法的法律文件及相关手续。1999年3月23日,王元群给银富公司总经理霍海波打电话说了此事,第二天,霍海波给大连市外经贸委发函,对银富公司与富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事做了说明。两天后,李培国强行接管大连奔德,让公司工作人员必须交接工作。王元群向霍海波和北京市商业银行报告了“3·25”事件,表示自己无力控制局面。随后,北京市商业银行就大连奔德问题给市政府写了紧急报告。接管的人事冲突一直接连不断,直到李培国2004年在深圳市罗湖边防检查站被拘捕。
北京市一中院对此案审理后查明,1999年3月,李培国作为富国公司的授权代表,在没有与原北京市商业银行达成转让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70%股权意向的情况下,使用虚假的转让协议书以及非法的授权委托书、转委托书,代表大连国际金融中心,向大连市外经贸委提交了虚假的股权转让申请等相关材料,骗取了大连市外经贸委批准股权转让的批复文件。随后李培国以富国公司的名义,将原北京市商业银行在大连奔德国际金融中心的70%股权(价值人民币9.52亿元)非法占有。一中院以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李培国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金融诈骗案10亿元三角关系大连房地产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