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拉山的“风水先生”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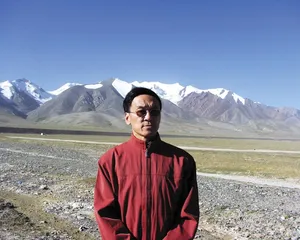
我第一次进入唐古拉是2001年8月份,当时作为专家组组长,看看整个方案,要讨论些技术方案。唐古拉地段有130多公里,唐古拉山口作为青藏线的咽喉之冲,海拔5072米,相对比下面更困难,有很多矛盾重重的地方。我们要选择唐古拉气候条件最好的时候施工,6、7、8月份是暖季,但由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比较大而且集中。这又给施工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在施工时候要减少对多年冻土的扰动,尽量不要有外界的热量,能不破坏的植被尽量不要破坏,不然太阳传递给地中的热量更多,而填土本身也带来大量的热量。
铁路选的垭口应该说比公路走的唐古拉垭口地质条件要好,感觉更开阔,气温比公路那边高,毕竟建公路时受时间和技术的局限。但是唐古拉山还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以为山上地形平缓,岩性条件比较好,积岩埋得比较浅。但到那儿才知道,有个缺点,暖季时候,整个地表积水比较严重。冻土的层上水很发育,给我印象就是到处水汪汪,一到夏天一大片水。一踩在土里,都好像有点冒水,山前缓坡地,都是这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冻土湿地问题。在唐古拉山口的湿地比公路地段要多些。有些斜坡湿地,处理不好,对路基稳定性有很大影响,这算是个比较难办的事。
第一次去唐古拉山,主要就是四处转,四处看。我们搞地质工作的,就是像风水先生一样,到处要看,到处要检查,看一看能看出些问题来。当时主要看出的就是这个“斜坡湿地”问题。其他问题还不大。因为整个分布面积不是太大,有个十几公里,后来我们还是采取加“片石区”,冷路基,加热泵什么的,都可以解决的。
应该说,跨越唐古拉的技术研究在70年代就开始了。现在的工作是在我们当时工作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冻土的整个分布范围是500多公里,完全是依据我们当年跑断腿做区域调查时画出的冻土地带分布图。
1974年,青藏铁路大会战。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青藏高原的冻土研究。1976年在唐古拉山口北面的风火山修建了一个483米的实验路基工程。在当时,青藏铁路第一次上马,我们主要是用这段实验路基提供设计方案。但是很遗憾,做了将近5年后,青藏铁路就下马了。有关的研究工作进入半停顿状态。现在来看,原因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国家没有足够财力,还有一个是因为冻土的技术不过关。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冻土技术是否过关看当时提的修建要求。当时铁路时速要求只是60公里,冻土技术其实已经过关了,而现在青藏铁路的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 在高原冻土技术过关后,现在青藏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100公里 )
( 在高原冻土技术过关后,现在青藏铁路的设计时速达到100公里 )
我1970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在东北大兴安岭的多年冻土地区研究过3年。唐古拉山附近的冻土和那边的冻土恰好是我国的两大种类。一种是高纬度,一种是高海拔。冻土自身性质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冻土的生存环境和环境变化是不一样的。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地表植被比较茂密,冬天还有积雪,这对多年冻土形成保温作用。而青藏高原植被覆盖不那么茂密,冬天很少有积雪,冻土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另外,青藏铁路大体与青藏公路平行修建,两者之间的平均距离不到10公里。在10公里的狭长走廊内已建有格-拉输油管、兰-西-拉光缆和青藏公路,再加上一条青藏铁路,其对环境的干扰强度可想而知。冻土环境十分脆弱,一旦破坏极难恢复。在这不到10公里的范围内,冻土环境的改变也必将影响到工程的稳定性。
我观察青藏铁路的冻土几十年了,大部分处在退化的过程中。因为全世界气温变化,有升高趋势。南北界往中间缩,多年冻土面积在变小,厚度也变薄,原来100米,可能变成90米、80米。冻土温度在缓慢升高。我们在风火山做的地温观测,测40年的资料,在这三四十年中,十几米处的地温升高了0.1、0.2、0.3摄氏度,对多年观测的人来说,这是很大变化。在风火山地区,是低温稳定冻土地带,年平均温度是零下3摄氏度,而在楚玛尔河地带,都是高温极不稳定的多年冻土,本来只有零下二三摄氏度,一下升高这么多就融化了。所以我们把青藏高原冻土分为4部分:高温极不稳定、高温不稳定、低温基本稳定、低温稳定,温度越高越不稳定。
现在想想,70年代那几年我们就冻土真是做了很多工作。第一是区域的冻土工程,我们把整个高原冻土的分布范围、特征,已经勘察清楚。后来青藏铁路下马之后,我们还在室内做了大量实验,把冻土的力学、热学性质做了大量实验。风火山冻土基地一直没停,坚持到2001年工程重新上马。
所以你要我说当年在风火山上的日子,几乎没什么记忆。一呆就是半年以上,非常荒凉,你现在看着很美的东西,当时就感受不出来,还是感觉很孤独。而且紧张。越是在野外,越紧张,因为本身很艰苦,就不想多呆,呆的时间就想多做点事,怕落下什么。夏天在外面取很多土样,晚上要做实验,但冬天就只是单纯做观测,没野外工作,大雪封山,就更无聊。我就在风火山上拉小提琴,反复拉练习曲,拉得别人都受不了了。有时候就在空房子对着房子唱歌,逮着一个厚厚的歌本,会唱的,从头唱到尾。受不了的人是会得抑郁症的。
最苦的还是开始做区域调查的时候。没有汽车,还要在路上搭过往军车、运煤车,有时候就要骑马进入无人区。还有经常带着地图和工具徒步进行地质填图,每天早上7点出发,正常是下午17点回来,走一天路,20公里地。带上一壶过去解放军用的绿色军壶,带上午餐——两个馒头,加两三片午餐肉,还有几颗糖。这些都是当时配给的,不是敞开供应。蔬菜根本是吃不上的。
中国科学院考察队的路线分北线路、南线、东线。我参加了后面两个,北线比较简单,小部分人在做。后面两条线路是我们工作重点,因为铁路最后修哪条主要是比较这两条。南线是冻土的南部界限,现在的安多以南。东线方案最后被否定了,感觉那里的地质条件更复杂。
不过我们在东线调查时遇过险。1976年8月份,我和两个同事到离开公路80公里的无人区工作,那天的工作任务是步行20公里进行地质测绘填图。开始很顺利,但越走越觉得地形不对,没找到早就应该出现的山谷,却走到了一条大河边。我仔细核对地图,分析周围地形和已走过的时间,判断是提供的卫星图有错误。那时已经是下午17点,离驻地已有30多公里,又开始下暴风雨。走到筋疲力尽还没有找到方向,我们只有在一个山崖下取暖,等待救援。幸亏有一位抽烟的同事,带了火柴和烟盒,第二天他把纸烟盒撕成三条,用仅有的几根火柴,点燃烟盒纸,让本来从我们上方走过的救援队员注意到了我们。
从施工角度来看,青藏铁路并不是很困难。从科学研究来说,比较困难的还是高温极不稳定地区。现在建立了冻土区长期观察系统,500公里,建立了78个观测端面,是使用无线传输,在今年6月20日之前可以全部做好,这样我在格尔木和北京就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把远在千里之外的唐古拉的数据检测出来,判断路基工程是否稳定,这个系统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在一条冻土区的铁路线,建立一个整体的观察。■ 唐古拉山风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