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绝代的中国标本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苌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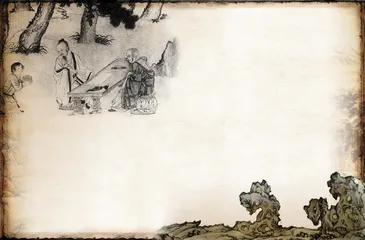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富有才情,在艺术领域内——写作或者绘画,各有造诣,受人尊敬。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挣钱方式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太远,但积累财富不是生活的主题。他们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很体面,但那种体面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模式化要求:开豪华车,住高档社区,穿名牌衣服,他们避开这股洪流,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能承担的最富个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活细节上有所讲究,但品位不是按商业社会的品牌标准建立。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几十年来国家变革与传统文化的割裂,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是另一种痕迹——他们传衍着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在主流的空隙间,游离于体制外,有点清高,有些不拘,博古通今,兴趣广泛,过着清人张潮所说的“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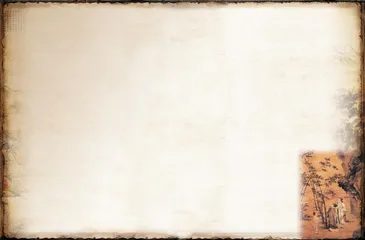
他们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精神气质,接近古代名士精神。“名士的精神实质体现在四个方面。”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说,“第一,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他们看重个体,忽略社会。第二,在个人和政权关系上,往往把自己看作真理的化身,不把权势放在眼里。第三,从思想方法上,是道和器的关系,重形而上,轻视形而下,认为无限胜过有限,喜欢琢磨玄妙和虚无的东西,忽略有限的东西。第四,从人生态度上,注重的是审美,而抛弃功利和实用的人生态度。”古时所谓名士,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人的谈资,这和你经常从娱乐新闻上看到的名人干的事儿性质不一样。名士和名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名士的言行举止蕴涵着一种生活哲学,恰是值得这个社会思考的。
如果在定义上妥协,把名士称号落在几位采访对象头上,他们都不太乐意。他们并不安贫乐道,生计当头,都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够洒脱。所有人都有他们相对独立又统一的对名士的看法,比较共通的是,名士绝对是不功利的,而这只有在一定的生活背景中才能做到。宁稼雨从事古代文学和文化史关系研究,是《魏晋风度》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等书的作者,在他看来,名士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出身门阀贵族,有垂手可得的金钱和政治地位,却又视其为粪土,这样才能催生所谓的风度。照这个标准,现在唯一拥有成为名士硬件条件的应该是高干子弟。但问题是,世风变了,以上精神状态在如今社会的价值判断中,不再是一种上层的境界,无法给他们提供潇洒行世的满足感。
小宝说:“名士要几个世代的积累,我们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到‘文革’,刀子下得特别狠。我们这一代中,以及比我们小一点的IT新贵,能让大家都服气的名士不大可能有,因为都有贫困记忆,这是一辈子逃不掉的。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觉得钱很重要,就不可能造就名士这种稀有动物。”这么说,我们已经失去培育名士的土壤很多年。“名士”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有名词,与其说表达一种期望,不如仅拿来作为一个参照框架。
阿城:知识结构决定人生
在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中,阿城谈到他知识架构的建立:60年代还在上初中,因家人的成分问题,有了很多悠闲时光,大部分时间都在书店度过。站着读完一本本外国小说、历史古籍,要么就是逛琉璃厂的画店、古玩店,和老师傅们学到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这样有了异于正统的知识结构,阿城说:“知识结构决定你。”
有个有趣现象。问到查建英对阿城的印象,她反问记者:“你去过他们家么,他家什么样呀?”采访小宝时,他问:“阿城是在织布呢吗?”阿城就是这样一个令他的朋友永远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他的传奇,你总是从别人口中听说。查建英说她在美国那几年,人们还传说阿城在教钢琴,“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我不是名士,就是一寒士。”这个寒士坐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如是说。这个下午,北京一转连续数日的苍白天色,碧空如洗,光线透过客厅落地窗洒进来。窗外是四面房子围成的天井,花草葳蕤,一棵一人高的小枫树刚长出漂亮的叶子。
阿城的家位于北京以北的一处村庄,之前他在城东的房子也是自己找人盖的,但因性质有问题,现在已经成了瓦砾。提起这事儿,阿城一句带过,我只是从小宝口中知道那房子给他带来不少麻烦。“现在这房子,地面以上算我的,地面以下是国家的。”阿城说,“人们还没安身立命,你们谈什么名士?等到土地私有制了,可以安身,再说立命的话题吧。”
阿城说他没有职业,但他总是很忙,最近一段日子,每天连觉都睡不够。这几年,他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国内也鲜见他的文字发表。有时看央视十套的“人物”栏目,会看到他一闪而过的名字出现在总策划名下。作为写作者扬名立腕的阿城,早就知道写作养活不了自己。“在国外啊,你说自己是作家,跟说自己是个要饭的差不多。只有咱们国家特殊,人们经常在名片上写自己是个作家。”
策划、编剧,是阿城这些年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不愿详细讲这方面的事情,问工作是否让他乐在其中,他说:“最好把工作和兴趣分开,否则一天到晚在工作中,不得休息。我有兴趣的事儿,不一定是费力的,工作是比较费力的,因为要做到合乎标准。”
1986年,阿城初到美国,陆续呆了近20年。“在美国,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朴素。”坐在北京的家里,重新审视美国生活经历所赋予的,阿城说,“再有钱人也会开辆皮卡自得其乐,可在我们这儿,汽车成了财富的象征。电视机、手机这样的消费品,美国人通常用到坏为止,国人忙不迭地更新换代,成了显示财富的工具。社会鼓励消费,还不能做到安身立命的人,却模仿着已经安身立命的国家人的生活,学到的全是皮毛。物尽其用,这样的品质50年前的中国人有,现在没有了。你要是穿着几十年前的旧衣裳,人们会笑话你。”
3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棋王》,几篇小说震动海内外文坛,查建英这样评价阿城的小说:他的写作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是因为他的基本姿态是“逸出”,“他的小说有一种冷静而温和的调子,既不是反抗,也不是控诉,是写他的主人公如何从精神上飘逸出去,沉浸在另外的世界中,比如棋道”。阿城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再写小说,一个原因是没有兴趣给不认识的人写作。“以前是要写给朋友看,写给比自己高的人看。这道理跟京剧似的,为什么没落了?因为比你唱戏的还懂戏的那票观众没有了。”这些年文字在国内发表得很少,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出版环境不尽人意,“《闲话闲说》有两个版本,国内的那个,我几乎不看。以前的编辑,还知道把删的地方留几个方格出来。现在的做法,是删得不留痕迹,上句和下句连着,读着还挺通顺,但意思全变了”。
洪晃对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情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特不待见我。那是在姜文家里,当时我刚看完《威尼斯日记》,特别崇拜阿城。我到的时候,看到他正跟别人聊天,侃非洲雪山草原什么的。我跟一旁犯怯,看着他们聊,插不上话。过了好半天,我看他还不理我,就问他:‘阿城哥哥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我呀?’他反问我:‘不跟你说话,就是不喜欢你啊?’他没承认也没否认,让人一下没了脾气。”洪晃说阿城有他那代人的执著,特别不容易受诱惑,觉得他活得特别明白。
看那些导演、作家和艺术家谈与阿城的交往,让人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他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而阿城说,“我喜欢和不读书的人来往,他们身上没有读书人的那股习气”。平时来往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他交友的准则是,对方有信用。
无论是美国还是北京,都被阿城称为他的“集散地”,他并没有定居的意念。“我从十几岁离家出走,已经习惯了游走的生活。”阿城说,因为这几年北京的事情多起来,所以就暂居北京。阿城说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自己太懒,极少有不高兴的时候——“当知青的时候,差点死掉,我这是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样一天天活着,不挺好么。”
小宝:曾经的上海文青
小宝住的麦琪公寓在上海市中心,俯瞰领馆区,这是解放前的老公寓,他买下来不久,就被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小宝说他喜欢老房子的设计,不像后来的板楼那般紧凑,只强调功能性。老公寓的空间稍微有些铺张:层高,卧室、卫生间比较大。对于家的概念,他说:“家应该是能让人像动物一样生活的地方。”
小宝生于上海,父母是北方移民过来的干部,80年代,一度是个意气风发的上进青年,那时他在军事院校教“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前几年热起来的‘新左派’,我早就研究过了。”小宝说,“我看现在的几个所谓‘新左派’写的东西,净是玩弄概念,而且字里行间透着人品很差。”80年代结束,他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
后来的小宝写过电视剧,办过报纸。陈村说:“他那份小报,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八卦报纸,他自己写专栏,没事就把谁给编一个段子。他要是诽谤人,看起来非常有意思,要是夸谁,那就有问题了。”现在和他来往密切的几个好朋友,孙甘露、陈村等,都是那个年代认识的。小宝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季风书园的老板,偶尔被请去参加电视脱口秀,或者在杂志上开专栏写书评。
这也是让近些年才认识小宝的毛尖,觉得并不了解他的缘故,尽管俩人经常取乐对方:“如果要评‘上海三宝’,那小宝绝对是逃不掉的。他蛮海派的,那种好的海派——灵活,幽默。说话很逗,喜欢装光棍的样子,怎么调侃他,他都无所谓,你找不到他的死穴在哪儿。但我看到的小宝是有舞台表演性质的,并不知道真实的小宝什么样,他把自己藏得很深。我听说过他在80年代的一些事情,比如那时别人都觉得他会做大学问,可现在他根本不愿意你说他学问好。我听来的小宝和眼中的小宝不一样,我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他。”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生活很辛苦,你看小宝,不辛苦,平时生活状态是放松的。”陈村说,“不用上班,书店生意不错,想干嘛干嘛。他人很聪明,做事情认真,不蒙人,不偷懒。他没有很大的发财理想,过自己愿意的生活,与自己愿意交往的人交往。”他很欣赏小宝的为人,不惊不乍,讲义气,很认同他的文笔,“他不算这行中的明星,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的眼光与众不同,文笔毒辣,可能因为他一直游离在主体之外。他知道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趣味。他不是不激愤,但他的激愤比较有个人色彩,他会把一些严肃的问题化解成黑色幽默”。
孙甘露说:“小宝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从没有放弃社会批判的立场,思考很冷静。你看他现在写的书评,虽然嬉笑怒骂,但根是严肃的。早年间,他系统研究过金庸和毛泽东思想,让他的思维体系有很大不同。”
为人风趣,喜欢呼朋唤友,聚会上总是抢着买单,但你看不见他的时候,八成是在家里读书,这是小宝的朋友对他的一致印象。孙甘露评价小宝“里里外外很干净,很有分寸感”。
“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年轻时倒是想走思想救国的路线。后来发现国家也不需要我们救,自救吧。自己过好了,国家也好了。而且那时的学术圈里,都是些说大话的人,看着很讨厌,就想离得越远越好。”小宝很愿意和你谈谈马克思分析错了的一处地方,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意识是怎么落后,讲讲为什么辜鸿铭和袁克文是他心目中的名士,但如果让他谈自己的生活态度,歇吧。不说,也是一种态度吧。
叶放:江南雅士生活
“不出城廓,能获灵泉之隐。”叶放引老庄的话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
苏州的画家叶放住在自己设计的园林中。站在客厅前的亭廊下,你能感到作为居住环境的园林,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园带来的不同气息,前者满是精心的细节,正值江南初夏,池塘里的荷叶在暖阳酥风中微微摇曳,锦鲤很活泼,池水也很通透。叶放用的是天然生态链,池中放水后,他放了100斤螺蛳,螺蛳可以吃水里的脏东西,又放养了吃螺蛳的乌龟。假山是他在浙江找人开采了一整座山头,从中挑选出700吨假山石堆砌的。山洞壁上,镶嵌着古代的碑文小品,小桥上刻着回文诗句,山石层叠间,桂花树和石榴树正枝繁叶茂。
从前苏州有文养的人,挣了钱就会想到造园子。叶放的外曾祖父毕诒策在浙江做知府,告老还乡后造了毕园。叶放小时候住的毕园,在他七八岁时,陆续搬进很多人,渐渐破落,风光不再。几年前,叶放和几个亲戚朋友合手买下五栋联排二层小楼,有了楼前这片500平方米的院子。由他来主持设计,这样经过3年的建造,叶放又回到园林中。
叶放画的主题一直是园林,园子造好后,他过上了临窗作画的生活。对园林,叶放有圆梦情结,园子周回曲折,弄得很是漂亮。造园时他预留了展示空间,只是没想到这个园林比他的画还要出名。有次邻居问他家是不是要做法会,因为门口站着40多个和尚,等着进门参观。采访时,正赶上不认识的设计师从远方来,叶放陪着喝茶。“叶放人很憨厚,他就不知道怎么说NO。”叶放多年的老友祝伟中说。叶放笑说把画画的时间都挤没了,有一点无奈,但似乎又没真往心里去。
叶放是个爱玩的人,但玩的和别人不太一样。儿时的叶放记得梅花初绽的早春,外公叫小孩们去折梅枝,谁折的梅枝最好看,就让他上楼插到书房的花瓶里。他从书房窗户往外看,看见另一家园子,重峦叠嶂,心中很是感慨。还有一些晚上,他听到嗯嗯呀呀的声音从厅堂传来,起床偷窥,看到的是大人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唱戏。
与叶放聊天,你会发现这个画家饱读诗书,有惊人的记忆力;吃饭,你发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他所流露出的闲情意趣——喜欢昆曲,古琴,吟诗,会票评弹,画国画,有古韵犹存的风雅。叶放的朋友说他就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还因为他的雅集。
菊花古剑和酒,早已被咖啡泡进喧嚣的庭院,古时候没人说party,文化人搞聚会就叫雅集。叶放办过琴会,诗会,曲会,花事雅集……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他在家里做的雅集主题叫“物有所诗”,讲古人如何将诗情画意寄托在器物上。
叶放的雅集办了有10年,让他结交了不少同有此好的朋友。晚上19点多钟,客人陆续到来,有教育工作者、医生、商人和作家等,寒暄后,大家围着客厅里的长桌坐下,交流诗作,把玩古董——写有诗句的笔筒、扇子、竹本和绣本的对联,欣赏古琴吟唱。叶放熟练地控制着聚会的节奏,渐渐你发觉来得都是“腕儿”:医生在古琴伴奏中,幽幽唱起“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他邀学芭蕾的儿子伴舞,小伙子光着脚,凝神跳起云门舞集式的自由舞蹈;两位台湾老先生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原来他们70年代初在加州伯克利念书,入校先被强制学习文化大革命和“老三篇”。这天是母亲节,有人想起他们故去的母亲,声情并茂讲起母亲的故事……
茶不醉人人自醉,诗物雅集后来成了歌舞晚会。每次雅集叶放都会写一个活动计划,这晚到后来,早就偏离了他原来策划的内容(抚琴诵诗,即兴赋诗),不过他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玩得尽兴是最好。■ 读书文学名士阿城叶放查建英中国标本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