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川:从谩骂中我看到 一种可怕的冰冷
作者:李菁(文 / 李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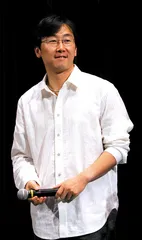 ( 陆川 )
( 陆川 )
“我感觉到了文字中的那种血腥,这确实让我想起了红卫兵。给那些最恶毒的谩骂者这样一个定义,我不后悔。”陆川在自己的博客上,将那些围殴者称为“红卫兵”,这一定义激怒了不少网民,陆川的博客由此也遭围攻。
“对韩、白之争这事本身,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评说之处;父亲说话时候,坦率而言,我也并不认为他该说——当然就事论事,父亲的那些话一点都没错,就算是污点证人,他也有开口说话的权利。白烨再怎么样,在正常体制的国度里,他有批评的权利。但我发现父亲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后,立即被蜂拥而至的网友围攻谩骂,那种批倒批臭的感觉,令我不自觉地想起‘文革’、想起红卫兵。”
出生于1971年的陆川,对“红卫兵”并无直接经验。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真正拍电影,中间隔了三年,喜欢历史的陆川在那段时间看了大批文献,“历史有时是惊人地相似,但只有红卫兵是特殊的——它是一个人发起,但集体参与的事件。在这种集体的盲动中,那种非常血腥、非常残酷的东西全部被释放出来,而当初所谓的政治信念,其实到后面完全不过是个人情绪与个人私欲的一种发泄”。而在这次事件中,“成群结队的小朋友摇着小旗,春游似地过来骂战”,陆川似乎感觉到了一种相似的盲动与发泄。
“一种社会秩序或者行为约束的东西被打破后,人内心的一种兽性是非常可怕的。你去看看围攻我父亲博客的那些谩骂,你会发现一种冰冷,特别可怕的那种冰冷。”陆川说,一个潜伏在网络下压抑了特别多愤怒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发泄愤怒的方式,这是值得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关注的话题。
起初陆川对这场论战并没有太在意,直到去父亲的博客上看到一片谩骂时,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伤害,“真的是没道理的骂,奇怪的怨恨和刻毒”。“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只是想保卫父亲,我没有考虑其他任何事情。打个比方,就像以前要抄家,抄到我们家,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我父亲。”后来有陆川的朋友告诉陆天明,陆川看了网上那些赤裸裸的谩骂后气得发抖,于是也有了那篇言辞激烈的文章。
采访中,能明显感觉陆川的态度因游移在不同身份中而显得矛盾:作为一个儿子,他捍卫父亲的姿态坚决而强烈,而作为年轻人,陆川又表现出一定的理解甚至宽容。“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也很分裂,”陆川轻轻一笑,坦率地说。
“老高真出手了,我心也乱了。”陆川这样描述得知高晓松加入后的心情。得知此信后,陆川曾试图让网站撤掉高晓松宣布开火的文章,却发现早被大张旗鼓地搁在那儿,“就像被强力胶粘在那儿,拔都拔不出来”,“现在想想,我们都是被摁在那里打架给别人看的”。陆川有些自嘲地笑笑。
“在我们种种表达还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敢于挑战现有体制的人,都会受到尊重。当一次社会变动出现时,一批年轻人出来,他要向现有体制索取话语权,他们要寻求代言——不光是产品有代言,对话语的欲望和对话语权的争夺都需要有代言的,韩寒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没有人关心陆天明究竟讲了什么,却都拿出誓死捍卫偶像的劲头和姿态。
“韩寒是个聪明人,会审时。”陆川轻松地笑笑说,“如果单纯从个人角度讲,我不会说韩寒不好,我也是从那个年龄和那个阶层拼杀出来的,内心也有那种挑战权威的冲动。”
与父辈单纯地把网络作为一个使用工具不同,在陆川成长过程中,网络曾是他一个巨大的精神慰藉。“我喜欢电影就是因为我上网写《寻枪》、写《黑洞》,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写,也不知道它们的命运会如何;我很穷,也很绝望,有时中午就吃一点点东西。”陆川经常跑到新浪的“影视论坛”上,因而结识了一大群热爱电影的网友,“他们给我苍凉甚至无望的电影之旅增添了很多温暖”。
那时陆川为自己取了第一个网名:愤怒的猪猪,他和一群网友也时常上新浪网战。“那时候年轻,体力好,可以整夜拍砖灌水,开始拼智慧,然后拼打字速度,最后拼体力。一般来说,谁也干不死谁。”陆川说,我们顶多就是换个马甲,装作另外一名网友“顶”一下自己刚才写的帖子,自吹自擂一下。直到有一天,好朋友王崴的死突然让他意识到网络的虚妄。“我们在网络中通宵达旦争执的真理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年轻人都有一股挑战权威的冲动,我也理解韩寒的这种挑战。”陆川说,对跑到博客上骂自己的文章,他看得也很仔细。“也有一些人实名,我看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子贴着自己照片的博客,骂得挺狠的,但别的文章也写得挺好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偶像‘挺身而出’,也是他们的权利。”陆川笑笑,“如果有机会我们坐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理解我的。”
“我突然发现,对于网络,我不那么从容,有点久疏战阵。”陆川有点自嘲地笑了,他不否认,“不从容”的背后,是名气、地位带来的心态之变,“不像以前那么能容忍,可能好话听多了,有点把自己当回事了。”陆川说,他个人对网络的认识就是这样:说话不被人喜欢,就要被灭。“网络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地方,也许‘陆川’不代表任何社会身份,‘陆天明’是另一串符号,他的社会地位和我们的父子关系都不应该被带进来,这就是真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区别。”陆川说。
陆川的初衷,只是出于儿子保护父亲的本能和冲动;但外界却更愿意把他放在名人+导演的身份上剖析他的话语,其中必然产生的错位与误读也令陆川多少有些尴尬,于是,在博客写了一篇文章后,陆川告别了这场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