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焰(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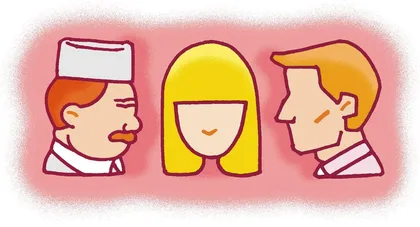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因为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要志向远大,至于哪个学的家从来没好好想过。高考填志愿时我还在琢磨到底哪个学的家既轻松、又自在,出成绩还快。我小姨是医生,她说:“女孩子学医合适,医生永远不过时,还越老越吃香。”这话说得太实在了,再说十几年前的医生也没现在这么大的民愤,我于是进了医学院。
上大学半年我就开始后悔了,觉得学医太苦,跟我妈嚷着要退学。我妈说:“你真要退学了,还不得重新高考呀。”这一说就把我吓回去了。直到现在,我还不定期地做备战高考的梦,据说做这种梦的人很多,有专家分析,这是因为现在的人心理压力大,太焦虑造成的。可见高考带给人的阴影有多大。因为害怕高考,我只好咬着牙读下去,到后来,也能拿个奖学金,评个优什么的。感觉就像别人给自己介绍了个对象,看着还行就结婚了,婚后才发现了解不够,想离婚又缺乏勇气,就这么凑合着,时间长了,倒也生出感情来。
大学后期经常待在医院里,看见总有些衣着光鲜的男女穿梭。他们谈吐优雅、举止得体,医生对他们也很客气。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叫医药代表,工作竟然是“指导医生用药”的。那时的医药代表不像现在这样不招人待见,一出口,东家都是“辉瑞”、“默沙东”这样的顶级大药企。十年前,外企还是很牛B的字眼,充满了神秘与诱惑。我当时甚至想,我可能还不够格去做这种工作。
我毕业以后去了一家很大的医院,有多大?我觉得在广州可以排进前三名。可我很快又后悔了,因为和读医的辛苦比起来,做医生的辛苦翻了N倍。且不说工作有多忙,光那种心理压力就受不了。我们那时急诊呼叫的铃声用了一首很温情的曲子——《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不做医生已经好几年了,可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有一种站起来就往跑的冲动。医生的收入不算低,但也没外面传的那么吓人。像我们这样的小医生,年资低,工资和奖金的级别也低,又没机会收红包和回扣。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形容是:做得像孙子。这个比喻相当贴切,我个人认为。
我那时总想跳槽去当医药代表,那时的医药代表还比较光鲜,而且收入很吸引人。可家里人老劝我:熬吧,熬吧,熬个十年八年就出头了,而且会越来越好。后来出入医院的医药代表越来越多,有外企的,也有国企的,反正他们没怎么指导过我用药,实际上,我也没见过他们指导过谁用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内容已经可以更改为:陪重要的医生聊天,并帮他们办事兼找乐子。“重要的医生”有一个简称叫“VIP”,有一次有位代表来找某VIP,VIP丢下一句“你在外面等一会儿”,就不见了。这“一会儿”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我见这位仁兄已经等得面带菜色,便让他进来坐,还给他倒了杯水。他大概心存感激,送了我一份小礼物,又爆了点“坚料”(广州话:内幕消息)。他说他们公司周末请几位VIP去度假村休假,到了晚上,VIP们提到找小姐,可那个度假村不提供这项服务。深更半夜,只好打电话动用黑道或白道的人脉找来几个,由于这个日程外的安排,他和同事也不敢睡觉,在外面打牌,等着小姐们出来好买单让她们走人。我听了惊得笔都捏不稳,哼哧了半天才说了句:“这……有点……那什么了吧?”他看我这样,哈哈大笑:“话你知(告诉你),只要肯提要求,事情就好办,就怕不提要求,那就没法下手。”
后来我就不想做医药代表了,我见过有VIP拿了别人的好处,又背地里骂人家是“高级乞丐”。我想我确实不够格,因为这是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得需要多强韧的心理素质啊。
除了平时的工作,还有一样让我头疼的就是写文章,要写文章就得搞科研,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啊?可明明有人进出两趟图书馆,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呀。我心里很着急,有空就跑图书馆,去了好多次也不太会把里面的资料整合成自己的。有时去了,看见正好来了新杂志:《译林》、《青年文摘》什么的,就把正事给忘了。
我现在的工作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医药代表。不过,不管我做什么工作,总得生病,家里人也会得病,所以我和医生扯不清干系。与普通患者比起来,我觉得比较幸运,因为我知道谁是真正的天使(得承认,这样的人也不少),求医问诊就很有针对性,少走很多弯路,“看病难”的体会没那么深。
另一方面,和医生比起来,我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不说别的,我只有在不做医生以后才享受到完整的黄金周长假。刚开始很不习惯,乍一下多出七天不用干活,不知该如何打发。而且女人爱漂亮,可当医生又不能太讲究。留着披肩发、穿着细高跟去上班不是不可以,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就等着瞧吧,给病人做心肺复苏,估计做完也就和贞子差不多了。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肯定实现不了了,倒也不觉着失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中间人,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普通患者,更不是医药代表。既没有普通患者“看病难”的烦忧,也不用像医生那样竹影青灯地熬年头,更没有医药代表人前笑、人后哭的悲凉。想到这,简直有点劫后余生的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