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非洲(37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袁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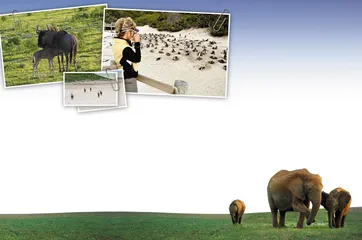
伊托沙草原上的辩证法
离开辛巴部落,我们的探险小分队继续向东。我明显感到距离非洲的西海岸越远,草就越绿,树也越高。据小分队的司机兼导游麦克介绍,受寒冷的大西洋季风的影响,非洲西部地区的降雨量很小。但今年这一地区的雨季出奇地长,雨量也是近几十年来最多的一次,所以许多原本一片黄土的地方现在却是绿油油的,枝繁叶茂。
我们的奔驰卡车开了一上午,终于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伊托沙国家公园(Etosha National Park)。这个公园其实就是一个占地23175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共有114种哺乳动物常年生活在这里。保护区内的大部分地方是不对外的,开放的这部分区域内有几条土路,按规定游客只能坐在车子里沿着规定的路线边走边看,但绝对不能走出车子。这样的旅行方式英文叫Safari,其实这个词原先是狩猎的意思,可现在意思完全变了,别说朝野生动物开枪,就是大声喧哗吓着了它们,都会被管理人员驱逐出境。
伊托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白色的干河”,因为平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白沙,平得像一张纸。可那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大片大片的草原,偶尔看到几片灌木丛也相当低矮,不到2米高,动物们无处可藏,非常适合游人观赏。最先被我们发现的是一群跳羚,这种体形优雅的哺乳动物跑起来一跳一跳的,速度奇快。接着我们又陆陆续续发现了条纹羚羊、黑牛羚、斑马和长颈鹿。它们不是正在吃草,就是正在喝水,很少见到真正闲着没事干的动物。今年雨季大量的降水使得伊托沙草原上到处可以见到浅浅的小水洼,这些草食动物们不需走远就可以满足胃的需要。
“它们多幸福啊。”一个小姑娘小声说。她的话立刻引来了一片附和声,确实,在我们这些习惯了十几平方米小卧室的城市居民看来,这里无边无沿,阳光充沛,到处是现成的食物,到处是游戏的乐园,在这里生活一定很惬意。可我仔细一想却发现了问题,这些动物们为什么总是在不停地吃啊喝啊呢?显然它们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草这种食品不好消化,绝对比不上既好吃又营养丰富的肉,真正幸福的动物应该是那些吃肉的家伙们。

“我们要看狮子!我们要看猎豹!”另一个小姑娘悄悄发出一声感叹。看了两个多小时的食草动物,大家都有些厌倦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不会陪你玩,不会为了拍你的马屁而做出任何谄媚的举动。也许,人类对小猫小狗的喜爱本质上满足的是人类自身对权力的追求,而在伊托沙这样的保护区内,人和动物是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主人。
100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在伊托沙看到的不是野生动物,而是猎物,手拿猎枪的“文明人”在这里找到了当家做主的快感。非洲英语其实不常用Safari这个词,他们习惯用“Game”,这个词的本意是游戏,在非洲英语里就变成了打猎的意思。“Game”甚至可以用做名词,意思是“野味”。词义的变迁准确地反映了当初白人对待这些野生动物的态度,它们是游戏的一部分,是棋盘上的棋子,娱乐的工具。于是,非洲大陆上的野生动物数量锐减,象牙和动物皮毛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欧洲,成了某些人炫耀财富的手段。这种做法可以从欧洲人的信仰中找到根源,他们认为世界分成三等:上帝、人类和自然,人类只有对上帝是需要敬畏的,而大自然则低人一等,理应服务于人类。

可对于土生土长的非洲本地居民来说,这些野生动物和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不过这也不能说明黑人天生就具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要知道,当初强大的祖鲁国就有用野生动物祭祀祖先的做法。黑人之所以比白人更加尊敬野生动物,主要是因为黑人掌握的打猎工具太过原始,在聪明而又强悍的非洲野生动物面前没有太大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如此大量的大型哺乳动物,与非洲黑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长期共处有很大的关系。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野生动物和人类共同进化,逐渐适应了人类的存在,懂得如何躲避人类的围捕。相比之下,其他地方的动物就不那么幸运,它们第一次面对的人类就是从非洲迁徙过去的掌握了高超技巧的猎人。于是,在过去的10万年里,世界其他地方有79%的哺乳动物灭绝了,而在非洲这个数字是14%。
 ( 克鲁格国家公园 )
( 克鲁格国家公园 )
“那么如今这些动物见了我们的车子都不躲,岂不是要遭殃了?”有人问麦克。
“不会,这里已经建成了保护区,从今以后再也没人敢在这里打猎了。”麦克的这个解释很值得玩味,因为当初在非洲建立动物保护区的想法反倒是源自白人。非洲最早的动物保护区是1898年在南非建立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这个保护区的发起人克鲁格以及后来的多位领导人都是白人,正是由于这些具有远见的白人的倡议和管理,才使得非洲的野生动物得以在保护区内延续生命。如今仅南非一个国家就有470个大大小小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种濒危的非洲白犀牛就是因为在南非的一个动物保护区得到了保护,才不至于灭绝。
 ( 黑羊羚 )
( 黑羊羚 )
“不过,非洲的很多保护区都是非洲原住民打猎的地方,设立保护区剥夺了这些人的生存权。”麦克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现在有很多保护区开始让原住民自己参与管理,旅游得到的钱也归他们所有,津巴布韦就实行了一种名为‘自然财富共同管理’(简称CAMPFIRE)的计划,让原住民从动物保护中得到好处。其实动物保护是离不开原住民的,他们熟悉动物的习性,比如非洲的豹子一般人无法靠近,只有桑人才能够走到距离豹子10米远的地方向它们发射麻药针,没有桑人的帮助科学家根本无法对这里的豹子开展科学研究。”
“快停车!”一个小伙子打断了麦克的介绍,“我好像看到了一堆骨头!”麦克把车子倒回去,果然在路边发现了一堆尸骨,皮毛还没有完全腐烂,阵阵恶臭不一会儿就充满了整个车厢。“这是大象的尸体,大概死了不到一个月。”麦克看了一会儿,肯定地说:“附近的狮子们肯定饿不死了,今年雨水多,它们的日子可不好过。”
据麦克介绍,狮子一般不轻易发动攻击,因为非洲的草食动物都已经学会了怎样和狮子周旋,要想抓到一头羚羊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旱季时候草料稀少,很多动物都吃不饱,自然也就没力气跑,狮子们就比较容易得手。另外,缺水的时候动物们都会到固定的几个水坑饮水,这也给了狮子打埋伏的好机会。“这地方缺水是常态,雨下得太多了其实不是什么好事。”麦克继续介绍说,“比如很多植物的种子都要经过一场大火后才会发芽,老的草不死,新的草就不会长出来。死亡其实是大自然的一种正常现象,就像这头大象一样,它的死反而会养活一些别的动物。另外,弱者的死其实对整个种群是有利的,不适应环境的基因就是这样被淘汰掉的。”
看来,不光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非洲也不相信。人道主义在这片荒蛮的土地上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非洲之王
我们在伊托沙公园里转了整整一下午,却没有看到一头狮子。雨季不但不利于食肉动物的生存,也不利于我们这些游客。眼看太阳落山,只好收兵回露营地。下车一看,车头粘着100多只蝴蝶的尸体,白的红的黄的花的,甚是好看,看来在非洲采集蝴蝶标本根本不需要网,开车出去转一圈就齐活儿了。
等大家手忙脚乱搭好帐篷,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打着手电摸进厕所,一盏孤灯周围聚集了十几只大蛾子,翅膀击打灯泡的声音听了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厕所是坐式的抽水马桶,很干净,但我却发现地板上有好几个叫不出名字的爬虫在找吃的。其中一条黑色百足虫足有15厘米长,1厘米宽,比中国的蚯蚓还要大。我坐下没多久,就听到蚊子们发出战斗号角。非洲所有动物的个头都比一般的大,只有蚊子是例外,它们的体形和中国蚊子一样,但攻击力十分强大,一般的驱蚊剂根本挡不住它们。我一边不断地拍打,一边盼望墙上那只大壁虎能有所作为。它显然没有听懂我说的话,趴在墙上一动不动。
晚饭是在黑灯瞎火下吃的,大家都饿了,一阵狼吞虎咽。突然一个苏格兰小姑娘惊叫起来:“哎呀,我刚刚吃了一个蛾子!”原来我们吃饭时候蛾子们也闻到了香味。她男朋友满不在乎地说:“不错啊,蛾子可是富含蛋白质的哟!”
我突然觉得,我们只是这里的过客,动物才是非洲的主人。
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被喊起来,麦克说清晨是看到狮子的最佳时间。不到7点,奔驰卡车便又一次开进伊托沙保护区。晨光下草原上早已聚满了各种羚羊和斑马,但大家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每个人都在养精蓄锐,等着狮子。
我们先看到的却是一头豹子,它躲在一棵小树后面,津津有味地啃着一条血淋淋的大腿。麦克把车子停在几米远的地方,大家举起相机一通狂拍。这时远处跑来两只豺狼,豹子警觉地抬起头,双方对视了一阵,突然那两只个头只有豹子三分之一大的豺狼冲着豹子狂吠起来,那豹子竟一转身走开了。豺狼不依不饶,追着豹子狂叫。豹子依然一言不发,渐行渐远,消失在小树丛的后面。不远处一头黑牛羚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切,好像在看豹子的笑话。看来不仅人类喜欢戏剧性场面,动物也是。
离开豹子不久,我们看到另一辆Safari汽车在远处停下来。富有经验的麦克小声提醒大家,狮子可能就在眼前。果然,5分钟之后,两头狮子出现在地平线上。麦克把车停稳,大家摇下窗户,屏住呼吸,注视它们的一举一动。狮子渐渐走近,母狮在前,后面跟着公的,满头金毛在风中飘摆。狮子不愧是非洲之王,它们仪态威严,迈着沉稳的步子,旁若无人地朝我们这方向走过来。它们身后还有几只专吃残羹剩饭的豺狼,活像几个小跟班。远处一群长颈鹿发现了敌情,全都停止吃草,紧张注视着这群敌人。记得小学教科书上说,长颈鹿之所以长这么长的脖子,是为了吃树上的叶子。可今天我立刻发现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起码在这片草原上,长脖子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长颈鹿尽早发现敌人。
狮子渐渐走近,它们的肚子瘪瘪的,显然有一阵子没吃东西。一群黑牛羚也发现了它们,一起扭转身体注视着这两个不速之客。300米、200米、100米……领头的黑牛羚一转身,带领属下开始狂奔。公狮子发出低沉的吼叫,母狮子突然加快了速度,朝牛羚们冲过去。但她似乎不打算真追,跑了几下就又恢复了平时的速度。黑牛羚眼见母狮子不追了,便也停下脚步,扭过身子继续紧张地看着狮子。等狮子慢慢走近,牛羚们便又开始逃跑,母狮子也又一次假装追了几下,停下来继续走路。如此这般重复了好几次。整个过程中周围还有一群跳羚和长颈鹿,但它们似乎断定狮子不是冲它们来的,只是停下吃草注视着狮子们前进的方向,并没有显出惊惶失措的样子。
“狮子一般不公开追击猎物,代价太大,”麦克介绍说,“刚才狮子是在试探这群牛羚中有没有弱小的个体,显然它们失望了。草食动物们见了狮子也不会一味地跑,只要两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双方就相安无事。”听了麦克的介绍,我意识到,眼前的景象表面上似乎充满杀机,其实光天化日下的猎杀反而并不那么可怕,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双方各取所需而已。“非洲之王”只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谁也不是这块土地上真正的王者。
我进一步想到,非洲其实是有人道主义的,只不过非洲的人道主义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无限制的同情,而是在一定游戏规则下的互相利用。人类本来也是这场游戏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过于聪明了,我们用自己的智慧从这场游戏中脱颖而出,自封为地球的主人,但最后却不得不为了争夺资源而自相残杀,并在屠杀过程中把祖先遗传下来的游戏规则丢在了脑后。(待续)■
非洲的三国演义
在南部非洲发展史上,有三股势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股是最早的白人移民的后代,史学家把他们叫做“布尔人”(Boers)。这些人从300多年前就随欧洲商船从好望角登陆非洲,在南非开垦土地,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Boers这个词在荷兰语里就是“农民”的意思,南部非洲历史上第一种通用语言——“非洲语”(Afrikaans)就是荷兰语的变种。布尔人虽然是欧洲移民的后代,但他们长年脱离欧洲,对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各种现代思潮完全一无所知,《圣经》是他们唯一的精神食粮。
1795年英国人占领南非,开始施行包括解放黑奴在内的新政策,这让布尔人很不快,遂开始了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他们离开海岸,向内陆挺进,一路上看到所有的原始村落都一片狼藉,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血腥的战争。布尔人以为当地黑人平常就是这样打打杀杀的,因此更坚信黑人是未开化的原始人,自己为非洲带来了文明。其实他们只不过正好遇到了一次非洲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史学家把它叫做“迪法盖”(Difaqane),意为“强迫迁徙”。这是由位于南非东南部的祖鲁国(Zulu)发起的一场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祖鲁人兵强马壮,当时的祖鲁国王沙卡(Shaka)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其成员不准结婚,专门打仗,所以祖鲁军队所到之处所有的原始部落就都遭了殃。
后来史学家对祖鲁国的这次大屠杀有很多不同评价,有人甚至认为沙卡是为了统一非洲的黑人部落,共同对付白人统治才这样做的。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白人进入非洲的时期非常类似于我们的秦始皇时代。
1838年,北上的布尔人和祖鲁军队干了一仗,结果大胜。布尔人认为是上帝保佑了他们,因此更骄横跋扈。其实,用火枪对长矛,岂有不胜之理?英国政府一开始对两强的争斗采取了放任态度,毕竟布尔人是信基督的白人后代。可后来眼看局势控制不住,便出兵干涉,最终打败了布尔人,取得了对南非的控制权。当然那时的英国政府也不是什么黑人的福音,只不过他们比保守的布尔人进步一点点罢了。
这三股势力的影子至今仍在。如今的南非就是保守的白人、进步的白人(包括来自国外的进步势力)和黑人这三方势力角逐的战场,所有矛盾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