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校园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唐克扬)
 (
20世纪20年代末的燕京大学校园 )
(
20世纪20年代末的燕京大学校园 )
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就栖居在昔日燕京大学的校园内,是为“燕园”。据说,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设计纪念标志的设计师以为燕园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那个“燕园”(如此,和清代叠山名家葛裕良参与经营的常熟“燕园”则取意相近),便设计了两只翩翩的燕子组成“北大”图形,这种历史误读很能说明某些问题。
北大校园的主要园林区的格局,在1952年之前就已经大致成型。
燕园中命运各异的园林构成了别样的历史层次,个中有趣的是,人们越是对这些园林投以关注,越是“保护”,它们就破坏得越彻底。2001年竣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重修朗润园工程,固然是一件挽救倾颓文物建筑的盛事,可它也为50年来未曾大举动土的朗润园的最终改造开了个头。
作为一个物理场所,“校园”对于北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1919年,位于城内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开始在西直门外寻找它的新址,远离北京城的燕大海淀校址其实并非它的最优选择,多少是不得已为之。反过来,蔡元培曾有将北大迁到西郊的想法,而当时北京政府也曾经提议建一条自北京去西山温泉的铁路,第一站就是今天的燕园所在地。当初北大和燕大没有能交换位置,而最终在1952年北大和燕大融在一处。不光燕大的师资力量,如费孝通、侯仁之等,都传承在北大的血脉中,燕大的标志建筑也为北大所继承。如今人们说起北大来,是西校门——燕大校友门,未名湖畔的塔影天光,相反,倒是马神庙、沙滩、红楼这些个老北大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渐行渐远了,一个地处围墙之内,有藤萝环绕绿荫缭绕的北大形象已经为人们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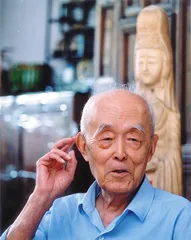
北京城内沙滩的红楼,和今天北大的距离,远远不是一小时公共汽车,40分钟出租车的距离。如果说老北大浸没于慷慨激昂的历史波澜中,新北大的校园则代表着另一种理想的学院生活的氛围。新北大的自成天地,却正是昔日国立大学的教育者们所诟病的地方。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说过,作为旧日教会大学的燕大,因为对中国社会没有使命感,所以不必离闹得天翻地覆的北京城太近。
1918年,美国建筑师墨菲规划燕大校园时,文献中但见“校舍”,“校址”,而不见“校园”。而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校园”,除了有一块足够大的地皮,还要有足以感兴的景致和史迹,最后,还要有一些随适超脱的心态,有青春蓬勃和温文儒雅的园居者和临流赋诗的情致。在“燕园”,这些条件碰巧都具备了。
 (
20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时期的未名湖
)
(
20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时期的未名湖
)
北大居于“燕园”的意义最终还是落实在“校园”中。
这个园居的第一点要义在于它使得学习、美育和生活合而为一,这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就是孔子所赞许的以自然生活而教化的理想教育境界提供了一种可能;其次,在校园中,传统意义上的耕读和雅集并行不悖,燕大时就有农学院,苗圃和试验田,以及自己从事后勤供应的传统,1945年后生活转向困难,燕大学生更是吃上了自己种植生产的花生酱等副食品。
1952年后,北大不仅继承了燕大校园,还以此为基础兼并了几乎所有周边优势区位的土地,像朗润园东部的新建筑群和燕南园南的新宿舍群,乃至近年来正式包入校园的成府部分土地。这样就使得先前的数个小园合并成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新“燕园”。自此以后,北大介入政治的热情已与以往不同,但它的学府气氛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浓郁。
燕园规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产生出一个被不折不扣执行的“总体”规划。在燕大阶段,由于精明的传教士们的坚持,墨菲宏大的古典主义格局被打了大大的折扣,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甚规则的布局,即使是在建国以后,行政命令的作用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或许因为北大总体上有一种多样化倾向的缘故,新校园的发展虽然迅猛,但对历史区域的侵扰并不是十分显著——至少到近年来都是如此。
历史上,即使是未名湖这样尺度的“公共”景观,也是多种利益平衡的结果,而非设计师一厢情愿的纸上功夫,最终,人们没有期求对这种景观做出明确的定义,是以“未名”为其名。1952年之后,在新建设的实际功用和整个校园的和谐美观方面,北大校园建设部门寻求了一种最大的平衡,亦未去刻意寻求一个新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类似于朗润园那样的历史区域之所以能保存完好,除了那个时代动迁的特殊困难之外,多少是因为它没有被寄予一个过于高扬的定位。
“燕园”因缘际会而独具的传统园林模式,未必是所有大学新兴建设的上选。然而,“校园”服务于教育的终极目的,以及它天然具有的和社会功利的距离,决定人们需要为它在一般的规划发展模式中留出些许生存空间,允许它在微观的尺度上保留局部的多样性和个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单纯历史保护的意义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