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的经济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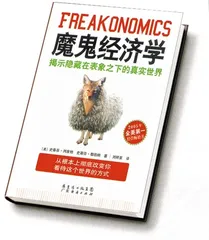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它的美妙就在于它不相信所有美妙的宣示。它把道德理想伦理教条丢在一边,将人还原为势利小人,寻找他们的趋利动机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它的解释因此非常有力。
史蒂芬·列维特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曾获2003年美国克拉克奖(the John Bates Clark Metal),这个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美国40岁以下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自称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同行相信他有一颗最有趣的脑袋。他身体瘦弱,学问却做得一点都不软,特别飞扬跋扈。去年他与记者史蒂芬·都伯纳合作,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在美国大卖。林行止先生曾撰文详细介绍过此书。今年,美利坚热炒势未消,中文版新书又登场(刘祥亚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列维特的研究要挑战不少道德成见,他在书里反复说:“‘魔鬼经济学式思维’并不会涉及到任何道德层面的问题。如果伦理道德代表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但他最主要的敌人是conventional wisdom,中文版译成“传统智慧”,我想稍微马虎点可以译为更通俗的“常识”——通常的见识。“常识”表面上不错,实际上不对。“传统智慧的形成往往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虽然通常很难看透,但它们仍然可以被推翻。”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社会,复杂事物之上还包裹着很多“常识”的欺人之谈,蒙蔽了公众的视界。列维特的方法是,在日常生活不疑处设疑,提出别出心裁的好问题,然后收集准确的数据,做严格的分析——人会撒谎,数字不会。《魔鬼经济学》回答了六个精彩的提问: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三K党跟房产经纪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才能成为完美的父母?名字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吗?列维特的结论跟常识大相径庭。结论并非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读了这本书,可能会像作者那样在生活中提问题,想问题。
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由他的旧书《被调整的目光》扩写而成,起码有半本书是新的。姜兄现在虽然贵为银河证券上海总部的党委书记,依我看那只是他的“外王”事业,他天生是个“内圣”,更合适搞研究做学问谈想法。《天公》一书,不足20万字,至少三项考证足以称道:第一,他推翻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1890年出土的成说;第二,他纠正了张爱玲自述祖父张佩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之误,“七家坨”应该是齐家陀;第三,他证明中国近代史上大事件“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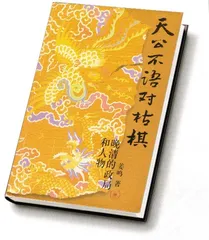
上海博物馆看到姜鸣考证后已改写展览厅内的说明牌。张爱玲早已往生,无法读到姜鸣的指正,自然也没有回应。不过张爱玲对至亲的祖父张佩纶的事迹都不甚了了,她对男人的了解肯定很糟糕,无怪乎她一辈子遇人不淑,嫁过两次都凄惨收场。她一生的错误说不定就是从齐家陀误做七家坨开始。
对康有为巧言令色、言大而夸的“公车上书”,史家多有争论,但立论的优势和考证的优势都在姜鸣一边。其实姜鸣还是相当厚道,对康有为编造历史做了一个相当高调的解释:“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甚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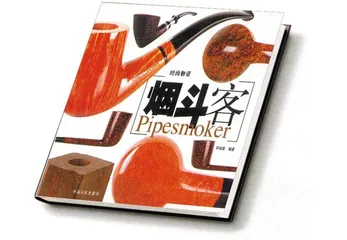
我以为对康有为的要求还应该高一点。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起于民间第一代改革家,写中国改革史,第一人就是他。这些最后推翻皇权礼教传统,取而代之的改革者,考虑到自己将身系天下民心,理应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不济也要做个贤人。但康有为开启了一个很王八蛋的传统,就是改革可以不择手段,不必在乎公道私德。从此以后的人心大坏,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大。
我看重《烟斗客》(邓程君编著,中国宇航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因为书里有很多作者自己的经验,并不是东拼西凑的杂烩。中国人能写出自己的吃喝嫖赌抽,说明中国已经开放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