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在新闻和小说之间
作者:孙若茜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for her polyphonic writings a monument to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10月8日,白俄罗斯女记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上是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
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成为诺奖的热门人物,已经有3年时间。2013年诺奖公布的前几天,这位白俄罗斯女记者的名字突然间出现在几大博彩公司赔率榜单的前列,并最终进入了诺奖官方的决选名单。今年诺奖开奖前,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赔率榜上已位列第一,力压常年陪跑的村上春树。她最终获奖的结果,并不意外。
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纪实文学,每一本书都要历经数年的采访写作,从80年代开始写书到现在,已经出版的也只有5本,它们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关于“二战”、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War's Unwomanly Face,曾译为《战争中没有女性》),《我还是想你,妈妈》(Last Witnesses,曾译为《最后的见证者》),有关苏联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呈现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其最新的作品《二手时间》也即将被推出。
1984年2月,苏联大型文学刊物《十月》刊出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好像是作者为了加以强调才故意为之,书的内容恰恰与书题相反,在这本题为“没有”的书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数百位曾经参加或被卷入“二战”的苏联女性。
谈起这部作品时她曾说:“超过100万名苏联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前线参加战争。她们的年龄从15岁到30岁不等,精通各种军事专业,成为飞行员、坦克驾驶员、机关枪手、狙击手和其他各种人员。她们不像在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只做护士和医生。然而,胜利之后,男人们都忘了这些女人。而女人得打另一场仗。她们藏起军人身份证和伤员症,因为她们想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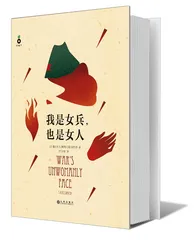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在她的这本书中,女军人谈论战争的那些方面,男人从来不提。男人更爱描述他们的英雄业绩,晒出军功章,而女人则谈论别的。例如,路过一片覆盖着尸体的田野是多么可怕,那些尸体像土豆撒满一地,全都是非常年轻的人。你为他们感到难过,不管他们是俄罗斯人或德国人。
写作从1976年持续到1981年,进行得很慢。如果是一本纯采访式的书,应该很快就可以写完。但这本书的关键完全在于其观点。阿列克谢耶维奇要找到的不仅是主人公,还有她自己,她必须要弄清自己在追求什么。因为单纯地去记录谈话似乎与艺术并不相干。有大概两年的时间,她所记录的话,远不如思考的事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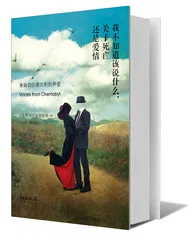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开始写书前先后在多个报社和杂志社任职过,但她始终对日常的报道不感兴趣,常规的新闻空间让她感到狭窄。“信息让我厌烦。”她曾这样说。她不想将自己困在新闻专业里。因此,当她开始写书时,虽然依靠新闻专业收集信息的素养,但所使用的文体,微妙地把持在新闻和小说之间,是一种将内在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的文学路径。
这样的文体要求她,当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事时,她必须将一切听进去,而后使自己消失在其中,并成为那一切。她形容那就像是一种非物质的转化。与此同时,她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她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节奏,当话题涉及人的内心生活时,节奏最为主要,因为那是灵魂的标记。
其次,是资料的筛选,有关人生的细节和详情。有时,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一切。收集80页的资料,最后可能只留下半页,和一个人谈话一整天,可能最后只用了一句,比如:“我很小上了战场,经过战争我长大了一点儿!”每次倾听别人的陈述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这贯穿她此后多部作品写作的始终。
她的第二部作品《最后的见证者》,依然聚焦战争,是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成年人的战争和战争给家庭与人们造成的不幸。虽然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很多家人都死于战争。外公死在布达佩斯城下、祖母在游击队遭封锁时死于饥饿和伤寒,两家远亲被法西斯烧死在窝棚。家人告诉她的故事,甚至比后来记录在她书中的,更令人震惊。这一切都给她的童年带来莫大的震动。于是很早她就开始关注那些没有被关注的历史,以及在晦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
此外,在绝对军事化的社会中,军事文学是必需的,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文学。它们偏爱讲述英雄,谈论人在前线动用体内的潜能变得比原来的自己更加高大。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恰恰认为,人在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低于人,且已不知低到了何等的边缘。因此,她的书中从不选用特殊的英雄人物——著名的将领或者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从未令她产生兴趣。而对于那些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很少讲到的,人在战争中、在丧失理智时会变成什么样,则用尽了笔墨。
书中有一位妇女讲其全家怎样被德军烧死的故事。那位妇女回忆了他们最终俘虏了德国人并用通条将他们戳死的情景。当看到那些俘虏在经受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而眼球爆破时,她说自己感到了幸福。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问她是否现在还做着别人眼珠爆破的梦,因为她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没有任何权利责备这样的妇女,毕竟自己的家人没有被烧死,婴儿没有被杀害。
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意识到,如果她再次写作,她会提那样的问题,会写这样的事。她希望探视人更深的本性,深入到朦胧,深入到下意识中。这种追求直接反应在她第三部有关战争的作品《锌皮娃娃兵》里。它讲述历时10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全书由几十篇与战争相关的人进行的陈述组成,包括参与这场战争的官兵以及战争受害者的遗孀或者他们的母亲们所讲述的故事,以相当数量的“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一位母亲的话”告诉人们它是哪种战争,当时人们怎样想,他们怎样互相杀戮,又怎样绝望地挣扎求存。
“作者是从妇女的角度在进行心灵的挖掘,这是心灵活动的文献。作者努力将人心掏出来展示给读者,让他们看看人心在战争中是怎样跳动的。”其中文译者、翻译家高莽谈道,“如果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前两部作品描绘的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壮丽的理想和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即苏联时代军事文学的模式,那么,从《锌皮娃娃兵》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二手时间》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二手时间》
让阿列克谢耶维奇产生写作《锌皮娃娃兵》的愿望,来自她对于以男性观点看待战争的抗议。有一次,她去到一个村庄,那里的公墓安葬着牺牲的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她发现,那是成年人串通一气的行为。而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因为妨碍别人发言,小姑娘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她明白,在这里,只有这个姑娘是正常的人。
而当阅读大量的军事文学时,她发现了类似的“串通一气”。她认为,那些对战争和杀人加以浪漫化的书写都是来自男性的本能。男性对武器怀有隐秘的赞叹,因此在使用武器时不会考虑到战后的问题。而让女人杀人则相对困难,因为她们本身创造活的生物,与活的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直到写作了这本书,阿列克谢耶维奇才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来的体制,是独立的人了。
然而,当这本书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评论走向了两个极端。反对的声音中,一些人甚至将她告上法院,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故事的讲述者,他们向法官抗议——“我没有这么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此的解释是:“其实他说了,不过我从中提炼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意思。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比如,受访者也许依照其意识所习惯的,希望从自己讲的故事里让对方得出某种英雄行为的看法,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提炼出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怎样被变成了一个杀人犯。
她的研究对象是感情的历程,而不是战争的历程、不是事件本身。因此,她真正感兴趣的部分,是人们有意无意间隐瞒起来的细节,她将这些资料集中起来,以形成时代的形象。“我从不强制资料——我先是找到它,摘录它。应该说——是资料形成我和我对世界的态度。否则的话,我就会重复自己,到处撞到自己身上。问题不在于浓缩而在于筛选。我进行筛选,有的东西会放弃。我的概念仿佛就隐藏在这种筛选和剪辑过程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谈到,她自己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写一本有关灾难的书。切尔诺贝利爆炸发生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最先冲到废墟上采访的人之一。但了解到的信息并不能让她得到满足。“纯粹的政治或科学解读远远不够,没有人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她突然意识到,她不敢坐在青草上,不敢吃苹果……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住在含毒的污染地带,她身边的人都开始患病,母亲双目失明,患甲状腺癌的孩子多达二三百人,而过去只有七八个。来到某个村庄,村民已经搬空不说,连同茅屋、水井、圣像都被埋了起来,很快,这些都变得司空见惯。于是,人们开始等待双头的雏鸡和无刺的刺猬出现——在科技灾难造就的那个将疯狂、荒唐视若平常,花朵盛开却没有味道的地方,一切悲伤、带着刺痛的未知都是可能的。她开始收集资料。与以往的写作相当,她采访超过500位目击者,对每个被采访者都录下超过4卷录音带,记下100多页的笔记,这花费了整整10年。
最新的作品《二手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标靶从战争、事件中移开,投射到时代。1991到2012年,她为这本书所做的采访一直在进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写作的方式依然没变,人们谈论着过去和现在,爱恨交加或冷漠。
早于诺奖之前,她的作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且在世界文坛屡获大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等。同时,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她的独立新闻活动也曾受到政府限制,《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战争中没有女人》)曾被苏联有关部门大幅删节后才得以出版,直到2013年的修订版,作者才将删节的部分补充回去。争议颇多的《锌皮娃娃兵》也曾被列为禁书。1992年,她在政治法庭接受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她还曾被指控为中情局工作,电话遭到窃听,不能公开露面。2000年,她受到国际避难城市联盟的协助迁居巴黎,2011年才回到明斯克居住。
在一篇访谈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被问道:“你撰写这些著作,自己居然没有变成疯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心理无法承受的。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写完你的任何一本书,肯定得进精神病院。你不是录音机,你是个活人,你得把所有一切从心里过滤一遍。这些可怕的资料,会不会改变你的心灵?”她的回答是,像切尔诺贝利,它既令人丧失理智,又能提供观察事物的深邃的哲理观点。“我并不只是在收集一些可怕的事情。”同时,她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是独自行进的,我完全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 小说锌皮娃娃兵作家二手时间文学奖军事历史战争诺贝尔奖新闻阿列克谢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