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与舞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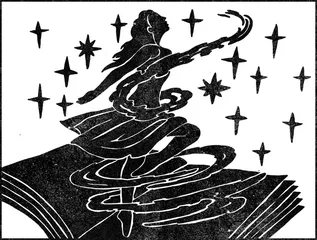
文 / 心里美萝卜
我曾有个签名本,里面有不少足球运动员的签名,都是十年前妈妈认识的一位体育记者好心为我收集的。但我天生不是做“粉丝”的料,只草草翻过一遍(我记得第一页是曲波签的),几次屋内扫除后就再不见其踪影。
辜负了别人的好意,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是看到很多时候明星签名真是得来不易。也是在大约十年前,我的同桌陪另一个同学逃学去看某乐队的演唱会,二人午饭时间就鬼鬼祟祟溜出了校园,直到晚自习临近结束才又猫着腰钻回了教室。仅半天前都还不是该乐队歌迷的同桌,此时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她如何在大雨里(场馆外?酒店外?我也不记得了)等了几个小时,最终等来了偶像,拿到了偶像的亲笔签名。此时周围同学都来围观那已被当作神迹的笔迹,观摩了好久也没认出横竖撇捺,可她的幸福表情还是把做了一晚上化学卷子的我感动到了(那时我逃课也只会往图书馆躲,但花半天时间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真不是什么能让你精神为之一振的事)。
被我当作过偶像的人中其实也不乏音乐细胞的,可惜巴赫、莫扎特他们都已不走穴多年了,我淋再多次雨也等不来他们的亲自接见,不过我至今记得小时候读音乐家传记时的失望心情——传记家们不是铁了心要将流水账记到底(有时真是连账单都不放过),就是小报记者附体,凡事大胆猜想,却不一定小心求证。当创作者创作出打动你的艺术品,你或许会不禁想要了解有关他的一切,有些人甚至会想搜集、拥有有关他的一切,然而即使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喜欢听别人的好故事,人世间再多事也不过那么点事,也许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就在于他们可以超越俗事琐事的腐化,不被人生的种种偶然所羁绊。
“身体合乐轻摇,明亮的一瞥/我们怎能分辨舞者与舞蹈?”这是叶慈《在学童中》一诗结尾的话。花甲之年的诗人重回校园,他在孩子们稚嫩面孔上试图想象自己与心爱之人小时候的模样;他感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这些古希腊先哲们早已归于尘土,其学说是否流传依旧;他又想到修女崇拜神像、母亲宠爱孩子,但神像终究只是石头刻出的偶像,而亲生骨肉终究会独立成人——比起学术与文字的传承,许多看上去实在而生动的事物反倒是稍纵即逝的。舞者只存在于舞蹈之中,作者则活在作品里。所以在诗的末尾,叶慈由伤感转向释然,生命就算不如期望的长久,诗人最终会通过他的诗继续与后世对话。
作者与作品同生,舞者与舞蹈同灭,而名者实之宾,不管你是“超白金一代”还是“摇滚天团”,如果我是球迷我会看你比赛,如果我是歌迷我会听你唱歌,到此为止,仅此而已,我不关心你的花边新闻,也懒得供奉你的笔迹。 故事生活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