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消失在世上》:用天真的眼睛看世上的时光
作者:孙若茜 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当小说《一个人消失在世上》(Mr Gwyn)在意大利出版时,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在读者见面会上朗诵了它的开头,然后说:“你们无法想象,我把这段写了多少遍,我本来想把那些版本都带来呢,但后来想想算了。”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作品销量上百万册的作家格温先生在散步的途中突然决定封笔。于是,他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罗列出他许诺再也不做的52件事情,其中包括了在学生面前假装自信、跟那些实际上很鄙视自己的同事假客气等等,最后一件事情是:写书。
他意图结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是彻底从过去的生活中抽离。旅行、不回电话……当这些人们常用来自我消失的手段被陆续使用后,格温开始寻求新的职业——他希望成为一名其工作中包含耐心、朴素和庄严以及神秘气息的抄写员。
在寻求与之对应的实际工作时,格温在一家画廊获得了灵感。他在画中看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时间。“他没有考虑到画家的技艺,他也不觉得这位画家的技艺很重要。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目标,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最终到达的那个目标,画中那个留胡子的人被画家搬回家里。他觉得这非常美好。”他决定了自己新的职业:写画像。
“格温先生停止写作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一直最感兴趣的是: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人们把自己所爱的东西重新放在一起的方式。”正如巴里科所说的那样,他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主人公的新职业:格温在还不知道工作的方向和结果时,已经事无巨细地着手于新工作室的方方面面,比如,它需要“像一天中的光线一样,从早到晚都在变化,连续不断,但又让人无法察觉的”优雅的背景音乐,需要一种发散着“天真”的光的灯泡,并且,它们要在760个小时至830个小时的寿命间陆续地熄灭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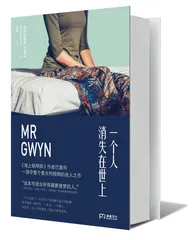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巴里科 著)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巴里科 著)
巴里科对此解释说:“在小说中,格温先生去买那些灯泡时,他对那个做手工灯泡的老人说:我要一种‘天真’的光。我对文学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在我的小说中,有很多天真的东西。我说的‘天真’是那些没有被世俗和厌倦污染的东西。”
格温先生要求每位被他写画像的人连续30多天每天4小时全身赤裸地随意地待在他的工作室中,而他,有时在一旁观察,有时则根本不出现。他终于成为一名抄写员,抄写那些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最终,每一幅画像都非常令人满意,自然也令旁观者好奇。但小说的文本中始终没有将它们完整地呈现出来,只是在全书末尾的对话中展露端倪:“他给我做画像时,我读了,画像的最后有一段风景描写。我就是那个风景,我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声音、脚步、气氛,我就是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那种准确让人不安,我甚至就是那风景,我以前是,将来也是。”“我们是整个故事,不仅仅是那些人物。我们是那些我们散步的树林,是骗人的坏蛋,是周围的混乱,是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是东西的颜色、声音,您能懂吗?”
巴里科的叙述一如既往的轻盈且充满诗意。起初,他还设想将小说每个章节的长度都写得一模一样,他希望将讲述的节奏与格温先生在公园里散步的节奏保持一致:缓慢、规律、充满耐心和张力。“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如果通篇都采用这种节奏,会显得沉闷单调。”他说,“幸好我最后改变了主意。”
“我是在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忽然产生的灵感,然后,这个故事慢慢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一本小说的产生,可能是某一天的某一刻,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片段,也可能是一个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场景。我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进行艺术加工,构建情节,最后就是运用自己的天分和手艺,投入写作了。”谈起这部小说的缘起,他这样说道,“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胸有成竹,我只知道有一个人要写‘画像’。我写书的时候,喜欢从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开始写,我脑子里出现了这个‘写画像’而不是‘画画像’的人物,就像我想到一个在邮轮上弹琴的男人,他从来都没有下来过,并且永远都不会下来。这些脑子里产生的想法,最神秘的是我觉得这些人物都很熟悉。”
他所提到的自己笔下“在邮轮上弹琴的男人”,正是那个住在“弗吉尼亚人号”邮轮上,一生在海上往返于欧洲与美洲大陆之间,直到邮轮被废弃、引爆也没有走下船的钢琴天才“1900”。——在吉赛贝·托纳多雷导演的电影《海上钢琴师》1998年风靡全球后,“1900”的故事大概无人不知。电影正是改编自这位当今炙手可热的意大利作家在1994年发表的一部独白剧《1900:钢琴师》,可见,亚历山德罗·巴里科向来是讲故事的高手。
《1900》的故事中讲述的有限和无限之间关系、欲望和现实的各种可能之间的生存困境,始终贯穿于巴里科的创作之中,这部关于格温先生的小说也不例外。但《1900》并不能代表巴里科小说创作的全部成就和至高的水平,他还拥有诸多形式内容上都富有创新意义的小说,比如获得意大利重要的文学奖项“康皮耶罗奖”的处女作《愤怒的城堡》、获得维多雷久文学奖和博斯克城堡文学奖的《海》,以及在2007年同样被改编成电影而红极一时的《丝绸》等等。当然,还有这本2013年写就的小说《一个人消失在世上》。
实际上,写作小说并不是巴里科唯一的职业或说专业。1980年他从都灵大学的哲学系毕业,却凭借自己的另一个音乐文凭成了为《共和国报》和《新闻报》撰写音乐评论、文化批评的记者、专栏作家。1993年,他在Rai电视台主持音乐栏目讲解歌剧。1994年又主持了一档文学节目“匹克威克,论阅读与写作”。同年,他创办专门教授叙事技巧的霍尔顿(Holden)学校并在其中任教(学校的名字来源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男主人公Holden Caulfield)。
2004年,巴里科以现代意大利语译文改编了《伊利亚特》,使其成为口述版《荷马,伊利亚特》,并在罗马和都灵的两家剧场里向听众进行朗诵,他认为这个新版本是“与现代公众的忍耐度相兼容”的,并将这种改编视为艺术品的修复。不止于此,他还策划了一个名为“Save the Story”的文库——请当代优秀的小说家,诸如艾柯、阿莉·史密斯、戴夫·艾格斯等等为孩子们重新讲述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经典故事,其中包括《约婚夫妇》、《唐璜》、《李尔王》、《罪与罚》、《格列佛游记》等等,巴里科让他们以当今的语言和自己的方式进行讲述。重述经典对他充满着吸引力,他甚至将做这件事形容为一种本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说:“我喜欢挑战那些伟大的作品,我推崇万古流芳:这是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开篇时,你告诉我们,格温先生的作品多种多样,这让我想到你。格温先生是否能代表一部分的你?他所追求的生活是否在诉说着你的个人情绪?
巴里科:不是的。实际上,格温先生身上有很多和我不相容的地方。有一些关于对作家这个职业的反思,可以说是出自我,但是他摆脱那种处境的做法,并不属于我,他的选择和我也一点儿也不像。我永远不会停止写作,也不会偷偷写作。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过去的很多作品中,故事都开始于20世纪初,为什么会对书写那个时代的故事有特别的兴趣?
巴里科:我喜欢这种时间差,这能帮助我更好地聚焦我所讲述的故事。我属于那种能看清远处,但是却看不清近处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我很喜欢你在书中营造出的氛围和书写的气质。这是你在写作中格外注重某些元素(比如结构的运用、语言的节奏等等)产生的效果吗?还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巴里科:通常,我会根据我要讲述的故事来选择写作的风格。《一个人消失在世上》的语言很干净,非常清醒和节制,因为格温先生的风格就是这样,他就是那道照亮这个故事的光,一切都通过他的语言得到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用了一种他可能喜欢的风格写了这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就像这本书中的格温先生买灯泡时寻找一种天真的光一样,你在写作中也寻找某种天真的存在吗?你认为什么是写作中“天真”的部分?
巴里科:“天真”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词,因为写作这个职业是那种狡猾动物的职业,但是这个职业里,也有天真的成分,这在写作中,“天真”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几乎必不可少。在每种写作里,都有回忆,通常还有一种怀念——怀念用天真的眼睛看世上的时光。甚至,作家身上的那种自恋,也是一种天真的自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很多作品中,主人公似乎都要去处理身份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比如格温,比如1900,以及他们都在面对一种生活的倦怠感和新的探索。这是你想要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主题吗?
巴里科: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你提出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我书里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很明显,这也是一个一直陪伴着我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始终想要通过作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巴里科:我觉得是“有限”和“无限”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在书中,你唯一提到的作家是波拉尼奥,你和他,或是和他的《2666》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巴里科:很简单,我觉得《2666》写得太棒了。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评论者都将你早期的作品与卡尔维诺进行比较,并认为你是卡尔维诺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你的创作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
巴里科:拿我和卡尔维诺相比,尽管我觉得很荣幸,但我觉得我对文学的看法,并不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我很喜欢他的书,但是有另外一些作家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再谈谈艾柯吧,虽然你们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相同的学术背景、相同的出生地区、相同的职业背景等等,但是在作品的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你怎么看你和艾柯之间的关系?
巴里科:他就是作家中的一个特例。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我不是,我是一个出于本能而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他博学的体现,而我的小说好像是无知的产物,因此我们很不一样。他写的《玫瑰的名字》改变了意大利文学史。我觉得他很伟大。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年前,你曾经策划了“Save the story”系列,此外还将荷马的《伊利亚特》进行了改编。因此我想问,“重述经典”这件事为什么吸引你?现在,你是否还对这样的改写怀有兴趣?
巴里科: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本能。我喜欢挑战那些伟大的作品,我推崇万古流芳:这是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然而,结果可能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这个做法本身是我认可的,是有价值的。这个做法非常有风险,但我认为值得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当今很多作家的写作都会追求技巧,而将故事本身弱化,我认为你所做的重述经典是对于故事性的一种强调,是这样吗?讲吸引人的故事对于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巴里科:有一些伟大的叙述者,也有一些伟大的作家,这两者很难集于一身。当这两者恰好融为一体,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两者兼得,这在我身上发生过一两次,让我写出了一些最让人满意的文字。
三联生活周刊:你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角色,主持音乐节目、文学节目,电影的编剧、制片人,等等等等,哪个是你觉得最有意思的?
巴里科:毫无疑问,是当作家。但是做“霍尔顿”(Holden)写作学校的校长,也是我很喜欢的职业。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前不久刚刚旅行回来,能否谈谈去了哪里以及有什么收获?
巴里科: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我决定给《共和国》报写一份报道,报道一场足球比赛。有人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精彩的体育赛事之一,在博卡(Boca)体育馆举行,是博卡青年队(Boca Junior)和河床队(River Plate)之间的足球比赛。真是不枉此行……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你足球踢得也很好,而这只是你众多爱好中的一项,能谈谈你在生活中的个人兴趣吗?
巴里科:我弹钢琴,但是弹得不怎么样,只是弹给自己听。一有人听我弹琴,我就会出错。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是否在写作新书,能不能对近来的工作有所透露?
巴里科:我才出版了一本新小说——《年轻的新娘》(La Sposa giovane)。现在我正在准备一个剧本,写的是一个名叫帕拉墨得斯(Palamedes)的希腊英雄的事迹:他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英雄,亚该亚人,在当时非常著名,但荷马一次都没有提到他。假如要研究这是为什么,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深度书评文学小说作家阅读人文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