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保守与进步于一身
作者:维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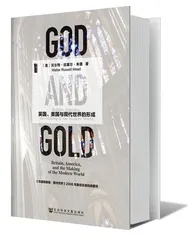 《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米德 著)
《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米德 著)
当弗朗西斯·福山说出“历史的终结”这个词时,在有些人看来,大概就像上帝吐出“要有光”,世界将随之一新——美中不足的是,最好再加上一个修饰语,即“英美模式下的历史的终结”。虽然这么说不免有些戏剧化,但大体而言,这便是《上帝与黄金》所抱有的基本观点。
很少人能否认英国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按艾伦·麦克法伦《现代世界的诞生》所阐述的观点,现代世界中的大多数特性,都得感谢英格兰做出榜样。《上帝与黄金》只是延长了历史回溯的期限,将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归结为英国、美国乃至“下一个英语民族”之间的火炬接力赛。虽然书一开头就承认,“我们胜利了,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错了”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次,但正是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将道德和民主原则引入国际社会”,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常识,即历史潮流长久以来偏向讲英语的人”。
不过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历史系谱中,其开创者并不讲英语。“英美模式”其实是海权强国所建立的国内国际体系,在书中,作者将荷兰体系比作这一操作软件的1.0版本,而英国引入了2.0版本,“二战”后的美国则沿着这一路径更新升级到了3.0版本。他就此说,近400年来海洋秩序的历史可以用10个字母简括:U.P. to U.K. to U.S.(从联合省到联合王国到合众国)。就此而言,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关键点并不在于人们说的是哪种语言,甚至“上帝与黄金”也未必最要紧(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对这两者甚至更狂热),而在于那种海洋体系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自由贸易下的市场体系。
英美模式获胜的原因,在我看来倒不如说是其特殊的有利地理位置。在“上帝”(God)和“黄金”(Gold)之外,应当再加上一个G打头的单词:Geopolitics(地缘政治)。从世界地图上看,美国其实也是个巨大的岛国,它仅有的两条陆地边界靠警察就可维持安全;而美国长期以来的孤立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和英国相同的岛国心态,即专注于自身,远离欧洲大陆的纷争,除非这种纷争将对自己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英美两国在近三四百年来的各次与列强争霸中的确大多以获胜告终(因此越战才格外惹眼),但在此值得补充的是:在英国内战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两国内部的战乱也已告终结。既然对内对外都无须增加大笔军费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对它们而言重要的便在于运用海权力量来保证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而当它们大量对外输出工业品时,这种商业利益便上升为国家利益。其本土几乎不可能受到入侵,这样,“胜利令英国的实力增长,失败也不能危害英国的实力”——这里的措词换成“美国”也一样。
也正是这种地理上安全有利的地位(背靠大陆的荷兰显然就不如英美安全,后来屡次遭到法、德等国的陆路入侵),使英美社会得以保持某种稳定的连续性。概言之,作为一个外在于大陆的岛屿,很少有外力会骤然打破它的进程,同时它又能关注到大陆的变化,吸取对自己有利的技术或观念,在大陆纷争时则可自由选择介入的时机。于是,英美社会呈现出某种看似矛盾的集保守与进步于一身的特性。英国虽然是最早出现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却是欧洲最推崇乡村文化和绅士风度这种“旧时代残余”的国度。至于美国,正如书中所说,“既是捍卫国际秩序现状、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加以改变的保守大国,又是寻求用市场经济和民主理念更替老旧权力结构的革命强国”。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历史证明,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的常常正是这种“保守进步主义”,因为现代化一方面要求变革,但又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就像核聚变固然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如果这能量无法控制则将是个灾难。英美的成功正是一系列条件的综合结果,它塑造了某种“长期社会”,并有完备而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持这种长期连续性,由于社会转型常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这就保证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积累与保存——无论是财富、权利、知识还是资本,都需要不间断的长期积累,才能最终引发变革。相比起来,欧洲大陆的国家或是常被国内国际战争所打乱,或是像俄国那样太过保守而缺乏进步创新的刺激,难以形成大量财富累积的过程,因为一次战乱或革命所带来的掠夺与没收,便可能终止这一进程。
因此,仅仅谈论“小店主国家”对黄金的贪欲,或美国对石油的贪欲,是没有意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后从美洲掠夺了数量惊人的贵金属,但由于缺乏一个有效运作的经济体系,这些过量金银的流入却只带来了诅咒:一方面造成其本国的物价暴涨,另一方面强化了国王的专制权力,因为有了这些黄金,他们便不再需要征召议会来收税,如葡萄牙在1697~1820年从未召开国会,造成五代人缺乏立法经验。其结果,只是造成了国家经济的停滞,金银从手指中流过后进入英国,反倒加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
甚至于“上帝”也未必重要。虽然英国通俗小说家E.M.德拉菲尔德曾说过,英格兰人的信条首要的一点便是“上帝是个英格兰人,很可能在伊顿公学读过书”,但类似的念头大概欧洲各国多多少少都有。开创现代海洋秩序的荷兰人,说起来并不能算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倒不如说是欧洲最世俗化的民族。固然,坚信“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的信仰本身就带来力量,但不难设想,这也会助长人的独断行为,因为既然上帝与我同在,那我自然可以忽视他人的反对意见——这一定程度上正是我们这些年在美国的单边主义中所看到的情形,在小布什当政时代尤为明显。而美国人之所以普遍比欧洲人(包括英国人)更常去教堂,恐怕很大程度上又还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安全所带来的社会连续性,使他们不必像在自己国土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那样对上帝产生幻灭感。概言之,当下美国人维持对上帝的虔诚,是其特殊经历的结果,而非原因。
显然,作者对“海洋秩序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甚至干脆判定“地球上其他文化别无选择”。虽然英美一体,但在这件事上,现在美国人往往比英国人表达得更为直率。杰里米·帕克斯顿在其《英国人》一书中说,在英国人看来,“以任何形式公开表示民族自尊,不仅是头脑简单的,而且无论如何是应该在道义上受到谴责的”。公开谈论本国的优越性有时的确令人难堪。鉴于作者本人就是美国人,这样说不免有几分自吹自擂之嫌。(他带着歉意说:“这样说粗俗得不可原谅,但在300多年的战争中,英语国家确实常胜不败。”)实际上,当你是世界头号帝国时,你无须经常去证明这一点,而且历史反复证明,为成功者回头去寻找他之所以成功的理由,有时候跟预测未来一样困难。 书评保守进步思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