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立陶宛为例:重新发现戏剧强国
作者:石鸣 ( 立陶宛OKT剧团演出的《哈姆雷特》剧照
)
( 立陶宛OKT剧团演出的《哈姆雷特》剧照
)
此次戏剧奥林匹克引人注目的是在30台国外剧目中,除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传统上人们认为的戏剧大国之外,还有不少剧目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等。“认真地说,像印度的戏,你觉得会卖得很好吗?我们现在观众的趋向还是对欧美的新戏更认同,这一部分戏既有口碑又有票房。但我觉得,既然叫戏剧奥林匹克,就应该尽量展现全球的戏剧图景,奥运会尽管得冠军的还是大国强国,但没有谁规定小国不可以参加。”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说。
然而,即便是在奥运会上,边缘小国也会在某些项目上表现出超越大国的明显优势。“文化不能势利眼。”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在立陶宛OKT剧院的《哈姆雷特》首演之后打趣说。这场三个小时的戏,因为节奏掌握得好,几乎没有感觉时间就一下子过去了,演毕后社交网络上传得最疯狂的问题就是怎么买票,到处询问的答案都是售罄。这个戏是小剧场,座位有限,按照戏剧奥林匹克的安排,每个戏都只演两场,剧场调配方面的问题也不可能加演。票价原本定为300、200、100元一位,据说第二场演出开场前价格在黄牛手上已经翻了几番。
也正因为这个戏,许多人的目光才第一次聚焦在这个波罗的海小国身上。“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大量信息,其实是欧美的主流信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当然他们倡导的未必不好,但是只盯着这些看,最大的问题就是漏掉了很多所谓小国。其实波罗的海三国无论从戏剧上讲还是从古典音乐上讲,都是真正的大国。”张宇说。
这次,沈林向戏剧奥林匹克组委会推荐的立陶宛OKT剧院的《哈姆雷特》或许就是一个没机会登上《纽约时报》的戏,也是沈林所说自己“花了30年看戏,才挑出来的几个好戏”中的一个。这个剧院(Oskaras Korsunovas Theatre)事实上是以其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Oskaras Korsunovas)命名的,而遍查这位导演的履历,发现他的教育背景就是从立陶宛音乐戏剧学院毕业。“你这样问有一个前提,好像学戏剧非要去美国、去英国。”沈林笑了,“我跟你讲,去美国就完蛋了,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戏剧荒漠。你到这些国家的戏剧节去看就知道,美国人说我们是来考察的,他们的教授都到波兰去朝圣,去看戏,到立陶宛去看戏。中国以后就应该多派人到波兰、俄罗斯、意大利学戏剧。”
OKT剧院也并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2007年,作为国家话剧院“永远的莎士比亚”活动的一部分,在国家大剧院曾上演过他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接待会上,我说中国人以前对于立陶宛的印象就是篮球,现在开始要加上一个话剧。”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说。
 ( 格鲁吉亚科捷·马加尼什维里国立戏剧院和拇指剧团演出《我的哈姆雷特》
)
( 格鲁吉亚科捷·马加尼什维里国立戏剧院和拇指剧团演出《我的哈姆雷特》
)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主力演员,这次也是演《哈姆雷特》的主力。OKT剧院的规模并不大,最初成立时核心成员只有7个人,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是立陶宛国立话剧院的导演,而OKT是他从国立话剧院分离出来自己搞的一个独立剧院。“你就记住,他之前所在的立陶宛国立话剧院地位在他们国家相当于我们的北京人艺。”沈林说。
OKT剧院从立陶宛国立话剧院的独立,是彻底的独立。剧院主页上写道:“我们切断了与当时的现实戏剧的一切联系。”一开始,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演出场地、办公地点,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必须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组织,人不多,但是大家都做很多事情,我们并不做商业性演出,但我们确实拥有自己的观众群,而且在立陶宛和整个欧洲都有很多巡演,这些都让我们生存了下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定的、非官方的赞助来源,我们还和国际性的戏剧节一起联合制作演出,比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我也和立陶宛的其他剧院合作导戏,但是主要作品还是留给我自己的剧团。”奥斯卡科尔苏诺夫说。
 ( 波兰ZAR剧团演出《剖腹产》 )
( 波兰ZAR剧团演出《剖腹产》 )
比较一下上次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这次引燃大家的《哈姆雷特》,沈林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很好,但是文本解读就不如《哈姆雷特》。这个戏他是下过工夫的,文本弄得特别细致,前后顺序调得很有道理,尤其是在我们搞莎士比亚研究的人看来就会特别兴奋,竟然还可以这样?”
全戏一开场,演员排成一排坐在化妆镜前,注视着镜子里的形象,不停地反复发问:“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声音从喃喃自语逐渐变成大声质问、嘶吼,然后一声巨响,舞台切换到莎士比亚笔下第一幕第一场。“非常有趣,因为原剧的第一句台词正好是:对面是谁?”沈林说,“关于这个开头,导演是有说法的。他原来自己想演哈姆雷特,后来决定不演了,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演员,打定主意一定要排。他说他曾常常看着镜子里面,每次看着镜子的时候都会想,这张脸能演什么?哈姆雷特吗?我是谁?我准备好了吗?我还要化妆呢。他说这就是演员在演出前的状态,在化妆室里,我马上要换一个新角色了,所以他就这样糅在一起了。”
 ( 格鲁吉亚科捷·马加尼什维里国立戏剧院演出《皆大欢喜》
)
( 格鲁吉亚科捷·马加尼什维里国立戏剧院演出《皆大欢喜》
)
全戏结尾时,一部分演员的角色已经死去,但演员还停留在舞台上,坐在化妆镜前开始卸妆,剩下的还活着的角色在说着台词,即将展开新一段旅程的霍拉旭甚至开始上妆,往脸上涂一个京剧面具。“最好的状态就是台上的演出还在进行着,但你知道你的角色已经完了,于是你走到化妆间开始卸妆。我把这些都摆在了舞台上,道具只有化妆台,和化妆台里装着的一切东西,白色纸巾、红色纸巾、矿泉水、人工假血,然而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和这些东西在给你讲的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层结构。这赋予了这个剧场里所有一切第三个维度,一切因此而变得立体了。”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解释说。
这部《哈姆雷特》在立陶宛首演于2008年11月28日,非常成功,立刻去欧洲重量级的艺术节,沈林便是2009年在波兰的一个戏剧节上看到了这出戏。时隔6年再看,他感觉似乎有许多地方的表演和调度都发生了改变。但是,文本上的基本结构是没有变的,比如,导演依旧给奥菲利娅安排了两次葬礼。据沈林回忆,当时演完后第二天立刻有许多导演、评论家追问奥斯卡科尔苏诺夫为什么要这么排,他的回答很明确:奥菲利娅是无辜的人,被所有人利用,她一上来我们就知道她是没有前途的,她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因此我干脆把王后宣布她死亡的那段台词放到她第一次与王后见面。那么,为什么奥菲利娅一出场脸上涂的就是一个日本能剧的面具?导演的答案是类似的:“能剧里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剧角色,这喻示着奥菲利娅的生命也即将成为悲剧。”
 ( 奥斯卡·科尔苏诺夫
)
( 奥斯卡·科尔苏诺夫
)
“在2009年的那个戏剧节上,看戏的人都是世界各国的导演、总监、策划人一类的人物,当时有一个汉堡剧院来的德国老太太,自己搞戏剧节,也是资深剧评家。她当时看了表演后说的一句话是:‘这个戏很不一样,很独特。’”沈林回忆道,“你看他们的表演,不像德国的那种程式化。在我看来,德国戏剧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程式,比如所有演员都面向观众对话,互相交流少,舞台调度一般都是前后动,不横着走,不形成一个情境,偏重大量的朗诵、宣读。比如这次戏剧奥林匹克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能看出这样一套风格。相比之下,去看波兰和立陶宛,坦率说,更丰富,什么样的都有,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他们表演上跟俄罗斯有关系,但又不像,比俄罗斯要冷,又不像德国的那种冷和愣。舞台上特别重视觉,但绝对不是西欧的视觉,不是荷兰的、比利时的,不是舞蹈剧场的那种东西。”
从某种角度上讲,奥斯卡科尔苏诺夫可以说是具有戏剧天分。他在立陶宛音乐戏剧学院读“大一”的时候,就导演了第一出戏。“那出戏非常成功,我当时才20岁,我本来是学表演,从那以后,就开始专注做戏剧导演,以此为志业,后来便进了立陶宛国立话剧院做导演。‘大一’导了第一出戏后,我就停止了学习,因为我已经是导演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对于旁人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对我来说却要靠自己的思维来重新发明的原因。戏剧对于我来说成了我分析自己、更好地认知自己的一种工具,就好像别人通过写作、写日记的方式来认知自己一样。戏剧对我来说就像宗教,像牺牲,像速记本,像Facebook,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
 ( 《哈姆雷特》剧照
)
( 《哈姆雷特》剧照
)
“戏剧是一只捕鼠夹”
——专访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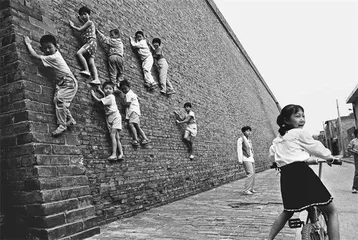 ( 《剖腹产》剧照
)
( 《剖腹产》剧照
)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这个戏原来演的时候是三面观众席,这次在东方先锋剧场演,舞台只有一面面对观众席,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做了很多修改?
科尔苏诺夫:我们在很多不同场地演过这出戏。空间主要是由我们使用的这些化妆桌来决定的,这些带镜子的化妆桌是第一个重要元素,第二个元素就是观众。观众自身也在镜子中被映照出来,和演员一样,就好像哈姆雷特在第二幕一开始时候对那些伶人说的,你们应该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去表演,像镜子一样。第三个元素是演员,因此是镜子、演员和观众的三者关系。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能改变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固有距离,这并不只指“距离”的物理意义,而是说我们要努力去破除横亘在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心理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东方先锋剧场的舞台很高兴的原因,这不是一个意大利式的舞台,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没有乐池,舞台也不处于一定的高度上,这有利于我们拉近观众和演员间的距离。
 ( 《哈姆雷特》剧照 )
( 《哈姆雷特》剧照 )
6年以来,这部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原则是要对表演不断进行彩排,这也是我要创立自己剧团的原因,为了能一直有时间排练。通常情况下,一部戏被排出来,首演诞生的同时也就宣告了死亡,因为之后就不会再排练了,只是按照第一次排出来的结果展示。我认为,只有在不断排练、不断改变之中,一出戏才有可能获得生命。时间流逝,演员们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智识,我也一样,时间对我们做出它自己的校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修改表演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一场演出理想的观众数是多少?
科尔苏诺夫:(开玩笑)一个。就像哈姆雷特在剧中对演员说的,你要知道,你只对着一个人表演,一个观看者,你就是自己唯一的观众。(正色道)实际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考虑一下,一次演出剧场只能容纳特定数量的、有批判眼光的观众,那么观众就最好能代表社会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剧场是一种共同经验,对创作过程来说,你只面对你自己一个人,但你最后需要把这种对自我的评估呈现给公众和社会,因此你需要有300个到500个人坐在观众席,一起来经历这个戏剧性事件。古代的模式是最好的,比如在古希腊雅典,所有的公民都来观看演出,那时候戏剧也确实在改变社会,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使用同一个演员来演叔父和被叔父谋害的老王?
科尔苏诺夫:首先,他们是同胞兄弟,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们看起来长得很像。尽管剧本里写的是老王英俊潇洒,杀死他的克劳狄斯则相貌丑恶,但我认为,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父亲的形象。也因此《哈姆雷特》这出戏在某些方面和《俄狄浦斯王》有关联,“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家喻户晓,我排过《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和契诃夫的《海鸥》,在我看来,这三个戏可以成为一个三部曲,贯穿主题就是父亲。在《哈姆雷特》剧本中的每个细节,我们都能找到这个三角关系,父亲、儿子和母亲。父亲的鬼魂就好像永动机一样,不停在哈姆雷特身后追逐着他,压迫着他,他无法摆脱,好像被逼迫着在父亲面前完成自身的净化。他把父亲看作圣徒、一个神圣的存在,同时把克劳狄斯完全妖魔化,是恶魔,是撒旦,这种两分法是哈姆雷特的想象,也是我们最终决定使用同一个演员扮演两个角色的部分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科尔苏诺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演员。
三联生活周刊:区分老王和叔父的手法是不是就是衣服的穿脱?如果是的话,就相当于叔父在做登基和大婚演讲前,将同一段话独白了两次,为什么这么安排?
科尔苏诺夫:对,是这样的。剧中在将近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说:这两个人之间的善恶、美丑之分如此昭然,你怎么能在这两个中间选择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那一刻,克劳狄斯的衣服半穿半脱,一只肩膀裸露在外,另一只肩膀则披着衣服,摆成十字形的镜子从一个方向映照出他黑色衣服的一面,另一个方向则映照出他赤身裸体的白色一面,就好像同一个人被分裂成了两个。
实际上,这场戏可以看作是克劳狄斯如何失去他的良心。克劳狄斯第一次独白,就像是独自一人给自己彩排,在那一刻他被两种情绪驱动,一方面他很恐惧,因为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兄长,犯下了杀兄之罪,被罪恶感所迫害,感觉有诅咒降临到他身上。《圣经》中,该隐犯下杀害亚伯之罪,这是一个类似的时刻,哈姆雷特后来在剧中的台词也提到过,他提醒叔父该隐犯下的罪过。另一方面,克劳狄斯也尝到了他想要的胜利的滋味,他要发表的这个演讲非常荒谬,都是毫无意义的胡话,他的台词的第一句是:我们要用一种非常现代、非常经济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哀悼,所以我们就不表示哀悼了。他在嘲笑他的眼下所见,尽他所能地变得犬儒。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演讲完全是为公众创造出来的,他这么做,表明他在失去自己的良心,被权力变成彻头彻尾的犬儒,这就是他要提前给自己彩排的原因。他要迫使自己进入一个完全恶人的模式,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已经完全像一个政客那样在大众面前去表演,他的眼泪也是伪善,但是彩排却是很艰难的,他必须摧毁他自己内在的人性部分。这一点克劳狄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相似之处。
三联生活周刊:剧中的王后葛特露和奥菲利娅之间似乎有一种母女的温情,你怎么解读她们之间的关系?
科尔苏诺夫:奥菲利娅没有母亲,这种人物关系设置常常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也因此王后对奥菲利娅有一种母亲的感觉,她对于奥菲利娅非常敏感,因为她在奥菲利娅身上认出了她自己。如果奥菲利娅不是后来失去心智而发疯,最后溺死,她会和葛特露一样,成为王妃,成为葛特露那样的人,完全倚赖权力、倚赖男人的世界而生存。因为奥菲利娅就像被牺牲的羔羊,实际上她是一个摆给哈姆雷特的诱饵,诱使他暴露自己的秘密,使得别人了解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什么、接下来要做些什么等等。她一直被旁人操纵,而葛特露也一直在权力争斗的两方之间周旋,没人能像葛特露那样理解奥菲利娅,这也是为什么莎士比亚在原剧本中安排葛特露来宣布奥菲利娅死亡的原因。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当初葛特露是怎么嫁给国王当上王后的,在权力游戏中,也许奥菲利娅正要开始说出真相,她就变疯了。葛特露理解这一切,因为这场权力的游戏她都亲身经历过。
而葛特露最后的死亡其实是自杀,当她拿起那只骷髅头做的酒杯,就已经明白自己将要死去。实际上,是她选择了死亡,当哈姆雷特对她说,“我要把你灵魂黑暗的那一面剖开来给你看的时候”,她明白了她会站在哈姆雷特这一边,并且死去,而不是站在克劳狄斯的那一边。在《哈姆雷特》的这个系统里,只能有两种生存方式,要么是政治化的生存,要么是人性的、人本主义的生存。哈姆雷特、奥菲利娅、葛特露都选择了人性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死亡;而霍拉旭在剧末变身福丁布拉斯,他选择了政治化的生存方式,因此他将活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台上那只大白老鼠象征着什么?
科尔苏诺夫:关于这只大白老鼠,有很多象征含义,贯穿整出戏。首先,它就像某种命中注定你无法避免的东西;另一方面,原剧本里哈姆雷特编了一个戏中戏,名字就叫作《捕鼠夹》,这就是我们允许自己在舞台上开这个玩笑的原因,有点像是哈姆雷特灵魂的某种展现,反射出哈姆雷特自己。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哈姆雷特给伶人们说:你们只是在对着一个人表演,他的心里想的是克劳狄斯,这就像是给克劳狄斯设下的捕鼠夹,但是最后被捕鼠夹扣住的却是哈姆雷特自己。那也是为什么在全剧结尾,哈姆雷特对自己的朋友霍拉旭说:我死了,你将活下去,给众人讲述所有的故事如何发生。我们把本来位于结尾的这段台词提前,放在戏中戏即将上演前,那时候哈姆雷特还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结局,却已经领悟到自己必然会死,但是他没有其他出路。我们想展现这个降临在他身上的、来自家族的诅咒。当哈姆雷特给克劳狄斯设下这个捕鼠夹的时候,相当于他也给自己设了一个捕鼠夹。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把整个做戏的过程当作是给我自己设的捕鼠夹,对我来说,戏剧就是某种捕鼠夹,好像一张要网住自己的陷阱,这是我对戏剧的一种理解。
《哈姆雷特》搬到舞台上时,经常被演成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一个试图反抗周围环境、人事的反叛者。但是实际上,根据莎士比亚原剧本,哈姆雷特已经30岁,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寿命都不长,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个成熟的成人,他没有时间去拖延,把事情搁置到日后再说。后来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是稍后;如果不是稍后,那就是未来的某个时候。事实上,他是在讨论死亡,他在说他不想拖延,他想活在当下。当我排演《哈姆雷特》的时候,我40岁,我理解了这种心情,我必须现在就把这出戏排出来,否则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了。我的生命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允许我一再拖延,我必须现在就行动。就像哈姆雷特一样,这也是一个责任问题。他要么成为国王,要么什么都不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关乎他对生命的所有反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戏为什么排了两年才排出来?
科尔苏诺夫:这是我第一次排《哈姆雷特》。我告诉我的演员们,实际上我们不必太介怀到底是要把这个戏排出来还是不排出来,我们到底能不能有一个结果。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哈姆雷特的行动机制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把这只戏剧的捕鼠夹给我们自己装上。我们想要自己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既是作为演员发问,也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发问。因此整个剧情被设置在化妆间,在剧院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我们把《哈姆雷特》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排演新戏,发掘新东西。做《哈姆雷特》时,OKT剧院已经做了10年,《哈姆雷特》被我们设定用来分析“到底什么是表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演戏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演出中到底是谁”,我们和哈姆雷特一起发出同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持续两年后,我们不仅排出了《哈姆雷特》,同时诞生的还有高尔基的《在底层》(The Lower Steps)和契诃夫的《海鸥》。
三联生活周刊:可不可以讲一下OKT的创立过程?你创立这个剧院时候才29岁,而且使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剧院,这在当代好像还没有其他先例。
科尔苏诺夫:我的戏确实很像是“作者戏剧”(author's theatre),但我并不是那个给我的剧团命名的人。当我还在立陶宛国立剧团里工作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用我的名字来指代我的作品,称之为“OK戏剧”。实际上,最开始是批评家们使用这个名词,以至于当我创团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名声,为了不至于引起混淆和误解,我们就沿用了别人对我们的这一称呼。
至于我创立自己剧团的真正动机,我之前曾经说过,我已经受够了国有院团或者说大型剧院的组织结构——部门臃肿,人员芜杂,却不怎么演戏,总之就是人浮于事,一无所成。一个戏被排出来,没人去关注观众反应,没人关心要继续彩排、继续修改,即使是很优秀的演员,也在这样的气氛下慢慢沉沦和堕落,导演对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后续命运一无所知。我不想这个样子,于是只能与国立剧团决裂。我有我和演员一起工作的方式,这种方式逐渐在实践中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所谓我的学派,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今,我们分道扬镳已经15年了,这15年来,我们吸引了自己的观众,积累了大概15台常演剧目,我招收了自己的学生。如今长期学生有15个,都是演员。我们有一个小的核心演员群体,在规模比较大的作品中,我们会和其他的优秀演员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演员训练方法是什么?
科尔苏诺夫:(笑)这个答案可以写上300页书了。简单说,主要原则就是演员要被训练成能够理解他自己,理解他是谁。这不太以斯坦尼体系为基础,斯坦尼体系要求演员把角色具象化,去展示角色的感受。但是我的要求更多的是要理解自我,你扮演的角色是谁有更多的自觉意识。实际上,在我最新的舞台作品《海鸥》中,你能看到演员并不是角色本身,他和角色不同,他在扮演角色,他和角色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是演员在讲述这个角色的故事。台词中的对话部分经常变成独白,由演员向观众陈述,既是扮演,又不是扮演,两种状态同时存在,这是原则。事实上,这样一种主要原则意味着对后台状态的废除,你几乎能看见一切,他的手势,他的动作,他的生理状态,演员和观众之间不再存在距离,这是斯坦尼方法和梅耶荷德学派的结合,以及其他学派的影响,包括铃木忠志的方法。我有一个女演员,也是编舞家,我们经常合作,她受过铃木方法很长时间的训练,我现在的学生也有一些具有铃木方法训练的基础。要说我的风格和其他大多数学派有什么不同的话,主要差别在于,其他大多数学派都在教演员如何融入角色,将自己融在角色中,而我让演员利用他的角色来成为他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戏剧传统是什么?
科尔苏诺夫:我和立陶宛戏剧有很强的联系,立陶宛戏剧受俄罗斯戏剧影响很深。首先是“导演剧场”,以导演的决定和选择为中心。其次,立陶宛戏剧还受到波兰戏剧的影响,以及德国戏剧。有一个很知名的立陶宛的现代戏剧导演Juozas Miltinis,他在法国学习,之后把新观念带回了立陶宛,在“二战”后发起了立陶宛的现代戏剧影响。我也受到东方戏剧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日本的,主要是通过我的老师Jonas Vaitkus,他对东方戏剧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说,戏剧中的立陶宛学派的确是存在的。当然,它也受到其他学派、传统的影响,因为立陶宛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本身就位于几大强国的边境线上,它成功地从几个强大的传统和影响中幸存了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苏联时期,立陶宛曾经以反抗之地闻名。事实上,正是在柏林墙倒塌的同一年,我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台作品,所以我能够说,我是“后柏林墙的一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可以自由地前往西方国家,这是一次开放,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文图片由“第六届戏剧奥林匹克组委会 ”提供) 为例立陶宛剧院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强国三联生活周刊哈姆雷特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