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脑GPS
作者:曹玲1988年,挪威特隆赫姆,两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坐在著名神经科学家皮尔奥斯卡安德森(Per Oskar Andersen)的办公室里,向安德森解释为什么必须跟着他学习。当时安德森正在开展对大脑海马体区域神经细胞活动的研究,海马区是大脑中一个与记忆有关的重要区域。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挪威科学家莫瑟尔夫妇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挪威科学家莫瑟尔夫妇
安德森对此非常犹豫,这名叫作梅-布里特莫瑟尔(May-Britt Moser)的女生说她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莫瑟尔(Edvard Moser)对行为和生理的交集感兴趣。
201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梅-布里特说:“我们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他实在没办法让我们走出办公室。”
“我们都来自非学术性家庭和非学术性的地方。”爱德华说,“我们长大的地方,没人接受任何大学教育,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做这些事情的秘诀。”
“还有不知道如何礼貌行事。”梅-布里特插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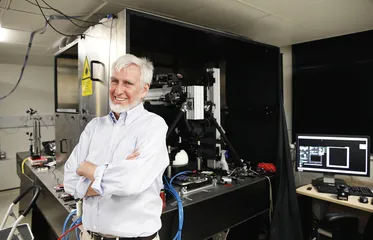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英双国籍科学家约翰·奥基夫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英双国籍科学家约翰·奥基夫
但他们狂热的好奇心和坚定的决心使得安德森最终向他们妥协,收他们做学生。
2005年,莫瑟尔夫妇在大鼠脑部发现了一种导航系统,他们称之为网格细胞(Grid Cell),并因此一举成名,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他们在英国留学时候的导师、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大脑中用来定位的位置细胞。
当时奥基夫发现,小鼠在房间的某个特定位置时,其大脑海马区的一些神经细胞总是处于激活状态,而小鼠移动到其他位置时,其他神经细胞则被激活。他因此得出结论:正是这些位置细胞,在大脑中形成了关于房间各点具体特征的“地图”。
然而仅仅拥有地图还不足以为我们导航,因为地图描述了每一个地方的特征,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地点的相对位置。还需要一个“经纬网”,让地图上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坐标。而莫瑟尔夫妇关于“网格细胞”的研究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介绍:如何知道我们身处何方?我们怎么找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径?我们如何存储这些信息,从而能够在下一次立即找到这条路?三位获奖科学家的研究解决了困扰科学界几个世纪的难题,揭示了大脑如何创建周围空间的“地图”,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定位路径。对大脑定位系统的认知,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大脑空间记忆的中枢机制。
这一发现的意义深刻又实用。网格细胞也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我们回忆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联想到事件的发生地,网格细胞的工作表明大脑里“不断地建立外部世界的地图”。这些细胞已经在灵长类动物中存在,科学家认为能在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都能找到。在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大脑中的这个区域常常被损坏,而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早期频繁出现的症状之一就是迷路。
奥基夫和莫瑟尔夫妇等人推测,大脑记录和记住空间运动的方式,可能是所有记忆的基础。这个想法和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记忆宫殿”相共鸣。“记忆宫殿”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计划进行长篇演说的哲学家为了记住自己的讲稿,会将自己演讲的不同段落与现场不同的建筑背景或场景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便能随着自己思维地图的指引,几乎非常流畅地完成抑扬顿挫的长篇演说,每一处不同的地标都会激活演讲人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区域,提示他接下来所要讲的话。网格细胞的发现证实了大脑、记忆与位置环境之间的关系。
莫瑟尔夫妇出生和长大的岛屿在距离挪威海岸几百英里的北部卑尔根,他们在同一所高中上学,但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奥斯陆大学再次相遇。
梅-布里特在农场长大,在那里喝酒、玩牌、跳舞都是不被允许的。当她从奥斯陆打电话回家宣布已经去过酒吧,喝过啤酒时,她妈妈会问:“接下来呢?”
他们于1985年结婚,结婚时还是本科生。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时他们已经有两个女儿,此时他们仍然准备去看看世界,在挪威之外的实验室接受训练。他们在英国奥基夫那里,以及爱丁堡大学理查德莫瑞斯(Richard Morris)那里都学习过。
1996年,莫瑟尔夫妇意外收到位于特隆赫姆的挪威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职位邀请。对于这项邀请两人犹豫不决:如果接受,那么就将意味着前往一个远离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偏远之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大学单打独斗。
“我们确实谈判了。”梅-布里特说,“如果只能获得一份工作,我们没有兴趣,而我们得到了两份工作。如果得不到需要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兴趣,但他们给了我们全部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他们一同回国的还有两个小女儿,一个蹒跚学步,另一个还在襁褓之中。
在特隆赫姆安顿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白手起家,在一间地下室里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另外还要建立一个实验动物基地。梅-布里特把那时候的实验室称为一个防空洞,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建立了自己的计划。
今年10月初,《自然》杂志以莫瑟尔夫妇的人物特写报道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开始将电极直接植入小鼠的海马体,并记录当它在一个大盒子内自由奔跑时产生的大脑信号。这些植入的电极灵敏度极高,可以记录下单个神经细胞发出的信号,这些信号会被送入计算机,匹配这些神经细胞被激发时小鼠在盒子中所处的位置。这些点的位置在屏幕上以黑点的形式呈现。为了确保小鼠的活动区域涵盖整个盒子区域,夫妇俩还特地在盒子底部均匀地撒上了一些碎巧克力。
“我们并没有立刻就找到网格细胞。”爱德华说。他们采用化学方法人为地让小鼠海马体的部分区域失效,并观察在这样的情况下位置细胞是否还照样会发挥作用。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注意到信息流是从临近的内嗅皮层传导而来的,这是小鼠大脑后下方一处垂直方向上的微小组织。此前没人对这一不起眼的组织投入过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一组织非常难于接触,一侧非常接近一根大的血管,在这里操作将可能引起致命后果。在向一位大脑解剖学专家请教后,莫瑟尔夫妇得出结论,植入电极的最佳位置应该是避开血管,而置于接近大脑皮层的地方。然后他们开始不断重复这一实验,记录来自内嗅皮层单个神经细胞的信号。
他们发现,每次小鼠在特定地点都发射信号的细胞,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海马中类似位置细胞的东西,试图定位外部世界。但是渐渐地,他们了解到,不管小鼠在什么地方,一个细胞都以同样的方式追踪小鼠的运动,这个细胞并不响应某些外部标记。当他们给小鼠足够的空间,非常有规律的模式出现了,那是一个呈六边形的网格形状,就像一个蜂巢。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设备出错了。”他说。
“我想,‘这个是一个错误?’”她说。
这样简单而规则的图形是他们无法相信的结果。一般来说,生物学实验得到的结果会比这个杂乱得多。莫瑟尔夫妇逐一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最终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既然这是事实,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盒子里并没有六边形状存在,这一形状是在小鼠的大脑内抽象形成,并叠加于环境背景之上的,当小鼠经过这一抽象六边形上的某一点时,某一对应的神经细胞就会被激活。这就是空间的大脑语言,大脑依靠这种语言来刻画周围的空间环境,这也正是长期以来人们苦苦寻求的问题的答案。
2005年,他们在《自然》发表论文,报告了发现的细胞并将其命名为网格细胞。接下来其他实验室确认了新的发现,随后更多发现接踵而至。
这项发现让理论学家也大吃一惊,因为六边形是借助最小网格数量达成最高空间分辨率的最优化图形方案。这一方案最节约能量,它展示了大脑运作设计的精妙与高效率。德国慕尼黑大学计算神经学家安德亚斯赫兹(Andreas Herz)说:“谁会相信这样一个优雅的六边形图案会存在于我们的大脑深处呢?真是难以置信,大脑竟然使用着同一个我们在数学中已经使用了数百年的简单几何图形。”这种令人震惊的简洁给人以希望,那就是整个大脑的运作机制或许是遵循着某些数学计算原则,因而最终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的。
要理解大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脑用来描述这个世界其他方面的语言或许不太可能和这次的情况一样简单,或许某个神经细胞实际上承担着对世界不同角度的描述功能,这种叠加会让解译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我们仍处于神经科学的牛顿前阶段。”爱德华说。
“我们有共同的项目和共同的目标,我们都强烈地为之付出,我们彼此依靠才会成功。”他说,“大部分夫妻共同抚养孩子,对我们来说,大脑项目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不同。” 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