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的茨威格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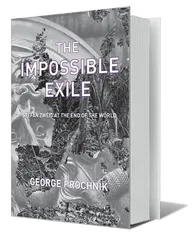 《不可能的流亡:在世界尽头的斯蒂芬·茨威格》
《不可能的流亡:在世界尽头的斯蒂芬·茨威格》
电影《布达佩斯大酒店》是受作家茨威格的启发而创作的,但它不是改编自茨威格的某一部小说,启发它的是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以及他的人生。电影中更像茨威格的不是那个听故事的客人,而是那个讲故事的门房。这个门房可谓八面玲珑,又有些神经质。电影情节跟茨威格本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门房是被纳粹杀害的,茨威格是在巴西自杀身亡的。
茨威格自杀后,巴西政府给他举行了国葬,总统出席了他的葬礼。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很愤怒,认为茨威格的自杀是懦夫的行为,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不该授予纳粹这一胜利,如果他更加仇恨和鄙视他们的话,他永远都不该这么做。”
茨威格为何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呢?自杀前,他刚刚写完回忆录《昨日的世界》和《巴西:未来之国》这两部重要的著作。他还写了小说《象棋的故事》,证明他遭受的考验并没有毁掉他的创作能力。他刚刚娶了一个比他年轻近30岁的女子。他自由地选择离开美国,落脚于好客的巴西。他一生中从未有过可怕的经历,或者面临生死抉择。他好像总是能够抢在时间的前面,有时间从容地打包,整理他的财产,挑选他的目的地。
茨威格早在1933年就离开了奥地利。流亡之初,他过得挺舒服。搬到伦敦后,他让妻子弗里德里克帮他雇一个秘书。她挑选了娇弱、谨慎的年轻女孩绿蒂。绿蒂经常陪茨威格一起旅行,还跟他一起去尼斯见他的妻子。有一天,茨威格让他妻子去办事,弗里德里克半路上想起她忘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就回酒店去取。结果发现茨威格跟秘书睡在一起。他们被惊醒了,但弗里德里克很冷静,找到文件后又去办事。回来后她没有要求辞掉绿蒂,而是去休假。几天后,茨威格上了船,弗里德里克陪他进了船舱。梳妆台上摆着一封信,夫妻二人都认出了绿蒂的笔迹,茨威格没有打开,直接把信交给了弗里德里克。这件事表明,茨威格很会息事宁人。
传记作者乔治·普罗尼克(George Prochnik)在《不可能的流亡:在世界尽头的斯蒂芬·茨威格》中说,茨威格是“一个富有的奥地利公民,一个焦躁不安地漫游的犹太人,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孜孜不倦地倡导泛欧洲人道主义,他不停地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他是一位无可挑剔的主人,热爱家庭生活、歇斯底里,高贵的和平主义者,卑劣的民粹主义者,神经质的肉欲主义者,爱狗,恨猫,是藏书家,穿鳄鱼皮鞋,时髦,焦虑,咖啡爱好者,有着孤独内心的同情者,随意地拈花惹草,对帅哥抛媚眼,大概是暴露狂,绝对爱说谎,趋炎附势,维护弱者,在老年的蹂躏面前他是可怜的胆小鬼,在死亡之谜面前他不动声色而又淡泊”。
 乔治·普罗尼克
乔治·普罗尼克
差不多跟茨威格同一时间到达美国的托马斯·曼宣称,他代表德国的精华:“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我身上带着我的德国文化。”茨威格缺少这种自信,感叹移民会转变一个人的重心。托马斯·曼是德国上等资产阶级的一员,根基深厚,而茨威格是一个犹太人,欣赏选择国籍的绝对自由,无论身在何处都觉得自己是客人。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后,茨威格再次陷入非理性的恐慌,担心德国入侵南美。他开始写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他第一次把纳粹写进了情节之中。1942年2月22日,他完成了小说。第二天,他就跟绿蒂服了安眠药自杀。 尽头茨威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