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自画像
作者: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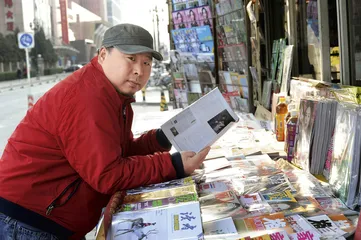 ( 信海光 )
( 信海光 )
“一千个铁杆粉”的可能
今年初,曾航和最早开始做微信自媒体的十来个人,通过微信群召集了一场“神农架会晤”。“坐飞机到宜昌,再坐5小时汽车,步行山路,到达神农架。之前我们在微信上很熟,讨论后台技术、‘粉丝’群等,但很多人是第一次见面。”曾航告诉本刊记者。他27岁,维护着微信公众号“移动观察”,有4万“粉丝”。他努力让说话的语气波澜不惊,保持职业范儿的稳重,虽然时不时摆弄的iPhone罩着动漫感的大红色赛车手机套。
那一次会议对微信自媒体也许会有历史意义。与会的还有成名于虎嗅网和雷锋网的潘越飞、《i天下网商》主编许维等自媒体人。“年初,关于自媒体的激烈争论爆发,很多人认为它没有前途,会像博客一样昙花一现,我们就决定聚一下,共商自媒体未来。”微信千字文的形式确实让人觉得“自媒体”就像移动互联网时代复活的博客,博客时代方兴东迅速名声大噪又快速陨落的历史还历历在目,以博客为载体的自媒体在财务上可维持的商业模式成熟前便沉寂了。“我有个朋友,在新浪写了7年博客,7年里总共拿到900元。”曾航说,他已经想不起自己过去的博客密码了。
自2009年被微博打断后,微信所开启的自媒体似又可能开始新一个轮回。曾航属于前途乐观派。5年前他进入《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做IT新闻时,乔布斯的第一代iPhone刚发布,移动互联网时代刚到来。2009年,3G与iPhone在中国市场的结合,引爆了移动互联网产业。也是在这时候,他走访了iPhone的全球产业链,见证了iPhone时代在全球的到来。在他写关于iPhone的书时,微博正兴起,“微博‘粉丝’在那时候增长得很快”,不久达到了4万。2012年,他受日本咨询公司野村综研的邀请写一本关于日本移动互联网的书。“移动互联网最发达的地方是日本,3G时代比中国早3到4年,4G时代2010年就来了,二维码与手机支付早已普及。”日本调研结束时,微信刚开始流行,曾航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公众账号上部分连载他即将发行的新书。他于去年底开公共账号后不久,运营科技博客“云科技”的程苓峰就开始尝试自媒体的商业模式,1月推出微信广告,报价每天1万元,3天5万元,2小时内接单,2个月10单进账17万元,看起来有戏。加之目睹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它在日本的成熟前景,曾航相信,这一次自媒体的“复活”将会是“革命性”的。年初那一次的会晤,他们成立了一个最早的微信自媒体联盟,这个联盟里,集中了从青龙老贼、魏武挥、葛甲、陈中等从博客时代即已成名的自媒体。
几年行业的浸淫,曾航的账号“靠口碑积累粉丝”,很快到了4万。“微信号不像微博,有推荐;公众账号靠口碑,靠朋友圈分享,但传播是病毒式的。”曾航的读者有很多移动互联网行业里的业内人和投资人,他每天大概花1小时维护账号,最近在连载尚未上市的新书,效果很好。“就像看连续剧一样,很多‘粉丝’不断催我更新。”更重要的是,微信的“推送”模式和圈子特性,定位和抵达非常精准。就在不久前,他在众筹网模仿徐志斌的《社交红利》试水小型众筹,“试探性请两位朋友在几个陌生人比较多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下众筹消息,仅仅几个小时,筹集到了1万元”。他自认为已经拥有了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里提出的“一千个铁杆粉”:细分市场的“长尾效应”在为聚合商和消费者带来好处的同时,加剧了独立创作者的竞争和无休止的降价压力,而只需拥有1000名甘愿购买你各种版本、所有作品的铁杆“粉丝”,就能糊口,维持生存和创作。
对曾航来说,这是一次玩票性质的尝试。他有给予他财政来源的职业,是手游公司“触控科技”的战略总监,并不指着微信自媒体赚钱生存,做自媒体更多是兴趣推动。他也接一些广告,参加一些活动,他将其视为自媒体商业模式的尝试。“自媒体如果能吸引到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来做内容,这些人通常不缺钱,兴趣推动,从表达、影响力和与‘粉丝’互动中获得快感。没有门槛的自媒体就会出现高水准的东西。”曾航翻动他的手机,“我很爱看一位市场总监写的历史,这完全是他兴趣推动的自媒体。他每天晚上无论多晚睡觉,睡前必花时间写上一段。”这些带着强烈个人色彩与人格特征的“专栏”内容,不需要与传统媒体的渠道博弈,就能直达“粉丝”读者。在曾航看来,正是自媒体在传统媒体之外的生存空间。“与流水线、组织团队协作、规律性生产的新闻的传统媒体不同,自媒体灵活、随意,虽然做不了多个人组织做的事,但带着有温度的个人调性。”
曾航不善调侃,说话一丝不苟,基本没有笑容。他对自己的魅力定位为“研究型”,深度思考类。“我只需要1000个有行业影响力的小众‘粉丝’足矣”,他说。他现在每天得花不少时间后台回复“粉丝”,“维护‘粉丝’的时间成本略高,4万‘粉丝’是个尚可持续的规模”。
“人格体”与“社群”
申音简直是个营销人才。采访他的中途,他就开始推销:“你看过《罗辑思维》吗?看过一两集怎么可能理解我们呢?要都看才能领会我们的价值观啊!”他能在罗振宇的百万“粉丝”中呼风唤雨,掀起创造历史的高额众筹,举办从剩女相亲大会到集体做月饼的活动,其辐射力与凝聚力甚至能让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粉丝”自发组织社交活动,将“罗振宇”牌的个人价值经营得风生水起。他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别叫‘粉丝’啊,我们叫‘有爱的知识社群’或者‘朋友圈’”,“别说我们是‘自媒体’,老罗是‘魅力人格体’,是我们社群价值观的载体”。
2012年,申音与罗振宇的人生轨迹在断断续续的一些不经意偶遇后产生了交集。申音2010年不做《创业家》主编后,做了两年微博、微信的社交媒体营销;罗振宇离开央视后,开始做一些跟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培训和互联网视频。两人各自认识到互联网的力量。“我做社交媒体发现,人人都是传播媒介和渠道,信息网状扩散,而不是传统媒体那样以中心扩散。老罗则认识到,互联网媒体是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决定内容,不再是被动的‘沙发土豆’,而可以主动选择。”两人再遇到一块儿,拍定做互联网视频脱口秀,申音经营罗振宇。申音对罗振宇初始状态的描述特别符合网络大众的心理期待:一个体制里的边缘人,不帅,胖,不受重视,口齿不清,带安徽口音,爱死磕,没什么名气。脱口秀的风格定位则是一本正经的体制内节目的对立面:诙谐、幽默、调侃,愉悦大众。这样,罗振宇的成名故事就是一条从旧边缘到新中心的顺理成章的互联网逻辑轨迹。
申音说,当时还有几件事促成他们能够做脱口秀自媒体。“技术大大降低了成本。如果我们在2011年做,成本至少得100万元。但2012年,佳能5D Mark Ⅲ一出来,相机有摄像机功能,拍摄质量高清、稳定,只需租几盏灯就成,一期制作成本几万元搞定。”《罗辑思维》的拍摄每次都在一间屋子里,没有观众,没有嘉宾。两人下定决心做微信视频,还因为当时“老罗在以流量为指标衡量的视频网站上不算成功,只能算圈子里有点知名度。我们当时判断,在视频网站上,流量为王。但在微博微信上,先有用户,后有流量,积累用户对我来说很容易,有各种技巧,只要把握关键节点做推广,好的内容就没问题”,“下定决心做微信后,微信还能与优酷相互倒流量,很快就积累了超过1000万个‘粉丝’”。
《罗辑思维》开播以来,“‘粉丝’增长速度大概每周3万多”,一直比较稳定,“没有明显爆发点,没觉得自己突然走红过”。申音说。就像微博微信的一般规律那样,总有几条转发率很高,“也有几期节目比较红,比如,《夹缝中的80后》、《你的女神你不懂》、《岳飞为什么必须死》,还有关于剩女和罗马的那两期。每期都是按老罗自己的阅读兴趣来,经常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选题”。申音他们对节目的定位就是“知识二传手”,“帮人读书,自己不生产知识,总结提炼别人的知识,再通过魅力人格分享给别人”。做了半年,烧着钱,商业模式还只探探脑袋,没有谱。直到今年5月,一个可能是临界点的事件出现了。“在微信30万朋友圈中征集现场脱口秀的报名,地点就在北三环的‘喜来登’,下午16点到18点,名额500个。就在微信上吼了那么一嗓子卖票,没想到人们特别热情,全场爆满。当时在现场见到好多稀奇古怪的人,从互联网公司的大老板,到中小企业主,再到好玩儿的家庭主妇,还有35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公务员和刑警,共同点是对知识的向往。当时我开始感觉到‘有戏’,暗想这兴许是个转折点。”
真正让整个自媒体圈都为之一振的事件,是今年8月9日的众筹。“当时我们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申音说,“在商业模式上,是走向广告,还是主要靠内容收费?我们决定尝试一下会员制,让会员做创作人的集体赞助人,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目标是让5000个发起会员和5000个铁杆会员‘供养’。”那次众筹竟然在短短5小时内卖出180万,创下自媒体“打赏”的历史纪录。这件事向申音证明了“用户情感”的重要性。但这个“社群”众口难调,以前有很多人觉得节目时间不固定、不规律,有骂声;每一期出来,都会有不同观点,甚至激烈的骂声。“中医那期节目,挨了很多骂,老罗也回骂,一些人走掉了。也有会员觉得得到不想要的东西,退费离开。”
这个“人格魅力体”如何长久下去?罗申组合打算做10年,但在潮起潮落都很快的互联网,它的影响力能否维持,充满不确定,互联网的用户都像短期内就做迁徙的角马,迅速新鲜迅速疲惫,迅速从一个地点扎堆奔向下一个地点,驱使力常是资本。申音在想让《罗辑思维》“超越自媒体”,建立起有共同价值观的社群,老罗成为一个凝聚力的化身,稳固节目与用户的关系。但这样的设想,在互联网似乎还没有先例。
生意经
像信海光这样的自媒体人,感到未来可期待的想象空间还是颇大。从传统媒体到知名专栏作家,从博客到微博、微信一路走来,信海光见证了所有互联网媒体形态的起伏兴衰。他说:“不断兴起衰落也许就是未来的特征吧,没有恒常就是种常态。”他作为科技圈人士成为最早一批微博用户时,“与名人之间都相互关注,那时人少,有时间相互看,微博也很有人情味儿。现在人太多,也没工夫去看了”。开微信公共账号也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参与舆论,获得‘粉丝’,爱好社交,就推着往那儿走了”。一开始,也是玩票,学习内容制作、图片表现形式等,但很快他发现,微信是有潜质成长为个人可操作的媒体的:“微博是个舆论场,通过时间线生存,140个字,顶多有些图片和发条长微博;微信则可以承载更多内容,像个人杂志”。他开始对自媒体很专注地投入时间。信海光正努力成为一个把内容生产者与产品经理角色结合起来的全面人物。“当渠道与组织不存在后,你得运营自己。微信没有微博编辑推荐的功能,连个人界面都没有,就必须自己运作,形成联盟。”他也加入了一家最早的自媒体联盟,代理一些业务。除此之外,他对与“粉丝”互动、杂志封面设计、内容定位、发行运作、商业模式等,都必须有自己的策略。有时经营“粉丝”是件很费心力的事儿。他说,有一次回家晚了发了条微信,当时就有“粉丝”说,推送的声音影响他休息了,要退粉,让他比较郁闷。如何把一个内容生产者与一个经理人的角色分开?经理人的角色会剥蚀内容生产者的价值吗?信海光似乎还没考虑过这类问题,他对自媒体抱着点投机心态。(文 / 蒲实) 移动互联网曾航罗振宇罗辑思维申音自画像自媒体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