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与寂寞:梅艳芳的舞台人生
作者:王鸿谅 ( 2003年11月6日,“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行。梅艳芳穿上刘培基设计的白色婚纱演唱《夕阳之歌》
)
( 2003年11月6日,“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行。梅艳芳穿上刘培基设计的白色婚纱演唱《夕阳之歌》
)
“尽显光华”
红磡体育馆1983年落成,在里面首开个唱的歌手是许冠杰,3场爆满。彼时的梅艳芳还是娱乐圈新人,刚拿到TVB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出了半张唱片,6首歌。不过3年,梅艳芳就登上了红馆的万人舞台,而且一唱15场,创下了新人歌手首开个唱的纪录,也是当年的红馆记录。后来刷新纪录的除了谭咏麟和张国荣,就是她自己,从28场到30场,风光无限。
梅艳芳的首场个唱原定于1986年1月3日,筹备工作提前3个月开始。刘培基受时任华星唱片总经理苏孝良之托,接下了幕后重任,负责梅艳芳的形象设计和服装,并构思为演唱会预热的新唱片封套和演唱会广告海报。刘培基原本只是服装设计师,却跟娱乐圈结下不解之缘,80年代初从英国重回香港发展,在参与设计《赤色梅艳芳》和《飞跃舞台》两张梅艳芳个人唱片封套后,被苏孝良看中,成为华星唱片的形象指导。
演唱会定名为《梅艳芳尽显光华》,广告海报拍了两个版本,一张是梅艳芳的腿部特写,穿着镶钻的高跟鞋,斜伸出一条长腿,踩着一只镶钻的话筒;一张是手部特写,珠光宝气地握着话筒,不过,这只手是她姐姐梅爱芳的。当初拍的时候,“光是打灯已经花了两个钟头”,收工后,合作的设计师陈幼坚突然意识到漏拍了梅艳芳的手——举手投足,尽显光华。为了不影响梅艳芳的工作档期,就找了梅爱芳来帮忙。两个版本的广告同一天推出,都是报纸头版的整版广告位。
一个新人首开个唱,海报上却没有她的模样,真的可以吗?即便很信任刘培基,苏孝良心中也有些疑问,刘培基的回答很笃定:“如果加场,值得庆祝,便刊登有她样子的广告,这样才显得矜贵。”广告打出去,起初只发售4场门票,没想到迅速告磬。于是华星立刻加场,广告也换上了梅艳芳穿着华丽晚装的海报。场次一再增加,直至创下纪录的15场,门票全部抢光。刘培基回忆,“加至档期再无可加,唯有尽量把搭建舞台的时间缩短,提前在1985年的大除夕开锣”。
 ( 香港资深音乐人黎小田 )
( 香港资深音乐人黎小田 )
演唱会的监制是吴慧萍,负责整个流程,她在无线制作过许多精彩的音乐节目。刘培基与吴慧萍的组合,几乎就是1983年许冠杰红馆演唱会的翻版,当年也是苏孝良邀请刘培基来设计舞台服装。从吴慧萍那里,刘培基学到了很多,他说:“她令我领略到做演唱会的台、灯、音与服装结合的重要性,衣服无需钉上太多闪亮亮的东西,同样可以达到聚焦效果。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整晚流程,歌曲编排与每个细节,每部分有多少时间让歌手换衣服,当我决定衣服的颜色后,再与灯光配合。”“我遇上最好的团队,大家都处于最佳状态,不是金钱着眼,而是全心全意共同做好一件事。”
等到梅艳芳的首场个唱,刘培基第一时间就选定了吴慧萍做监制。“演唱会的第一场工作会议,在苏孝良家里进行,我正式介绍梅艳芳认识了吴慧萍。”面对以工作态度严谨行内有名的吴慧萍,梅艳芳下意识的反应,是挤到刘培基的单人沙发里一起坐,这让刘培基感叹,“说到底她也是个新人,难免有点怯生生的”。只不过,真的站到红馆的舞台上,万人瞩目,梅艳芳反而很镇定,刘培基评价说:“她已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镇定得一点也不像新人。”“她可以演绎任何歌曲,可以驾驭任何衣服。”
 ( 1982 年,19 岁的梅艳芳成为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 )
( 1982 年,19 岁的梅艳芳成为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 )
演唱会的重头戏,是一件钉满大颗闪石的晚装,为了搭配自己设计的这件礼服,刘培基专程从纽约有名的水晶店订购了一批水晶手链,所有的一切不惜成本,都是为了让梅艳芳“尽显光华”。15场演唱会结束,刘培基找华星唱片申请了另一笔广告预算,再次刊登头版广告,给梅艳芳“造势”,照片上的梅艳芳穿着那件闪石礼服,而刘培基想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梅艳芳亲自手写的“多谢”二字。刘培基回忆说:“我要求阿梅亲手写,她的字写得不好,其实这也是在意料之中,但我还是用了她的字,因为这代表了诚意,是真实的梅艳芳,她是捱出来的。”
新秀赛的机遇
 ( 梅艳芳在首场个人演唱会“梅艳芳尽显光华”上深情献唱 )
( 梅艳芳在首场个人演唱会“梅艳芳尽显光华”上深情献唱 )
TVB新秀歌唱大赛,是梅艳芳踏入娱乐圈的敲门砖,那是1982年。“当时无线电视来找我过去,说想做一个唱片公司,就是华星。”香港资深音乐人黎小田对本刊记者回忆,“我问他们有什么歌星,没有。当时我在丽的电视已经做了8年,所以决定用丽的电视的‘旧招’,搞歌唱比赛,我们曾经选出过一个张国荣,一个钟伟强。”张国荣自然不必介绍,至于第二名钟伟强,如果加上“中国好声音60岁的香港参赛选手”的标注,也许更为人知。
在位于半山的大房子里,音乐依旧是黎小田的滋养,坐在钢琴前,旋律从他指尖流淌,停下来,在发烧级配置的音响里放上一张他最新作曲的碟,回忆也变得轻快。“那是TVB的第一届新秀大赛,3000人来报名,我们听都听到烦死了。”他笑,“赛程好几个月,一轮轮淘汰,我也去找一些音乐届朋友介绍人。”当时的参赛条件很简单,“30岁以下,没有唱片公司合约的人都可以来。”有朋友介绍了梅艳芳。“他们说有一个唱得很像徐小凤的,在一个舞厅唱,在铜锣湾那边,总统戏院,我去听她唱,就是蛮不错的,我就去找她,问她有没有兴趣参加新秀比赛,她说‘你不认得我了,我以前参加过你的节目的’。”那是黎小田和薛家燕共同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就叫“家燕与小田”,梅艳芳和姐姐梅爱芳小时候来做过嘉宾,只是黎小田已经没有印象,他感叹,“原来她很小就出来唱,唱了很久了”。他也没有想到,虽然梅艳芳已经唱了这么久,唱到在夜场小有名气,却并不自信。“她说我怕,我说不怕,她说跟姐姐一起来,我说好。最后,她们一起来了,刷到最后100人,她跟姐姐都进了,张学友没进,被我‘叮’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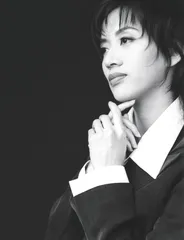 (
)
(
)
比赛选新人的标准是什么?黎小田说:“声,色,艺,三样都有最好。”如果不能齐备,那至少“男的要帅,女的要漂亮”,“最起码要高,五尺六寸到七寸,穿上高跟鞋,五尺九寸,一出场就压台嘛,那个气场很要紧”。张学友被“叮”走的原因,黎小田说,“他太丑了”。他找出来做对比的,是第五届新秀赛季军黎明。“黎明唱得不好也进了,为什么,他帅嘛。”时至今日,黎小田依旧很坚持对外形的挑剔,“声音再好,外形不好,也红不长久”。把这套标准放在梅艳芳身上,黎小田评价:“梅艳芳不算选手中很漂亮的,但她唱得很好,动作很好,舞台气场很好,她拿着麦,手指是会动的,我们叫body language,身体语言,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过一点就不行了。”“那时候我们十几个评委,黄霑、顾嘉辉、林燕妮等等,都是很厉害的人,都说她很好。”黎小田甚至对梅艳芳做出一个预测:“从新人来讲,再来十年,都不会出一个像她这样好的。”
决赛是直播,1982年7月18日,梅艳芳演唱了徐小凤的歌曲《风的季节》,她留着刘培基看来“老气俗气”的波浪长发,穿着华星给她准备的略微夸张的金色礼服,用低沉的嗓音打动了评委和观众,拿到了冠军。梅艳芳出生于1963年10月10日,比赛当晚还不满19岁,声音中却是超越年龄的细腻和沧桑。她的故事,也随着电视台一轮轮的比赛宣传,为更多人所知。自幼丧父,5岁出道,十来岁辍学,跟姐姐一起在母亲的歌舞团里唱歌卖艺,供养两个哥哥读书,一路从荔园游乐场唱到舞厅。80年代,刚好也是香港经济开始勃兴的年代,一切充满生机,机会无处不在,梅艳芳个人故事里蕴含的励志精神,刚好切合了时代的脉搏,成为典型的“香港梦”:出身草根,奋斗不息,终有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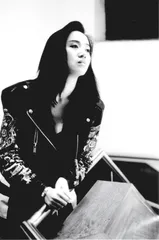 (
)
(
)
很多与梅艳芳合作过的人,都是从新秀赛开始关注她。香港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长彭志铭身兼数职,他是出版人、文化评论人,也是制片人,梅艳芳出演女主角的第一部电影《祝你好运》,就是他做制片人。彭志铭对本刊记者回忆:“其实梅艳芳还没有比赛前,已经听说过她,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星,在电视台里面也参演一些路人甲乙丙,临时演员。只是她样子不美,演点小角色也没有人特别注意。”直到新秀赛直播,“她真的唱得很好”。当时彭志铭在罗维电影公司,他回忆说:“我们是小公司,要很小心投资,我们看中梅艳芳一定会大红,因为这是TVB的第一届新秀大赛,她是第一名,电视台一定会让她红的,这是机构的因素。”
对于新秀赛,梅艳芳一直心怀感激,她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很多有才艺的人怀才不遇,而我却是个幸运的人,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更能够以沙哑的声音及丑样获得观众的喜爱,我相信因为我超越了自己的能力拼命地去搏。”她因此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我不是一下子暴涨的,我从小便入行,慢慢一步步才爬到今天的位置,自大的事情我不敢做,我怕有一天万一掉下来,自己会承受不了。”
 ( 梅艳芳与张国荣 )
( 梅艳芳与张国荣 )
投石问路
在黎小田的记忆里,80年代,香港娱乐圈还处在摸索的过程,连经纪人都是新生事物。“华星公司送我去日本,学习经纪人怎么做,那时候香港还很不流行经纪人,就是一个人带一个徒弟,我们做唱片公司,是公司制,要做一个团队,很多要学。”从日本学习回来,搞完新秀比赛,“跟梅艳芳一次就签了8年”。黎小田笑,“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心血的问题,这样我才会放心在你身上投资很多东西,请人来栽培你”。只不过,黎小田也记得,第一届新秀赛的选手里,“只有梅艳芳签了8年”。
对于梅艳芳的定位,一开始并不清晰。黎小田认真回想了很久,很坦诚地告诉本刊记者,“最初写歌给梅艳芳,真的没有过多的考虑,就是写什么她唱什么”。最初她甚至连《IQ博士》这样的儿童歌也唱过。梅艳芳第一首开始被传唱的歌曲是《心债》,TVB连续剧《香城浪子》的主题曲,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心债》刚上电台宣传,就占据了冠军位置,梅艳芳歌声如此沧桑,情感如此幽怨,又带着时代气息。华星公司这才决定给梅艳芳出唱片,投石问路。这张叫《心债》的同名大碟,只能算梅艳芳的“半张”唱片,她只唱了6首歌,另外6首,属于游林利、胡渭康和蒋庆龙的三人组合“小虎队”。
唱片封套是黎小田打电话请摄影师杨凡拍的,杨凡撰文回忆:“在利舞台的华星公司第一次见到梅艳芳。我对梅艳芳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苟言笑,她是个沉默的女孩,一般的应酬说话完全欠奉,问她一句她就答你一句,决不加油添醋和你周旋应酬。”“记得她穿着厚重的衣服,把全身包裹得密密实实,我们想看梅小姐真实的身材,也好替她造型,她则怎样都不肯把外套脱下来。黎小田说,可能这个女孩从小在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脱件外套也是一种障碍。”“回顾七八十年代的娱乐界,那时一切还没完全走上如今企业化的轨道,明星与歌星的形象基本上要靠自己,服装化妆首饰都得自备,许多时候我会到她们的府上去挑选适合的衣饰,当然也有某些公司借用,弄脏了还得原价买下。至于18岁的梅艳芳,当然不会让我登堂入室上梅妈妈在铜锣湾的唐宁大厦,翻箱倒柜地替她寻找适当的衣服。”“于是拍照的那天,梅艳芳穿了一套黑白宽边粗条的两件头,自己梳头化妆。我必须承认,看见那个造型,第一个让我想起的动物就是像斑马,实在没有灵感。”最后杨凡只能重拍,让梅艳芳换掉“斑马装”,给她设计了一款“乔治桑的男装造型”,勉强过关。多年后再看这张照片,梅艳芳是紧绷的,拘谨而倔强。
多年之后,杨凡坦陈了照片背后的另一个秘密。他当时一直想为新人梅艳芳寻找更好的拍照背景,看中了帝苑酒店的一家法国餐厅Lalique,那里“玻璃门窗都是法国Art Deco的人物图案,尤其大厅有两面落地镜居然浮雕了两个典型的Deco人物,陪衬着忽明忽暗的灯光”。这想法还没付诸实施,“又有另一家唱片公司老板来电,说是秘密签约徐小凤,还找了梁淑怡替她在伊利沙伯体育馆开演唱会,不惜工本让徐小凤来个形象唯美大变身”。唱片公司老板约杨凡在波斯富街的一家日本餐厅吃饭,杨凡说:“我提起最近要替华星新秀梅艳芳拍封面,借了Lalique。原本嘻哈谈笑中的老板,忽然间停了下来,数秒后说道:你不觉得徐小凤坐在那块Lalique玻璃下更美吗?”结果,“坐在那块Lalique双人雕花镜片下的不是梅艳芳而是徐小凤”。杨凡在后来自省:“这件事除了唱片公司老板和我,没有第三者知道,更别说徐小凤、梅艳芳和华星。我也肯定唱片公司老板忘了此事,因为他并没刻意要求我把雕花玻璃下的主角调换,他只不过提醒了我巨星与新人的分别,其余的决定就是我虚荣与势利的心魔。”
虽然照片一般,但唱片《心债》还是得到了市场认同,华星开始有底气给梅艳芳出真正的个人大碟,《赤色梅艳芳》。这张专辑中很多歌改编自日语歌,黎小田说:“因为那时候华星的陈淑芬跟日本大洋公司很熟,可以拿到很多日本歌,那时候香港很多歌手都翻唱日语歌,宝丽金公司也有他们的渠道,像谭咏麟、张学友也翻唱了很多日语歌。我们找了很多适合梅艳芳声线的歌曲给她,好几个歌都红了,尤其是《赤的疑惑》。”《赤的疑惑》是日本电视剧《血疑》的主题曲,原唱是山口百惠,改编给梅艳芳的时候,“降低了一点KEY,因为山口百惠的KEY比较高,梅艳芳要低一点”。黎小田回忆说:“从第二张唱片开始,我们对梅艳芳的歌就有选择了,因为听完《心债》,她适合唱的类型,是那种情感很幽怨的歌曲,‘快死了快死了,又死不断气’那种感觉。”黎小田觉得,这可能还是跟梅艳芳的个人经历有关,“可能是她经历过很多,苦过,所以看起来蛮幽怨的”。
“百变”尝试
“我觉得梅艳芳不只是一个出色的歌手那么简单,那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并不知道,所以打电话给刘培基。”这是华星总经理苏孝良的回忆。2013年12月,香港文化博物馆收藏了刘培基的设计作品开展,已经像“世外高人”一般的苏孝良不仅亲自到场,还配合展览需求,录制了一段视频,讲述梅艳芳的“百变”缘起。
苏孝良在视频里说:“在中环的文化酒店,Eddie(刘培基)讲了一大套理论,那时候,巨星的表演也看不到什么主题,刘培基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元素都集合到一起,配合唱片的需要、演唱会的需要来做包装。将作品与艺人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不只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因为苏孝良的引荐,梅艳芳才认识了刘培基。
第一次合作,刘培基给梅艳芳设计了东京音乐节比赛的造型,白色的薄丝棉袄,配黑皮裤,再加一条深色大围巾,兼顾时尚与民族感。第二次,就是个人大碟《赤色梅艳芳》。苏孝良说:“看到唱片封套,很震撼,封面看不到梅艳芳的大照片,好大胆。要是开会决定,一定通不过,但是我对他(刘培基)有100%的信心。”接下来是《飞跃舞台》的喷画设计。再到后来的《坏女孩》、《妖女》、《似水流年》……刘培基每一次出手,都令梅艳芳的形象耳目一新。苏孝良评价说:“这是刘培基对香港娱乐业的贡献,说到艺人的形象设计,他是创始人,有他帮手,整件事都不同了,没有刘培基,就没有今日的梅艳芳。”这或许是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因为刘培基的评价是:“如果没有苏孝良,就不会有今日的梅艳芳。”
从1982年梅艳芳新秀赛出道,黎小田就一直担任梅艳芳的唱片监制,他们合作了11张粤语专辑,直到1989年的《In Brasil》,因为华星高层人士变动,苏孝良、陈淑芬、黎小田等一干元老离开。在黎小田的记忆里,作为监制,他只管梅艳芳歌曲的品质。“每一张专辑,我们都要考虑歌曲的快慢搭配,这是将来舞台表演的需要。如果要上舞台,多一点快歌比较好,因为每一个show一开头,一定要有三个快歌,打动人家,一开场就是慢歌就不行。一定要两三个快歌,然后再是慢歌,过门比较长,让她缓一缓喘气,每一个歌星都是这样的。这是设计。”“我们主要做歌,‘百变’是刘培基的事”,“每一次刘培基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每一次唱片封套出来,我们都觉得非常好,跟音乐很配”。
刘培基的灵感,来自梅艳芳的音乐和对她逐渐加深的了解。“每一张专辑,听一曲主打歌,听一遍,感觉就有了。”他和梅艳芳之间的默契,在长达20年的合作中不断累积,已经到了不需要言语,彼此几个眼神就心领神会,刘培基觉得,这也是缘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奇妙,从一开始,她已非常信任我”。
不过,在文化评论人彭志铭看来,刘培基与梅艳芳的合作,应该称为“彼此成就”。“刘培基的设计要成功,一定要那个人能够承受这个力才可以。如果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人,你怎么做,观众都不接受,就是失败的。但梅艳芳有这个魅力,她有控制人家承受的力量。”彭志铭解释说,“反潮流才是潮流,她的每一次反潮流,变化也许不一定好,但她可以带领这个潮流,每一次人家都能认同,这才是她的厉害。比如她有一个新造型是粗眉毛,其实并不好看,但你去找那时期的电影,其他女明星都学她,个个在影片里眉毛都很粗,这就是大家认同她,她能托得起新潮流。”这也是梅艳芳与张国荣的不同,“张国荣跟潮流,但他是潮流里能做到最极致的那一个”。
巅峰光芒
“娱乐界是偏门来的,七十二行之外才是演艺界,不是正行来的,所以你漂亮也好,帅也好,唱得好也好,不红就不红,是命。”为什么那么多届新秀赛办下来,最出名的只有一个梅艳芳?黎小田想了很久,给出的答案有些宿命论。
新秀赛只是娱乐圈的入场券。第二届比赛的冠军是吕方,也是黎小田一手发掘的,那时候吕方参加TVB的表演,“唱什么《中国人》之类的歌,我就打电话到无线的化妆间找他,说你唱得不错,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新秀比赛,我说我是黎小田,他吓得电话都掉了”。吕方决赛最后唱的什么歌,黎小田记不得了,但他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唱完歌,观众鼓掌叫安可,比赛哪有安可啊,梅艳芳当年比赛都没有这样的效果。”这场比赛,彭志铭也记得:“吕方现场唱得太好,第一名不可能不给他,可是他不可能像梅艳芳一样红的,他不算帅,个子也不高,可塑性也没有梅艳芳好。”这些黎小田自然也很清楚,单纯的好声音在娱乐圈不可能走得太远,“吕方也只红了几年就没有了”。
再回想起来,刚出道的梅艳芳其实也不被看好,黎小田记得:“陈冠中有个杂志叫《号外》,有个专栏叫Dress to Kill,专门讽刺明星的衣着,有一期的照片就是梅艳芳,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刘培基。”香港乐评人黄志华则告诉本刊记者,梅艳芳的第一张专辑《心债》发布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报馆做记者,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利园酒店,现在已经拆掉了。当时去的记者不多,梅艳芳也很拘谨,“不太会应对记者”。那时候,他的主编就“很不看好梅艳芳”。黎小田倒不是很看重这些,他觉得媒体与娱乐圈的关系,就是“越不红就踩得越厉害,越红就捧得越厉害”。
梅艳芳是个异数,在香港女歌手的排序里,她像一个断档,在她之前,红得发紫的是徐小凤、甄妮这样的前辈,然后她出现,女歌手里再没有人能与她比肩。黎小田觉得,梅艳芳是天生的属于舞台的歌手,“台型好”,“容祖儿也算能唱能跳,但就是没有梅艳芳那么压台”。第一场红馆个唱的15场纪录,证明了梅艳芳的舞台魅力,她成了华星的掌上明珠。在刘培基看来,“1987到1988年,可以说是梅艳芳演艺生涯的巅峰时期”,“唱片销量好,人缘佳,形象百变,舞台上挥洒自如,我觉得当时她的状态好到无可挑剔”。
1987年底的28场跨年演唱会,定名《梅艳芳再展光华》,不过是第二次重返红馆开唱,梅艳芳已经创下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演唱会纪录,也得到了“梅廿八”的美誉。这次的演唱会由陈家瑛担任监制,10个环节,刘培基每环节都为梅艳芳设计两套衣服。演唱会以《冰山大火》作为序幕开场,其中《伤心教堂》一曲的两款造型,一黑一白,都类似“婚纱”。梅艳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伤心教堂》是每次都会令她感触落泪的歌,“灌唱片时也有流泪,我不希望像曲中的人那样,嫁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如果幸运的话,一生人只会嫁一次,希望将来的婚礼,能够隆重其事,在红馆设一百桌喜宴”。
28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夜,她披上黑色纱裙献唱《伤心教堂》,刘培基回忆:“不止泪如雨下,还有点泣不成声,以致影响了声线,歌迷不断高呼‘不要哭,我爱你’。没有人知道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刘培基在自传《举头望明月》里有详细记述:“踏入午夜零点,28场演唱会结束。圈内外的朋友挤满了化妆间门外,等候他们的‘梅姐’换衣服去庆功。华星交给我一张支票,那是梅艳芳演唱会的尾数……当支票交到她手上,她望着我,豆大的眼泪滚流而下,我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你不知道今晚外面有人追债么?’”
“我当然知道。她因为替人做担保,借钱的人不还债,放债人就来向她追讨。”“一场的歌酬,又怎够偿还那数百万的欠债?不过,最令她伤心的并不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想不到那个人会如此不负责任,这对她来说才是最大的打击。”“庆功宴上,她与干爹何冠昌同坐,未几,有人来找我,说阿梅在哭,要我过去看她。大家都以为她因为被人追到红馆追数而落泪,却不知道她刚刚收了歌酬,翌日便要用自己的血汗金代人还债。”“我怜惜地看着她,真不懂得如何安慰这孩子。”
告别与复出
舞台上的风光,与现实中的一团乱麻,总是这样交织在梅艳芳身上。人生如戏,在她身上能找到最好的注解。在彭志铭看来,从小唱歌卖艺的梅艳芳,是旧式江湖里历练出来的,所以有旧式江湖儿女的典型特征,“真性情,重情义”。她出手豪爽,逢单必买,有求必应,一张张支票开出去,很快成了“大姐”,只是围绕着的她的很多人,心里的算盘太清楚,并不配这样的真心相待。
亲情上,除了姐姐梅爱芳,她与总是欺骗她的其他家人已经日渐疏远;爱情上,虽然她总是高调又奋不顾身,却总是落得最后的遗憾。这种感情上的缺失,终究是舞台无法弥补的。相反,舞台上的声名反而像一个巨大的爱情障碍,横亘在她和她那些不那么著名的男朋友之间。她说她想做山口百惠,只是并没有与她相称的三浦友和。经历了1988年巅峰,她的事业也开始不那么如意。一方面是源自她的脾气,因为彻夜疯玩不爱惜身体,她迟到的时间越来越长,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更换制作人之后,她的唱片市场有所变化,销量下降。《镜花水月》之后,她想出一张经典老歌翻唱,但是华星却不同意,刘培基亲自去跟公司的人商谈作保,才帮梅艳芳争取到了《似水流年》。
“我也不明白,我唱了那么多年歌,对这个圈最少都有一点贡献,为什么,在我的唱片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候,人人都要踩一脚?”梅艳芳开始感受到落差,舞台的诱惑在缩小,而内心的缺失在放大。1991年初夏,梅艳芳去伦敦表演,刘培基无意间听到她跟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她对着电话那边的人柔声说,‘你不要做得那么辛苦,我来做就好了,我捱就可以,你不用捱……’”刘培基说他很震惊,连珠炮似的责骂了梅艳芳:“神经病!你是否想做个男人?以后是否要称呼你梅先生?”梅艳芳没有怎么辩解,反而跟刘培基说了另一番话,她想退出,“我已经很累,不想再做下去了”。
面对刘培基的追问,梅艳芳再三表示自己的积蓄足够过活,不会后悔,刘培基也就“不再查根究底”。刘培基回忆说:“她四五岁已经在游乐场唱歌,唱了20多年,觉得累是可以理解的,我11岁学做裁缝,快30年了,何尝不累?我明白她的心态,虽然我花了全副心思栽培她,但我知道,不应该再规劝或者勉强她。”当梅艳芳把退出舞台的想法告诉华星,全公司上下都震动了,但他们无法说服她。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1991年12月23日在红馆开唱,一共30场,直到1992年1月27日结束,再次刷新纪录。但是这次的演唱会刘培基并不满意,因为梅艳芳执意要做“麦当娜”,他做了让步,满足了梅艳芳的模仿心愿,但身为设计师的骄傲并不能自我认同。
宣布退出舞台的梅艳芳只有29岁,熟悉她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疑问,能守多久?刘培基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山口百惠,可以那么年轻便不再恋栈舞台上的光辉,我觉得阿梅并不享受退休生活。”“她没有开口说后悔,也没有说日子过得闷,但从她的言行中,我隐约体会到她的感受。”终于,1994年4月,梅艳芳推出了新唱片《是这样吧》,外界已经揣测,这是她要复出的第一步。到了1995年初,复出已成定局。在刘培基看来,这是梅艳芳的一次人生转折。
热闹中的孤单
刘培基记得很清楚,2002年12月6日,罗文尾七刚过,他从香港回到泰国家中,“伤感的情绪仍未放下,凌晨2点多,接到梅艳芳的电话,‘今天收到体检报告,医生说不太好’”。确诊是宫颈癌,虽然梅艳芳展现出了极大的求生意志,与病魔抗争,她最终还是没能熬过2003年,12月30日凌晨,她还是离开了。
刘培基给梅艳芳设计的最后一身服装,是她的寿衣,用象牙色的真丝缎,做了一套旗袍。灵堂上的照片是《是这样的》那辑专辑里的黑白照片。刘培基致悼词,他写道:“梅艳芳最大的优点,是她的善良……”这是一种最高褒赞,但梅艳芳担得起。她受过很多苦,一点一点捱出来,对于钱财却看得很淡,她经历了太多欺骗,从来都是人负她。刘培基说她是“女孟尝”,门客三千。不管谁找她借钱,不管是多么拙劣的理由,她都很爽快。她身后留下的支票簿存根,总额高达数千万。人人都看她赚钱容易,却不知道她承受的心理压力。刘培基记得,梅艳芳确诊宫颈癌后,曾经告诉他:“就算不踏出这个门,供楼、我的制作公司,养活自己和其他人,每个月的开支大约需要50万……我也不过是个女人。”在住院接受化疗,因为并发症声带受损后,梅艳芳最惊恐的却是,如果不能再唱歌,以后就没有谋生手段了。这些都让刘培基心如刀割。
梅艳芳年轻时的那些莽撞和疯狂,真正的朋友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黎小田说:“可是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劝一次不听,也就不再多说了。”他只是感慨,“梅艳芳很有悟性,如果她身边刘培基那样的朋友多一点,她会领悟更多,成就会更大。”“什么样的朋友,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人。”黎小田说,“我跟陶杰是朋友,他会影响我看很多书,看很多电影。但梅艳芳身边那些普通朋友,我是最不赞成的,每一个就跟她说阿姐,叫她买单。我不像草蜢,整天跟她泡吧去玩,我是不去的,我不喜欢。自己要有自己的修养,我一个人可以在家安静听音乐看书的,但梅艳芳就做不到。”“她太喜欢热闹。可是你热闹完了,要一个人回家的,那你回家会怎样?我劝过她的,每天都出去干吗?每天都有人陪她吃饭,每顿都是她买单,‘你是赚钱多,你是大姐大,可这样是不对的,每个人都赞你好,是不对的’。”
自梅艳芳走后,她的母亲和大哥针对她的遗产,打了持续10年的官司,把她风光世界的另一面彻底挑破在众人面前,一地鸡毛。两个哥哥以各种名目,依仗着母亲的威严,没少从梅艳芳这里拿钱。等到她挚爱的姐姐梅爱芳因宫颈癌病逝,亲情裂痕再也无法弥合。在住院接受治疗的最后两个月,梅艳芳做出了遗产分配方案,成立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支付4名外甥和外甥女的高等教育费用,支付她母亲每个月7万港元的生活费,让她保持一个专职司机、两名佣人的生活水准,直到过世。将香港和伦敦的两套房产留给刘培基,然后,所有的财产捐给一个佛学会。她在立信托基金和遗嘱的时候,跟见证人说得很清楚,不希望她的钱,落到除基金受益人之外,任何一个梅家人手里。
“热闹中的孤单。”这是导演关锦鹏对梅艳芳的描述。他对本刊记者感慨:“我常觉得,好的艺术家个性使然或者命中注定,是要孤独跟寂寞的。她活得特别累。家庭并不是她的避风港。台前风光背后,这中间有很多留白给观众和朋友,真正有多孤独跟寂寞,可能她可以自己排解,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甚。”
(参考资料:刘培基自传《举头望明月》)
(文 / 王鸿谅) 赤色梅艳芳黎小田百变人生刘培基寂寞心债娱乐八卦舞台演唱会唱片制作梅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