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中的“小人物与现实”
作者:黑麦 ( 《钢的琴》剧照 )
( 《钢的琴》剧照 )
《王二的长征》刚刚完成它的首演,走上了全国巡演。剧中,4米高的阶梯围绕着舞台,王二携带的书信被放大为背景幕,一路上,“革命者”王二遇到了企图创造新世界的“同志们”:他们中有19岁的团长“老革命”、不甘心做姨太太的“文工团”、戴着十字架的“大鼻子”、为诗歌而革命的“自由颂”、红军的俘虏“反动派”等人,在长途跋涉中,王二成长为战士,他似乎也更加明确了这个征途的目的。三宝最中意的一篇剧评这样写道:……经过岁月洗礼,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初加入长征队伍的初衷?
按三宝的话说,《王二的长征》不是一部简单的红色戏剧,“它更具有现实意义”。他和编剧关山都是“体制外人”,做这样一部“红色主题”的音乐剧并非必要,而戏剧最终成形,是因为他对革命者和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三宝说:“革命的初衷源于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它真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情感和信仰。《王二》之后,我们会依据当时的‘环境’创作‘红色三部曲’,未来两部的题材可能是中国的音乐家或者作家。”
早在1998年,三宝便排演过《新白蛇传》,在对音乐剧概念尚不清晰的时代,这部被称为“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的《新白蛇传》连演3年共计900多场,到深圳21世纪演艺中心去看《新白蛇传》,曾经成为当地人的一股文化潮流。那时,三宝是圈内炙手可热的作曲者,凭借不计其数的打榜歌曲,他的“流行音乐身份”也被多数人所熟知。但是在2005年后,他几乎暂停了所有的影视音乐创作,“告别了流行音乐圈”,一头扎进不被人广泛关注的音乐剧。
2005年,《金沙》成为三宝音乐剧的“又一种尝试”,这部半命题剧最终也演变成为成都的名片。《金沙》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此也掀起了中国音乐剧的创作热潮。也正是从《金沙》开始,三宝对音乐剧有了更多理解。他说:“在做《金沙》时候,我更注重演员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歌手里挑演员,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了音乐的完整性,但是在这部戏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舞台的某种完整是光凭歌手优质的嗓音无法弥补的。”
此时,三宝与编剧关山也确立了之后的写作方向——摒弃“宏大”的题材。“人们提到音乐剧时总会联想到大爱、古典浪漫、史诗、魔幻、神话这些字眼儿,我觉得大的东西很空洞,我们想做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反应他们的生存环境。”两年后,那个被推敲了多年的剧本《梁祝》,最终被这对组合改写成为一部名为《蝶》的“小故事”。“我们只保留了主人公的名字和最后化蝶的桥段。”在《蝶》中,三宝用“宣叙调”代替了对白,他说,“我用了3年时间来写这部音乐剧,剧中的每一次开口都需成为音乐,对情感的转折要经得起反复推敲。”然而,今天的三宝对当初的这个做法有些“疑虑”,他认为剧中的“情感使用”显得有些“铺张”,“我有太多想说的话,结果都被注入到音乐和剧情中,让人抓不到重点”。

这部耗资近4000万元的大型音乐剧上演时,团队中似乎也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其间三宝坚持指挥着由41人组成的现场乐队。2007年9月20日,当《蝶》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三宝也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了协和医院,然后又被转入阜外心血管医院。住院期间,关山来探视,当二人谈到剧本时,三宝似乎更坚定了做音乐剧的某种想法。在《蝶》以后,他与关山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静养的两年中,三宝经常出入北京的小剧场,也偶尔在美国观摩音乐剧,他在42街看腻了“给游客表演的百老汇音乐剧”如《妈妈咪呀》、《歌剧魅影》等,辗转来到纽约大学附近,开始观看“外百老汇音乐剧”,一部名为《春光乍现》(Spring Awakening)的音乐剧对他有了启发。“这是一部曾经获得托尼奖(Tony Awards)的作品,它讲的是高中生对性的认识,我认为它想表达的是教育制度的禁锢。”吸引三宝的,不只是剧情,还有这个剧团“因陋就简”的制作水准。“舞台简单至极,没有天幕,乐队不过5人,表现方式尤其有趣,一些观众就坐在舞台上,当演员没有戏时,他们就一并坐在一起,整个剧打破了音乐剧的常规。”从纽约回来,三宝看了《雾都孤儿》,便和关山着手准备《三毛流浪记》。
 ( 《三毛流浪记》剧照 )
( 《三毛流浪记》剧照 )
在三宝的印象中,张乐平笔下的那个大头小身子男孩,就是华人社会中广为人知的“小人物”,他的故事与当下的青年人有某种相似。三宝说:“这个漫画作品虽然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但它所表达的是成人世界、社会阶层对每一个人的影响,虽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却与今天相似。”于是,在这场“三整一律”的剧中,三毛的故事被“减法”成一个主题——饥饿。当深色丝绒大幕开启时,歌声便响起:“如果石头不会磕碎牙齿,如果玻璃不会划破舌头,我要把它们全部吃下肚子里……”“剧情也讲述了现代故事”,关山将拆迁、选秀、物价上涨等现实话题融入剧情,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在观看演出后说:“这是一出笑中带泪的音乐剧。”
剧中没有脸谱化的“坏人”,“一切坏事情都事出有因”,三宝也比以往更加注重音乐在剧中的细微情绪。“音乐可以辅助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剧中,当三毛被巡捕带往警局时,他的内心活动是终于能有吃的了,因此我用了一种类似行军的音乐,听起来是昂扬并非悲伤的。”

为了不使音乐“抢占表演”,三宝这次所选的多数演员多是表演系出身,一水儿的新面孔。“70%以上我都很满意。”他说。对于音乐一向苛求的他,似乎也终于放弃了某种标准。“只要声音不触及我的‘底线’,我就能通过。”当然,三宝的“底线”并非降低水准。他补充道:“我在美国看戏时,偶尔也会用专业音乐人的标准去衡量台上演员,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能达到专业演唱水准,但我认为,这些演员有一种舞台‘技能’,他们能通过自己的表演来掩饰这些‘瑕疵’。”
三宝于是逐渐在音乐剧中为音乐“找到角色”,2012年末,当《钢的琴》上演时,它的声音开始“变得立体”。全剧包括了18个唱段,“摇滚乐的粗糙和金属感能体现出工厂的氛围;二人转的演唱能表现出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三宝认为《钢的琴》有着深深的年代感,以及浓烈的工人阶级情怀,“强烈的节奏能让人感到力量”。
 ( 三宝作品: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剧照 )
( 三宝作品:音乐剧《王二的长征》剧照 )
《钢的琴》演出后,三宝曾参加过一个音乐剧研讨会,一些音乐剧从业者和剧评人的发言都是从“对题材感到意外”谈起的。三宝说,从《音乐之声》进入中国开始,很多人对于音乐剧有了一种“框架式”的认识,音乐剧被赋予了过多的标签和属性。“很多人还对我没有为《钢的琴》写一曲能流传下来的音乐或歌曲感到遗憾。在我看来,那些容易被记住的音乐往往不能摆脱‘俗’的成分,也许我是故意没有写出这种音乐来,毕竟音乐剧不是用来打榜的。在音乐剧的100多年历史中,真正被传唱下来的‘金曲’也屈指可数,每一首曲子的成名都是由多个条件组成的。”
三宝和关山合作了6部音乐剧,创作时,两个人住在一起,逐渐生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感似乎来自他们对舞台的理解。“王二这个角色是我和关山很早碰出来的,他的社会属性很强,是在任何时代中都能找到的人,他看似有着结实的肩膀,却总耷拉着脑袋,他心中有个老爷,却也能为自己找到曙光。”三宝说,之所以叫他“王二”,是因为他普通,像三毛、陈桂林(钢的琴),“也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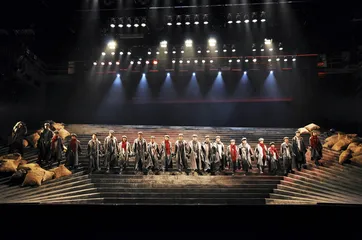
三宝用歌、演、颂三种表达方式串起王二的长征路。“音乐是时而重型时而阴郁的,我用摇滚乐、电子乐和Trip-Hop舞曲来表达情绪的起伏,热烈和阴郁,我们通常看到的‘红色主题’音乐往往是磅礴和积极向上的,我可能是第一个这样表达‘长征’的人。”在剧中,三宝还用到了舒伯特的《圣母颂》和《国际歌》。他说:“我和关山都有一个情结,就是在音乐剧中演绎一次《国际歌》。在故事的结尾有一组对话:‘我们到了陕北,你干啥还要走?’‘我去前线,一直走,跟着各省走。’几个声部错落着,最后一齐唱起《国际歌》。”
在三宝看来,音乐剧本身没有固定型态,它的魅力在于现场和互动。“我不敢说我有多少经验,但我坚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想打破我们所认识的‘主流音乐剧’,这么多年,很多人还停滞在判断某个剧是否应称之为音乐剧的阶段,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音乐中找到主线,找到自己。”
 ( 三宝 )(文 / 黑麦) 三宝小人物现实国际歌音乐剧艺术钢的琴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
( 三宝 )(文 / 黑麦) 三宝小人物现实国际歌音乐剧艺术钢的琴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