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罗斯曼、兰迪·谢克曼、托马斯·聚德霍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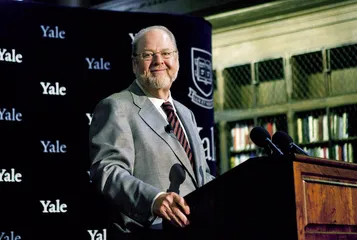 ( 10月7日,在美国纽黑文市,获得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罗斯曼出席新闻发布会
)
( 10月7日,在美国纽黑文市,获得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罗斯曼出席新闻发布会
)
“为了确保货物在合适的时间被运送到正确的目的地,一个繁忙的大港口需要仰仗多个运输系统。同理,一个被分隔成不同单元(学名细胞器)的细胞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细胞产生的很多分子,比如激素、神经递质、细胞因子和酶等,需要被运送到细胞内的其他地方,或者被运出细胞,送到体内的其他地方。不管是细胞内还是细胞外,所有的分子都要在正确的时间被转运到正确的地点。”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宣布2013年度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后刊出的新闻稿,该文把细胞比作港口,把分子比作货物,方便大家理解这三位获奖者所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类似的写法在很多科普文章中都能见到,这么写虽然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深奥的科学问题,但弄不好会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给读者留下错误的印象。
比如说,经常有科普作者把人体比作一支军队。在他们的笔下,细胞们仿佛都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士兵,按照司令官(大脑)发出的指令行事。这样的写法虽然可以形象地表现人体各种生理活动协调一致的情况,却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大脑通过一种类似无线电波的神秘方式下达了指令,而聪明的细胞则从五花八门的电讯号中找出发给自己的那条,然后按要求行事。但实际上人体是一架化学机器,这些指令都是以信号分子的方式传递的,接受指令的细胞也没有任何分析能力,而只是通过简单的生化反应来接收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动作,不存在“智慧”问题。
今年的这三位获奖者各自通过巧妙的方式,揭示了这套生化反应的机制,并为很多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科学基础。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谈谈每位获奖者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从中可以了解生物学研究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以及背后的原因。
詹姆斯·罗斯曼——从观察到实验
 ( 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教授兰迪·谢克曼在家中 )
( 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教授兰迪·谢克曼在家中 )
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首先来自双眼,观察是最古老的研究手段,也是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早期生物学研究的绝大部分突破性成果都是来自观察方法的革新,以及观察技术的进步。比如,古人曾以为心是意识的所在地,肾是“气血”的发源地,直到有人勇敢地尝试人体解剖,这才终于搞清了五脏六腑的真正功能,并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生理学。以前人们只能用肉眼观察,显微镜的发明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人们终于明白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生物学从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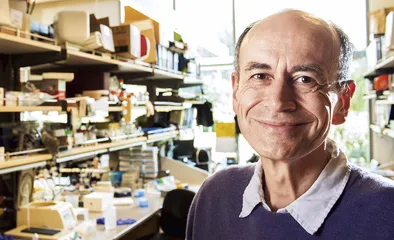 ( 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聚德霍夫
)
( 2013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托马斯·聚德霍夫
)
早期显微镜的分辨率有限,以至于当时的细胞生物学家们以为细胞就像是一锅浓汤,里面漂浮着若干个功能元器件。随着光学显微镜的精度越来越高,尤其是电子显微镜的出现又将分辨率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科学家们终于意识到细胞内部更像是办公室的格子间,被一层层脂质膜分隔成很多单独的工作室,各自执行不同的功能。比如细胞核负责储存DNA,也就是生产蛋白质的图纸;线粒体负责生成能量分子(ATP),为各种生化反应提供能量;内质网(Endoplasmic Reticulum)好似工厂,负责生产蛋白质;高尔基体(Golgi Apparatus)则很像是物流中心,负责对刚刚生成的蛋白质进行必要的修饰和包装(比如添加糖基),然后分发到需要的地方。
细胞内甚至还有专门的废品回收站,学名叫作溶酶体(Lysosome),负责把没用的蛋白质收集起来分解成氨基酸重新利用。
如此复杂的结构需要配备一套专门的物流系统,电子显微镜揭示出这套物流系统是由囊泡(Vesicles)组成的,它们在显微镜下就像是一个个体积很小的圆球,外表是一层脂质疏水膜,需要运送的货物就包在里面。观察显示,囊泡的形成过程很像是中学生都学过的酵母菌出芽生殖,即先在母体上形成一个凸起,然后体积逐渐增大,根部逐渐收紧,最后和母体断开,成为一个独立的囊泡,裹着货物奔向目的地。到达指定地点后,囊泡外表的那层膜和接收方的表面膜发生融合,从而释放出携带的货物,这个过程和出芽生殖正好相反,很容易理解。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真核细胞内部的运输系统都是由囊泡组成的,细胞之间的运输系统也是如此。生命体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生物膜都是由相同的脂质分子组成的,彼此间很容易相互融合。
那么,关于这套细胞运输系统的研究做到这里就完事了吗?远着呢!上面的描述都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镜头下的囊泡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准确地到达指定地点。但实际上囊泡都是体积很小的化学分子,没有智慧,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行为都是在简单的生化反应支配下完成的,这才是生命最奇妙的地方。不过生化反应是在分子尺度下进行的,超出了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此时光靠观察就没用了,必须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才能发现其中的秘密。我们的第一位英雄詹姆斯·罗斯曼(James E.Rothman)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
罗斯曼于195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76年他从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博士后,并于1978年前往斯坦福大学,开始研究囊泡。正是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期间,也就是1980年,罗斯曼发明了一种方法,成功地在试管里实现了细胞外的囊泡自主生成,为下一步的生化分析奠定了基础。
所谓生化分析,就是把一群相同的分子集合起来在试管里进行化学反应,通过这个办法把发生在细胞内的某种生物化学过程放大,以此来达到显微镜达不到的效果。这就要求生物学家首先必须拿到大量纯度很高的样本,专业名词叫作“提纯”。正常细胞内虽然有很多囊泡,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其他蛋白质,如果不加提纯很难进行生化分析。罗斯曼经过多次试验后,成功地在细胞外再现了囊泡生成的过程,这就相当于把细胞内的其他不相关成分都去掉了,只留下囊泡生成过程所必须的基本元素,这样一来科学家就可以通过简单的生化分析,找出囊泡生成过程所需要的所有元素,进而从分子水平上解释这一复杂的过程。
换句话说,这也是一种“观察”,只不过被人叫作“实验”而已。
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罗斯曼利用这套系统把囊泡的生成和到达目的地时的对接过程全部搞清楚了。具体说,他找到了囊泡生成过程所需要的所有蛋白质,阐明了这些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还研究了囊泡到达目的地后与目标膜发生融合的过程,发现这一过程很像我们所熟悉的拉链,即囊泡表面的某种蛋白质与目标膜上的相应蛋白质像拉链一样结合在一起,然后双方发生融合,囊泡将内容物释放出来,交货完成。
从此,那个在显微镜下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操纵的囊泡再也不神秘了,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生成出来,并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目的地,完全是分子之间的特异性相互作用所致,可以用简单的化学原理加以解释。
有趣的是,当罗斯曼通过生化实验找出细胞运输系统所需蛋白质后,发现早有一人通过其他方法也把它们找出来了,此人的名字叫作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是一位比罗斯曼更早出场的英雄。
兰迪·谢克曼——基因分析的力量
兰迪·谢克曼于1948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197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分子生物学本科学位,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亚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当时DNA的秘密刚被揭开不久,这其中就有科恩伯格博士的贡献,他搞清了DNA分子的合成机理,解开了染色体复制的谜团,科学家们首次学会了如何解读生命的密码,这使得分子遗传学领域聚集了大量人才,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正是在这股热潮中,谢克曼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开始研究细胞运输的机理。当时人们已经通过电子显微镜发现了囊泡是细胞运输的工具,但具体细节几乎一无所知。谢克曼决定用刚刚诞生不久的基因分析法研究囊泡,这就首先必须找到有缺陷的细胞。
谢克曼的思路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极为常见,理解起来一点也不困难。试想你领导着一个团队,想知道这个团队中哪个人的作用最大,你会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让他去休假一段时间就行了。如果团队人数太多,试不过来怎么办呢?答案也很简单:分析一下过去的失败案例,看看当时有哪些人正好在休假,答案自然也就清楚了。
这两个研究思路之所以在生物学领域被广泛使用,主要原因就在于基因研究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前一种情况,如果你想知道某个蛋白质到底有什么用,只要把与之相对应的基因关闭就可以了。对于后一种情况,就是先想办法找出功能缺陷的个体,然后分析到底哪个基因被关闭了,这在技术上也不是一件难事。
谢克曼就是这么做的。他首先诱发酵母菌发生基因突变,然后从中筛选出货物运输出现异常的酵母菌,这些细菌身体内聚集着大量囊泡,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调度失灵的码头,集装箱不知道该往哪里运,只好胡乱堆放在仓库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遗传学特有的优点了。谢克曼通过分析比较突变酵母菌和正常酵母菌的DNA序列,找到了突变的基因,再顺藤摸瓜,找出相应的蛋白质。谢克曼将这个筛选过程重复了很多次,找到了所有与细胞运输有关的蛋白质,从而构建出了整条运输线的生物化学过程。从此后,细胞运输领域的研究就从纯粹的形态描述转为对分子机理的研究,囊泡的神秘性被打破了。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谢克曼和罗斯曼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生物系统里却找到了如此相似的蛋白质系统呢?答案也很简单:细胞的货物运输是维持生命体正常运作的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为它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不可能改变太多,这种特性在生物学领域被称为“保守”。后来的研究多次证明,生命过程中越是重要的部分也就越保守,DNA的复制和遗传,以及蛋白质生产和运输等等这几个至关重要的部门是最保守的,在各种不同等级的生命体当中变化非常小。
谢克曼和罗斯曼把细胞运输的生化过程基本搞清了,接下来就该把成果应用到实际中去了,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Südhof)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托马斯·聚德霍夫——时间就是一切
我们的第三位英雄托马斯·聚德霍夫于1955年出生在德国的哥廷根,1982年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和神经化学博士学位。1983年他前往美国,在位于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结束后他在该校谋得一个教职,潜心研究神经递质的传递过程。
人们很早就知道,神经细胞是通过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相互联系的,负责发出信号的上游神经细胞将神经递质裹在囊泡里,通过和细胞外膜的融合把神经递质释放到细胞外,被下游的神经细胞接收。此前的神经生物学家们大都把注意力放到了后半部分,即下游的神经细胞是如何接收信息的,但聚德霍夫另辟蹊径,决定主攻这一过程的上半部分,即负责运输神经递质的囊泡是如何形成并释放的。
初看起来这项研究没什么新鲜,和前两位相比甚至有些重复,但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难点。首先,神经细胞不能分裂,培养起来也很困难,因此也就很难获得大量的实验材料,极大地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其次,神经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速度太快了,到底有多快呢?想想人类的反应速度就知道了。事实上,人脑细胞的反应速度是以微秒来计算的,这个时间尺度是生物学研究的短板,聚德霍夫挑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就越容易啃出花样。在潜心研究了20多年后,聚德霍夫成功了。他证明上游神经细胞接到信号后会迅速打开细胞表面的钙离子通道,让细胞外围的钙离子扩散到细胞内,与突触结合蛋白(Synaptotagmins)相结合,启动囊泡释放神经递质。这个过程不但速度很快,而且非常准确,完全符合神经细胞的需要。
后续研究表明,这套精密的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各种神经疾病,比如早老性痴呆和自闭症,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但目前尚属不治之症,科学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争取早日找到治疗方法。
结语
任何一个复杂系统,一旦物流或者信息交换出现问题,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人体也是这样,有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糖尿病、免疫紊乱和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于物流不畅所导致的,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做的贡献可以帮助医生们更好地对付这类疾病,最终造福人类。(文 / 袁越) 生物技术医学研究获得者霍夫诺贝尔医学奖兰迪聚德科学谢克诺贝尔生理学2013蛋白质结构医学托马斯蛋白质詹姆斯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