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
作者:薛巍 ( 安东尼娅·麦卡洛 )
( 安东尼娅·麦卡洛 )
心理学与哲学:从分离到融合
朱利安·巴吉尼是英国《哲学家杂志》主编,安东尼娅·麦卡洛是英国知名心理治疗师,他们合著了《心理学家和智者:现代困境指南》一书。在全书的上篇,两人分别回答了如何面对20种人生困境,包括:为什么追求完美的生活却越来越混乱?为什么一直追赶目标,却永远是失败者?为什么信奉婚姻忠诚却无法抗拒诱惑?到底应该谦虚谨慎,还是要高调做人?为什么下定决心后总是无法坚持到底?为什么对于过去,心中总有无限后悔和遗憾?这些问题有的并不重大,甚至有些多愁善感,有的又太重大,如最后一个问题:“活着如此空虚,人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下篇是两篇短文,分别是《哲学家眼中的心理学》和《心理医生眼中的哲学》。两位作者都认为,为了帮助人们应对人生困境,哲学和心理学应该相互补充。
巴吉尼说:“在人类文明的最初几千年,并不存在哲学和心理学之分。直到19世纪,实验心理学才开始独成一派。虽然这两个学科的分道扬镳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在1913年这两者提出了一次‘离婚’申请。当时107位德国、澳大利亚及瑞士哲学家联名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不再将哲学教授职位授予实验心理学家。虽然他们非常欢迎在这个学科上取得的令人可喜的进展,但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需要学者投入全部精力。对精神生活的实验研究需要有独立的系科和教授,把哲学留给哲学家。”
巴吉尼说:“如果哲学不想成为空洞的推理,那它就需要心理学。如果不了解事物实际上是什么样的,那么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论断就不能当真。”但他更多谈到了心理学为何需要哲学,关于什么可以让我们幸福,心理学肯定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就变成了伦理问题,此时我们便需要转向哲学。他认为,心理学本质上是一门描述性学科,目的在于准确描述思维的实际运作方式。问题在于,一些更为狂热的从业者和布道者以为心理学能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科学处理的是关于标准和平均值的问题,而我们得尽力去过属于个人的、独特的生活。更为根本的是,科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如人们从一些事情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但只有哲学才能确定我们是否从正确的事情中获得了快乐,以及我们究竟该为自己的福祉付出多大努力。
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追求善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那我们所做事情的意义和价值便会发生改变。比如,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例,其中的危险在于,心理学可能会玷污、贬损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心理学会让我们把他人看作通往极乐的手段,而不是看作本身值得我们珍视和爱的人。比如,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的儿媳格雷琴·鲁宾在《幸福计划》中说,有一次她拥抱她丈夫至少6秒,因为她碰巧看到一项研究说,6秒是促进催产素和血清素流动所需的最短时间,这两种都是刺激情绪、促进感情的化学物质。在拥抱的时候想着这些,肯定会让拥抱变味,让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变成一种工具性的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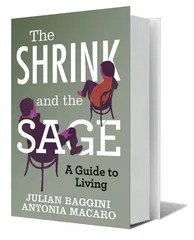 ( 《心理学家和智者:
现代困境指南》 )
( 《心理学家和智者:
现代困境指南》 )
安东尼娅·麦卡洛指出,心理治疗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受到了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爱比克泰德认为“困扰人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这一思想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
心理治疗中还有一派是所谓存在主义治疗,但安东尼娅说:“是维特根斯坦还是海德格尔对生活谈的更多一些?我投票给维特根斯坦,因为他关于理由和原因之分的观点与心理治疗有很大关系。理由是我们用来解释所作所为的一系列信念与欲望的一部分。原因与主体的体验无关,最好被看作需要实证研究来证实的假设。理由和原因很容易被混淆,维特根斯坦虽然觉得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但他认为,由于弗洛伊德混淆了理由与原因,因而让他的精神分析陷入一团混乱。弗洛伊德致力于以无意识的因果机制来解释症状与行为,比如,一位年轻女士的歇斯底里被解释为是性压抑引起的。但这既不是理由(这与她的体验无关),也不是原因(这不是一个实证性假设)。”
 ( 朱利安·巴吉尼 )
( 朱利安·巴吉尼 )
安东尼娅认为,许多治疗师仍在这种混乱中。人们常常误以为所有心理疗法的目标都是揭露隐藏的原因,而其实心理疗法更经常与人们的理由打交道。比如许多酗酒者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喝酒,他们想知道是什么遥远的原因(基因、教养等等)导致他们酗酒,但这通常不是最有用的。相反,一旦我们发现人们喝酒的理由,我们就可以周密部署,明察这些理由的隐藏含义,进而对其提出挑战。
那些死之前该做的事
在回答“怎样在有限的人生里让生活更加丰富?”这一问题时,巴吉尼认为,可以用最新的心理学来完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观点。他写道:“生活如同比赛,在人生抵达最终期限之前,我们要尽可能多做些事。但是,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这么做带来的最终结果通常是空虚的生活,而不是充实的生活。”
生活是一种现在时现象,我们可以回忆过去,期待未来,但是只能存在于当下。这只是部分真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通过回忆、树立目标和做计划,我们其实既存在于某个时间点,也存在于一段时间中。生活的伦理阶段要求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当前是否快乐。克尔凯郭尔意识到,审美和伦理生活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认为,没有什么理性的方法让这两者达成和解。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冲突,只有通过牺牲理性,审美和伦理才能达成和解。
巴吉尼认为:“克尔凯郭尔的诊断是准确的,但他开的处方有点轻率。我们可以用更现代、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克尔凯郭尔的范畴论。”他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成果。卡尼曼在许多实验的基础上,区分了两个自我。每个人内心都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体验自我,只存在于此时,这个自我通常依靠直觉、自发、无意识运作;另一个是记忆自我,这是反思、理性的部分,思考体验自我做了什么,将会做什么,并把片段的体验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自传式叙述。哪个自我对我们更重要?答案肯定是记忆自我,因为记忆自我具备反思能力,能真正判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而体验自我只是一种感觉。记忆自我本身没有内容,靠的是体验自我提供的内容。人生的各个时刻的经历提供原材料,组合形成个人传记,因此我们要让经历发挥作用。但这种组合过程不是简单的加法。因此,当思考死去之前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能只是想着积累积极体验,而是去做能让自己更满意的事情。巴吉尼说:“一味遵从死前要尽可能多做些事情的现代律令,人就将错失一切,只能成就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审美阶段的卓越。”
对于“怎样在有限的人生里让生活更加丰富”,心理治疗师安东尼娅的观点跟巴吉尼的很接近,只是表述得比较诗意。她说:“闲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中有太多好玩的东西,到处都有可看的东西、可读的书籍、可听的音乐,你永远都不会厌烦。有许多网站给你提供帮助,告诉你在死之前要去爬的最雄伟的山,要去欣赏的最壮观的日落景象,要去拍摄的野生动物。体验新的东西无疑是好事,不要日复一日地沿着习惯的轨道前进。”
我们经常被告知,学习新东西有助于我们远离老年痴呆,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多做事是度日的唯一好方式。首先,如果你依赖于通过猎奇来让生活充满乐趣,可能你会终生劳碌,总是在寻找下一个惊喜。若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继续,你便会深受不满足感的折磨。
新体验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东西,还有许多事情同样有价值——简单、知足、品味日常生活中的小乐趣,体会平凡生活。“有些东西年复一年地出现,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有新的收获,四季更替就是很好的例子。临近2月底的时候,黑鹂鸟开始在屋顶、枝头唱歌,夏天迎来罂粟、忍冬花的开放,树上结出的浆果则表示秋天到了。表面上平常的生活,可能因为充满对各种东西的欣赏而富有价值,而冒险的人生则可能缺少这种欣赏。丰富的生活可以是这样的生活:所做的事情不多,却体验得很深入。”(文 / 薛巍) 遇上哲学家心理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