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远在何方?》
作者:孙若茜 (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和她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 )
(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和她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 )
1938年纳粹德国爆发“水晶之夜”后,遭屠杀和迫害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再在欧洲找到容身之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大都采取了限制性移民政策。当时被置于殖民管辖且不需要签证的上海,就成了犹太人逃亡的避难所。1941年的上海,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避难者达到1.8万人左右。他们虽得以幸存,却在极度贫困和文化差异中生活得无所适从。长篇小说《上海,远在何方?》就是这些流亡者的众生相。
小说的作者乌尔苏拉·克莱谢尔(Ursula Krechel),1947年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期间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戏剧学,毕业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克莱谢尔就已凭诗歌步入文坛,先后发表了12部诗集,并获得众多文学奖项,成为德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女诗人。2008年发表的这本小说处女作则为她开启了小说家的身份。
1980年第一次造访上海,使克莱谢尔对犹太人流亡此地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回到德国后便立即开始了有关的资料收集。她寻遍德国的档案馆,又前往英国伦敦的犹太人档案馆,同时找机会和当时在上海流亡过的犹太人后裔交谈,以了解犹太人当时在上海的真实处境。由于此前她的创作一直集中在诗歌和话剧上,因此当时的她并没有打算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想查清历史的痕迹。
1990年第二次到上海,她根据资料找到了很多当时犹太人收容所的原址,并继续和一些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对话,包括中国人。“慢慢地我就想,如此众多的人物、庞杂的线索,必须用长篇小说的篇幅才能概括进去,并且要写全景式的故事,在故事中挑选几个主要人物。”克莱谢尔告诉本刊,“我的文学创作最主要内容就是要把这些共同的故事找到一个连接点编织在一起,能够找到一个合适叙事的结构。”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和情节结构,而是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流亡者形象。”《上海,远在何方?》的中文版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导师韩瑞祥教授在译者序中提道,“小说中,报道、评论、文献引言和叙事交替穿插,互为镜像,相互映衬。”除了将文献性资料和虚构的内容通过巧妙的叙事结构形成有机的整体外,韩瑞祥告诉本刊,这部小说的文学特点还在于:“因为她是诗人,她语言的构想充满想象的意识,而小说的叙事又要求她要非常具体,这种融合使小说的语言形成了很多的层面,极其简单的句子中可以存在象征,给读者一个潜在的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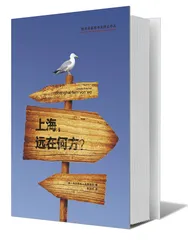 (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和她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 )
( 乌尔苏拉·克莱谢尔和她的作品《上海,远在何方?》 )
前不久,乌尔苏拉·克莱谢尔作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邀请的“中德作家论坛”的德方代表作家之一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同时,《上海,远在何方?》的中文版也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生活周刊:从1980年你第一次到上海,一直到2008年这部小说出版,其间你都在不断搜集各种关于犹太流亡者的资料。为什么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持续关注这个题材?
克莱谢尔:这首先可能是一个道德倾向或者说是道德责任的问题。在我过去读过的文学作品里,50年代那批作家的作品更多涉及回归的文学话题。因为他们经历了战争,被战争偷走了很多东西,爱情、亲人、家乡等等,和平之后他们回到自己家乡,想找回这些东西。而我的关注点,是战争中最普通的受害者、老百姓,他们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声音,但是没有文学作品把这些表现出来。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大家觉得终究还要活下去,往前看。当时很多人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流亡地又回到了德国,他们到底如何融入到新生活中,等等。这些有关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我特别关心的事情,也是我小说中涉及的内容。
虽然官方自有它的历史观,但作家就是要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把一切事情搞得非常清晰,把很多没有被说出来、被发现的东西,说出来发现出来。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它的反思和清算不是一种反复的纠缠,而是要让已经发生的错误决不能再一次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从极具主体意识的诗歌创作,到几近还原历史的小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形式间的转换,对你来说是轻松的吗?
克莱谢尔:在我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诗歌占很重要部分,大约写了50本诗集,其中很多诗作被选在中小学的教材中。直到写《上海,远在何方?》之前,我也是在尝试写篇幅比较短的小说。我认为诗歌和长篇小说虽然形式非常不同,但在创作方法和创作灵感来源上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我在写诗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在报纸上看到某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词,把它放在完全陌生的语境或者词汇的连接中来进行诗歌的创作。这和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巧,找到一些资料,然后加工使它变成长篇小说。并且我的诗歌创作并不是那种漫无边际的想象,而是强调结构,要用语言形成节奏,里面也会有关于主题的命运发展,这和小说的创作也有相同之处。
对于我来说,不同的创作形式是由不同的题材决定的,比如《上海,远在何方?》这种全景图,1.8万人在上海,不可能每个都去描述,所以就提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来展现时代图像。
三联生活周刊:写进这本书里的内容,几乎都是史实,甚至连一些主人公的名字都是真实的。你怎么把握和运用搜集来的史料,使这本书可以成为成功的小说而不会变成一本历史书?
克莱谢尔:把历史这么写作出来,对我而言相当于一种挑战。做准备工作的时候,除了看大量文字材料,我也看了很多那个时期的照片,和很多历史见证人有过谈话。当时这1.8万名犹太人在上海创造出了自己生活的圈子,演话剧、出版一些杂志等等。但是在处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我又不得不把它们抛开,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成了报道,或者成了反映当时史实的书,而不是一本长篇小说,因为小说里面必须要有虚构的内容,需要一个结构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小说的创作时间,差不多跨越了20年,从开始处理史料到最后从史料中达到一个高度才能进行虚构性的创作。
对于我的小说来说,虚构和史实之间的比例比较难把握,有那么多的这段历史见证者现在还活着,德国通过“二战”给这么多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不幸,所以不能有太多虚构,只是对一些具体细节点进行作为文学的发明创作,并特别注意小说语言的美感、语言的游戏、一些影射。因为我原来是诗人,诗一样的语言怎么样跟处理史实的风格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是在写故事的时候,如果用今天的视角,很容易带着自我视角的限制。对于我来说,我喜欢写他者的题材,比如我作为德国人写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作为一个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来写这样的故事,也就意味着要做双重决定,所有的一切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陌生的,都是他者,对于每个读者来说,在读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是他者的视角。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偏爱用他者的视角写作?你的另一本小说《地方法院》在这一点上也有相似之处。
克莱谢尔:从我个人的经历说,因为出生在与卢森堡、法国交界的地方,从小就接触了很多异语言、异文化。当时我就想,在这些作为占领军驻扎的法国人、美国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就是通过另外一种眼光、通过一种异文化的眼光去观察另外生活、另外这些人所受的苦难,我认为这是很值得一写的。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才能保证这种视角给读者带来的距离感是恰到好处的,既能保持一定距离,又和读者有所贴近?这是不是你在小说中选用一个书商的角色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原因所在?
克莱谢尔:我之所以塑造和选择这么一个人来承担整个故事的结构,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在小说中本身就是一个书商,书商讲书的故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另外,他是一个柏林人,讲话相对轻松又略带一点讽刺的意味,所以由他来讲述历史,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视角。他是亲历者,在书中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些经历输出给读者,读者也会产生亲历感,而作为书中的人物,通过作者身份在一个历史界限中的叙事,又产生了距离感。
另外,我在收集资料时,的确在德国图书馆的档案馆里找到过这么一卷当时的录音,录音从未被公开发布过,讲述的就是他当时在上海整个的经历。我觉得一个人给你讲自己所经历一生的苦难,而讲完以后就被忘却、被丢掉,这太残忍、太可怕了。因此我就把它整理出来了,作为小说中的一个素材。(文 / 孙若茜) 读书文学小说谢尔上海何方犹太民族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