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绘画的旅游地理
作者:李菁( 夏鲁寺北外配殿南壁壁画《四臂观音》,公元14世纪上半叶 )
“从最开始被西藏的自然风光吸引,再到被它文化、宗教上的东西所吸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5年22岁的于小冬参与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壁画临摹工作,第一次见到1300年前大昭寺吐蕃时代的壁画原作,“如被魔力抓住”,自此开始了与藏传佛教绘画的不解之缘。除了画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名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研究者,2006年,他将多年研究心血著成《藏传佛教绘画史》一书。
“西藏的佛教绘画绝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民间绘画,这些绘画无须解释,靠着自身的完美便足以证实它应有的地位。它是衰落的印度佛教的中心向北方迁徙,是喜马拉雅以北的高原之上佛教正统传承中心地带的艺术;它曾是政教合一的古格王朝、萨迦王朝、格鲁派喇嘛王国具宫廷气派的艺术;它是融会了西域、南亚和中原艺术的因子,消化综合后产生的具独特绘画面貌的自成体系的艺术。在佛教艺术领域,西藏的绘画在它的鼎盛时期是可以称冠整个亚洲的。从12世纪到16世纪,西藏绘画的贡献让所有亚洲的宗教艺术黯然失色。”在《藏传佛教绘画史》这本书的后记中,于小冬这样认为,“可惜的是在美术界的视野中,西藏总是不被看到,从没有给予西藏艺术应有的地位与评价。”
“壁画的年代是可以判断的,至少我不会被蒙蔽。”于小冬很自信地说,“我是以风格史的方式来写这本绘画史,从图像到图像、从图像的风格辨识,什么样的造型、构图、用色,每个造型单元有什么区别等等。我的劣势是不懂藏文,不能从文献中去研究。但我的优势是画画的,对形式很敏感,所以我就可以写看得见的美术史。”
于小冬说,从藏传佛教绘画史发展历程看,外来多种文化和教派势力两方面影响最大。“早期是受印度、尼泊尔影响多,到了后来,中原的民间绘画、寺院壁画对它都有影响。比如勉唐风格已经吸收了好多中原因素,有明代的寺观壁画、民间绘画的影响很明显。”于小冬举例说,壁画里最早出现的形象肯定是莲花,“如果一幅壁画里出现了牡丹花,这肯定是受中原影响的”。包括五官也不一样,“比如早期12世纪前后可能是椭圆的脸,逐渐发展成波罗风格,就有点像现在最流行的脸形,下面小,上面大,五官比较集中,夏鲁寺就主要是这个风格。像半裸的、着衣比较少的,显然是南亚的传统,菩萨身上的璎珞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后来就逐渐变成了中原这样宽袍大袖的风格。早期是红蓝对比比较多,后来就逐渐发展成红绿对比较多,再后来绿色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看到寺院壁画好多整个都是绿色的,如果宣称它是吐蕃时期的,那肯定是乱讲。吐蕃时代的底色都是深蓝色的,而且是棋格的,没有山水,都是装饰性的,不是任意排列、故事穿插在其中,而是一排一排的,很严整,每个人在每个人的位置。”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地考察,我脑子里像有一个地图和图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这些绘画艺术是怎么发展的。”于是,按照时间脉络,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
 ( 托林寺红殿后殿西壁壁画《释迦牟尼诞生图》,公元15世纪 )
( 托林寺红殿后殿西壁壁画《释迦牟尼诞生图》,公元15世纪 )
7~9世纪:吐蕃王朝时代(西藏佛教前弘期)
佛教文化从印度波罗王朝和中国大唐王朝传入吐蕃王朝。拉萨留到今天的吐蕃绘画遗址只有三处,一般认为有大昭寺二楼东北角的壁画,二楼护法神殿的壁画及布达拉宫法王洞壁画。于小冬认为,后两处壁画中虽人物着吐蕃装,但绘画并非吐蕃作品,故实际只有大昭寺一处。
 ( 托林寺红殿后殿西壁壁画《供养天女》之二,公元15世纪 )
( 托林寺红殿后殿西壁壁画《供养天女》之二,公元15世纪 )
“大昭寺是吐蕃时期的,里面的大格局是非常早的。原来的老壁画都被搬走了,现在看到的都是晚期的。但是里面的门楣、木雕、建筑构件、构件上的彩绘都是老的——彩绘可能是新的,但是样式是早期的。它学习的是印度的那烂陀寺,就是唐僧取经的地方。它里面的柱子,现在被很多朝圣的人摸得都圆了,但是柱子的造型就是从印度来的。里面的部分壁画和敦煌有联系,也和中原有关系。”
10~13世纪:西藏佛教后弘期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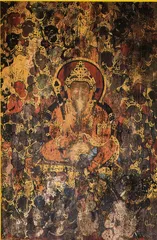 ( 大昭寺二楼东北角法王自修室内壁画《佛与众菩萨》,绘于吐蕃王朝时代 )
( 大昭寺二楼东北角法王自修室内壁画《佛与众菩萨》,绘于吐蕃王朝时代 )
10世纪,吐蕃王室后代一支在西部阿里地区建立古格、普兰、拉达克三个小王国。阿基寺(境外的拉达克地区)和部分托林寺壁画,具有这一时期边缘文化的地域性特征。12~13世纪,阿里和卫藏几乎同时间接受了波罗风格的影响。西部是粗放、简洁的波罗中亚画风,时间短到对后世几无影响。相反卫藏的波罗风格持续时间较长。卫藏地区没有受克什米尔风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波罗的艺术营养和汉地绘画(汉地风格主要是指唐五代时期的敦煌遗风)的某些因素。在10~13世纪,以波罗风格为主,并可见诸多敦煌因素和吐蕃因素的时代特征。卫藏的波罗风格正统而严格,绝不粗放、简陋。扎塘寺和部分夏鲁寺壁画是其代表。
扎塘寺(山南扎囊县)建于1081年,是后弘期最早的一批寺院之一。其壁画遗存在西藏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是后弘期卫藏最早的寺院绘画遗存,是“下路弘法”表现在美术中的实物见证,同时也反映出融合汉地敦煌和印度波罗艺术因素。现存早期壁画有大殿里西北两壁,保存完好如新。
 ( 大昭寺二楼东北角法王自修室外右侧壁画《六臂观音》,绘于吐蕃王朝时代 )
( 大昭寺二楼东北角法王自修室外右侧壁画《六臂观音》,绘于吐蕃王朝时代 )
夏鲁寺(日喀则)这一时期的波罗样式绘画仅存于主殿门廊内的一小部分,已陈旧残破,从中可看到波罗风格的纯正和画技的丰富变化,预示了夏鲁绘画将要出现的辉煌。
13~15世纪末:藏传佛教绘画鼎盛时代
 ( 扎塘寺壁画《供塔菩萨》之一,公元11世纪 )
( 扎塘寺壁画《供塔菩萨》之一,公元11世纪 )
14世纪,由于萨迦教派推崇和赞助尼泊尔风格的宗教艺术,邀请尼泊尔艺术大师阿尼哥到萨迦寺建造金塔,卫藏地区的佛教绘画逐步形成了尼泊尔样式的夏鲁风格。尼泊尔风格造型妖媚和色彩纯艳的不足,经朴实真诚的藏民族性格的过滤,使静穆典雅的气质融入了华丽的视觉效果中。夏鲁寺壁画是这一样式的典型代表。“它受尼泊尔波罗文化影响。尼泊尔的工匠也参与过创作,那时候尼泊尔的大艺术家阿尼哥来过中国,说不定有他的影响。”
15世纪,受夏鲁风格和中原汉地文化影响,江孜样式也逐渐形成完善。江孜风格指15世纪在后藏江孜地区形成的绘画样式,属于藏族艺术家自己创立的绘画体系,它和夏鲁风格一起标志着藏族佛教绘画史走入了鼎盛时代。位于日喀则江孜宗山脚下的白居寺,其壁画是这一样式的典型代表。“它的吉祥多门塔是这一风格的最高成就;包括好几个大殿里的泥塑,非常精彩。环绕四层佛塔共有大大小小76间佛堂,俱绘满壁画。”
( 夏鲁寺壁画《龙尊王说法图》,公元14世纪 )
14~17世纪:西部的阿里和拉达克的古格样式
这一时期,格鲁教派日渐强大,势力范围扩展到古格地区,一度消沉的西部佛教艺术因此再度兴旺,古格样式得以形成。古格样式指克什米尔风格和江孜样式融合的绘画风格,它标志着以古格为代表的西部绘画艺术的成熟,以优美、富丽、高贵、细密为特色,完全放弃了粗放的西部波罗风格。古格王宫和托林寺壁画是这一样式的典型代表。
 ( 夏鲁寺壁画《说法图》菩萨局部,公元14世纪
)
( 夏鲁寺壁画《说法图》菩萨局部,公元14世纪
)
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卫藏地区的不同流派形成
“这一时期,勉唐、青孜、嘎玛嘎赤三个早期绘画派系分别形成。教派势力左右画风,流派之争也体现不同教派势力的斗争。萨迦派支持青孜派,嘎举派扶持嘎赤派,格鲁派推助勉唐派。”
 ( 扎塘寺壁画《说法图》罗汉局部,公元11世纪
)
( 扎塘寺壁画《说法图》罗汉局部,公元11世纪
)
勉唐派加强了主尊着装的汉族化表现,人物造型厚重圆浑,有唐代遗风。勉唐画派是西藏画史中最重要、规模最大、追随画家最多的艺术流派。它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艺术在15~17世纪印度、尼泊尔画风的彻底结束和具有本土特色的藏族绘画样式的形成。以扎什伦布寺为代表的格鲁教派大寺院留下了最早的作品。
青孜派影响范围主要是山南和后藏。他们和勉唐派一样,都从明代汉族艺术中吸取营养,同时,青孜派又保持了尼泊尔风格艺术传统的诸多美质,是最典型的过度风格。青孜派画家大多被萨迦派高僧赏识和支持,因此该派的影响力与萨迦教派的兴衰密切相关。
( 扎塘寺壁画《说法图》菩萨局部,公元11世纪 )
嘎玛嘎赤派画风受中原汉地风格影响最深,是在勉唐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王者气象是嘎赤派最突出的特色。“嘎玛嘎赤派主要影响区域在藏东,现在还有传人,有时也把嘎赤画风说成是藏东风格、康区风格。17世纪,嘎玛噶举教派在和格鲁派的斗争中失败,噶举教派余部退居康区,因此康区一直是嘎赤派最发达、延续时间最长、风格传承最纯正的地区。”
17世纪中叶至现代:新勉唐派树立典范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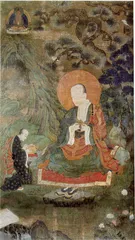 ( 嘎玛嘎赤派唐卡《罗汉卡利卡》,公元15 世纪后 )
( 嘎玛嘎赤派唐卡《罗汉卡利卡》,公元15 世纪后 )
17世纪,天主教传入西藏西部,导致古格与拉达克两国发生战争,古格王国灭亡,古格样式优秀的绘画传统也因此中断。同时,格鲁教派在蒙古军事实力的扶持下取得最终胜利,五世达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新勉唐画派因此受到格鲁教派的推崇。
新勉唐派在吸收明、清两代汉地绘画影响,又融合嘎赤画派风格的基础上,把《度量经》作为制作壁画、唐卡的严格标准,逐步形成了佛教绘画的标准样式,西藏绘画史风格样式的发展自此停顿。标准样式随格鲁派的影响覆盖整个藏区,远播到内外蒙古、满族地区和尼泊尔等邻国,出色地完成了服务宗教的智能,成为藏传佛教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典型绘画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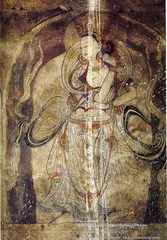
“新勉派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藏巴·曲英嘉措。他的画拿到西方大师的队列中都是一流的。”藏巴·曲英嘉措是最受五世达赖喇嘛重用的一位绘画大师。在扎寺的扩建工程中,由他负责指挥工匠们设计和制作壁画与塑像。
“今天所称的新勉更多是指代一种通行所有藏传佛教区域的‘标准样式’的绘画风格。这种流行风格和曲英嘉措个人的作品有天壤之别。‘标准样式’附生于新勉,是在平庸的后继者手中逐步形成的。曲英嘉措是一位造型能力极强、写实技艺很高的大师。而新勉画派的追随者大多数是机械而刻板地学习‘标准样式’,忽略了该派祖师最精彩的传神之处。”

于小冬也推荐了藏区其他一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在云南离丽江很近,有一处白沙壁画;比如昌都地区的类乌齐县,有一个很大的寺院,壁画也比较有名;拉萨东边墨竹工卡县,有一个尼玛拉康寺院,目前我看到拉萨附近留下来的吐蕃壁画最好的应该是那儿,至少是9世纪以前的,非常好。有点残破,但是非常大气饱满。在拉萨周边,桑耶寺也有很好的壁画,虽然很近代,但是非常好。”
“西藏的文化有一个特点:是在河谷发展起来的,林芝那时候主要是一些部落文化。林芝有一些石刻不错,8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就在林芝农牧学院后山上,有很好的摩崖石刻。应该是比较早的,看样式是14世纪以前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 托林寺红殿门廊壁画《十六金刚舞女》,公元15世纪前 )
( 托林寺红殿门廊壁画《十六金刚舞女》,公元15世纪前 )
藏传佛教绘画风格的五种主要类型
新勉唐画派派生的“标准样式”。
 ( 青孜派唐卡《莲花网目金刚》,公元15 世纪后 )
( 青孜派唐卡《莲花网目金刚》,公元15 世纪后 )
这五大类型宏观上串起了藏传佛教绘画风格史的整体脉络。藏传佛教绘画风格样式从吐蕃时代起,历经西部克什米尔风格、卫藏波罗风格、尼泊尔样式、江孜样式、古格样式、勉唐派艺术、青孜派艺术、东部绘画艺术和新勉唐派艺术九种演化,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移,即: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风格向汉地绘画风格的转移;从外域风格向本土样式转移。审美取向也随之从静穆空灵向华丽世俗转变,从凝重庄严向真实亲切转变,绘画的内在精神追求也从表达宗教精神的殊胜境界向崇尚世俗社会物质感观刺激转变。
印度的波罗类型(包括吐蕃时代的大昭寺、11世纪的扎塘寺、12世纪的阿基寺和黑水城(境外))。是指印度波罗王朝(8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期)艺术的风格样式。人物面部造型的主要特征是:正侧面多呈斜方形,下巴凸出宽大,下唇厚凸,眼睛呈弓形;正面的脸形上宽下窄,呈方形特征。
( 扎什伦布寺通瓦敦丹殿壁画《释迦牟尼说法》局部,佛陀示现神通变化,公元17 世纪中叶 )
克什米尔类型(包括11世纪阿基寺、15世纪以前的古格艺术、16世纪古格样式)。是指犍陀罗风格与波斯艺术传统相结合,最终在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形成的佛教艺术样式。人物造型的主要特征是:圆脸、丰乳、细腰、宽臀和小巧的手足。
中原汉地类型(包括吐蕃统治敦煌时代、11世纪的扎塘寺、15世纪江孜样式的一部分、15世纪勉唐派艺术、15世纪以后的嘎赤派、17世纪以后的新勉唐派、18世纪以后的司徒班钦风格)。不是指受文人画影响,而是受汉地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影响。
 ( 扎什伦布寺通瓦顿丹殿壁画《佛祖示现神通变化》局部,公元17 世纪 )
( 扎什伦布寺通瓦顿丹殿壁画《佛祖示现神通变化》局部,公元17 世纪 )
尼泊尔类型(包括14世纪的夏鲁寺、15世纪江孜样式的一部分、15世纪的青孜派艺术、16世纪古格样式的一部分)。是印度笈多王朝艺术风格的发展,人物造型的主要特征是:头部上宽下窄,眼睛位置偏下,四肢修长。 (本文部分图片选自《藏传佛教绘画史》)
于小冬的《藏传佛教绘画史》
 ( 扎塘寺壁画《供塔菩萨》之一,公元11 世纪 )
( 扎塘寺壁画《供塔菩萨》之一,公元11 世纪 )
1984年,20岁的于小冬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后,选择去西藏大学当老师。上世纪80年代的拉萨,聚集了一大批像他这样从内地入藏的理想主义者,比如马原、牟森、皮皮、田文、贺中、李津、罗浩等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文学、诗歌、绘画、哲学,在拉萨形成了一个别有氛围的小圈子。
1987年,陕西考古队帮助西藏做文物普查,他们去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拍了很多壁画,这些壁画呈现出的艺术水准大大超出于小冬的想象,“我觉得它们的艺术价值应该在敦煌之上。因为敦煌壁画更多是民间的工匠、艺人创造的,而西藏这些大部分都是王朝的画师创作的,尤其是古格的部分”。
 ( 唐卡《萨迦班智达》,公元18 世纪中叶 )
( 唐卡《萨迦班智达》,公元18 世纪中叶 )
“陕西考古队拿出那个东西把我镇住了,我就特想知道它们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这个风格是怎么产生、形成的。”这样一个机缘引导于小冬开始逐渐研究起壁画。这一年,于小冬和藏大美术专业的师生们,带着一腔热情去阿里临壁画。他们坐在卡车的货斗上风吹日晒雨雪尘沙颠簸一路,虽然终于亲眼看到了那些令他激动不已的壁画,可是临摹壁画的行动却四处碰壁,只能遗憾而归。
第二年,文管会友组织十几位画家赴古格临壁画,上次临画被拒的经历让于小冬视这次机会为千载难逢。他向学校请假,学校不批,他一怒之下写了辞职报告,随拉萨画界那些年轻的同行们爬上东风牌货车,第二次西去阿里。“为这事我觉得怎么做都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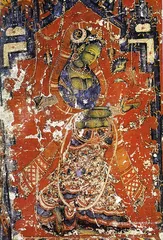 ( 阿基寺壁画《绿度母》,公元11 世纪 )
( 阿基寺壁画《绿度母》,公元11 世纪 )
那段时间,他们住古格王宫的破山洞里,白天临摹壁画,傍晚坐观日落,他说,陶醉于古格壁画的日子,这几乎成了他半生里最幸福的时光。两个月后回拉萨,他面对的是学校严厉的处分,加之失恋和拉萨骚乱的影响,他体验了人生中最苦闷的阶段,甚至心生弃职离藏之意。后来在好友的规劝和陪伴下,他又重返西藏大学任教。
虽然遭遇小波折,但他对充满异域风格的藏族绘画艺术的热爱却更加明确。他用现在看来相当简陋的破相机开始了对壁画和唐卡的翻拍搜集。“十几年里相机换了两部,图像像质越来越好,可翻拍壁画和唐卡的机会却越来越少。”1990年勉唐画派的正宗传人、宫廷画师的后代丹巴在西藏大学首开唐卡课,于小冬重当学生完整学习勉唐画派唐卡的制作技艺。受这些艺术影响,他从国画改成油画。
 ( 唐卡《弥勒菩萨》,公元16 世纪 )
( 唐卡《弥勒菩萨》,公元16 世纪 )
1992年,于小冬的8年援藏期满,可是他却不想走,于是又待了5年,直到1997年调回天津,任教于天津师范大学。从20岁到34岁,他在西藏生活了13年零5个月。为此,他创作了《干杯西藏》,以示对那时候一批理想主义者的告别。但是即便回到内地,他每年还是会被“召唤”到西藏生活一段时间。
1995年,于小冬考察了白居寺和夏鲁寺,领略了藏传佛教绘画鼎盛时代的最高水准,渐渐萌生了写一本藏传佛教绘画史的念头。为此,1997和1998年他两度自驾破北京吉普,单车闯阿里,历尽九死一生的危险和艰辛,考察古格王国的周边文化,得见11世纪的洞窟壁画。20年里,他临摹几十米壁画、寻访百余座寺院、翻拍千余铺古墙,对西藏历史、藏传佛教、中外美术史的学习从未中断。至此,他对西藏的佛教绘画有了完整的概念,也更坚定了写史的勇气和信心。2000年,他开始动手写作,6年后,完成了《藏传佛教绘画史》,他也成为研究藏传佛教壁画的专家。
 ( 夏鲁寺南配殿南壁中央比卢遮那佛下主壁画局部,公元14 世纪中叶 )(文 / 李菁 周翔(实习记者)) 地理藏传佛教绘画史藏传佛教佛教绘画壁画旅游地理艺术美术大昭寺
( 夏鲁寺南配殿南壁中央比卢遮那佛下主壁画局部,公元14 世纪中叶 )(文 / 李菁 周翔(实习记者)) 地理藏传佛教绘画史藏传佛教佛教绘画壁画旅游地理艺术美术大昭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