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工程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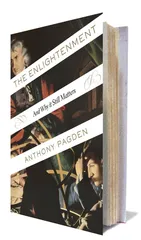 ( 《启蒙运动:为何它仍然重要》 )
( 《启蒙运动:为何它仍然重要》 )
颠覆中世纪的自然法
麦金泰尔在《德性之后》中对启蒙运动的描述很怪异,他认为启蒙运动基本上发生于北欧,法国是启蒙国家中最落后的,因此基本被他排除在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安东尼·帕戈登所著《启蒙运动:为何它仍然重要》则从法国写起:“1794年,孔多塞坐在巴黎塞万多尼街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在烛光下写《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素描》……1794年3月25日,孔多塞逃离巴黎,随身只带了一本贺拉斯诗集。第二天,在距巴黎9公里处,又累又饿的他在一家餐馆点了一份煎蛋,侍者问他要几只鸡蛋,他说要12只。他立刻遭到了逮捕(只有贵族一轮才吃那么多只鸡蛋)。两天后孔多塞死于狱中。”
帕戈登搜罗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但他的整体观点也很清楚。他说:关于什么是启蒙、它是何时在哪里发生的、是一场还是多场,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试图把它分成激进的和保守的,或区分不同国家的启蒙——冷静、通达的英国启蒙,严肃认真的德国启蒙,极端、仓促的法国启蒙。虽然启蒙内部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启蒙运动都认为人是理性、仁慈的,并相信进步和人类的自我提高能力。它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宽容、世俗政治、普遍主义的来源。
但帕戈登认为启蒙最大的成就是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最突出的特征不是用理性来审查历史、自然、神学和政治权威,而是认识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从而同情他们。帕戈登认为,这是世界主义的根源:启蒙运动的核心信念是共同的人性,以及意识到我们属于更广大的世界而不只是自己的团体。
少数欧洲知识分子何以能够不说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而是说自己是“世界公民”?世界主义是一个古老的信条,在启蒙运动期间,它得了非常不同的含义。它反对狭隘的宗族主义,能带来永久的和平。
 ( 帕戈登 )
( 帕戈登 )
帕戈登说:“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是对霍布斯人性观的扩大化和人性化。”霍布斯认为,从本性上说,我们寻找的不是朋友而是荣誉和好处,使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不是为了相互帮助,而是因为恐惧,“上床睡觉时人们会锁上门;外出旅行时会带上武器,害怕遇到劫匪。国家用堡垒守卫边界,城市有城墙,因为害怕邻近国家”。相互恐惧不仅使人们群居,而且使人们愿意受到市民社会的束缚。人类有伤害同类的天性,但又都渴望活下去,每个人都会竭尽全力保全自己。人不仅好斗、邪恶,还有理性。他们明白,如果让每个人为所欲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为了结束这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原始人得出结论:有必要放下为所欲为的权利,满足于有限度的自由,为此他们定下了契约。并不是所有人都迈出了这一步。有许多人仍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如美洲印第安人。对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来说,城邦的建立是为了实现先验的计划,对霍布斯来说那只是出于为了自保的理性计算。在霍布斯看来,市民社会的创建令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但是这不是如亚里士多德和神学家们想象的,通过改造人性实现的。这是通过限制人类的破坏天性而实现的。社会没有改变我们。我们本质上仍像在自然状态中那样邪恶。
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论
 ( 普芬道夫 )
( 普芬道夫 )
帕戈登说,霍布斯的人性观是有缺陷的:它是一种高度还原论的观点,认为人的全部动机就是自私。他剥除了人性中爱、亲切、感觉到同类的能力,只剩下了恐惧。“澡盆干了,孩子也被泼出去了。”霍布斯不仅消灭了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神学秩序,还消除了不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人类交往。但经院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像霍布斯说的那样贫瘠。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法为霍布斯排除的许多东西留下了空间。经院哲学的自然法观念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和政治规范提供了基础,它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人,不管他们的文化和信仰是什么。它还要求人类相互尊敬,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一起生活的冲动。它要求人们相互帮助,甚至帮助陌生人,和睦是自然法的一部分。
因此,在霍布斯之后,人们需要对人性更深入、更有同情心的记述,第一个做这种尝试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萨缪尔·普芬道夫。普芬道夫说,他的立场接近于斯多葛的理论,霍布斯则是过火的伊壁鸠鲁学派的理论。帕戈登写道:“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之间的对立,以及它们跟怀疑论之间的关系,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在亚当·斯密与弗兰西斯·哈奇森、狄德罗与卢梭、孔多塞与休谟、维柯与康德那里看到它们。”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快感。伊壁鸠鲁学派把道德原则还原为生理感觉,他们的原则是自爱,追求安全和舒适。霍布斯认为,人类的唯一共同点是对快感和痛苦的计算。休谟说:“伊壁鸠鲁和霍布斯主义者欣然允许世界上存在不矫饰、不伪善的友谊;虽然他会努力把友谊的成分分解成其他成分,用自爱解释一切感情,用想象力把感情扭曲、改变成各种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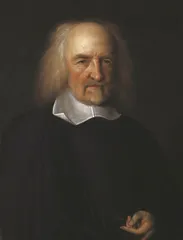 ( 霍布斯 )
( 霍布斯 )
斯多葛派认为美德只会带来幸福,把一切落在他头上的坏事看作外在的。即使在面对最糟糕的麻烦时,他们也会保持不为所动。斯多葛派还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认为所有的人,不管其文化和信仰,都有共同的人的身份。存在一套超越信仰和文化、所有人都接受的概念或思想。人类相互之间有感情关联,西塞罗说:“从父母对孩子的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切,这是人所以为人,人不把其他人当作异己。”这就是后来的世界主义的基础。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斯多葛派。他们都是兼容并蓄的折中派,大部分时间是斯多葛派,偶尔是伊壁鸠鲁派,几乎总是怀疑论者。狄德罗说,折中派“把偏见、传统、古代、普遍同意、权威踩在脚下,他们勇于为自己思考,回到最清晰的普遍原理,考察它们,讨论它们,只接受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而且这种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做人类的学生而非导师,更感兴趣的是改造自己而非他人,更感兴趣的是学习真理而不是传授真理。但在这种令人陶醉的混合中,为理解人类社会提供基础的是斯多葛派因素。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反映了斯多葛派和谐自然的思想。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要把别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跟斯多葛派的道德观很类似。
帕戈登努力为启蒙运动辩护,把它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今天,许多人怀疑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欧美历史就是压迫、殖民和剥削的历史。启蒙运动轻率、乐观的主张是虚伪、傲慢的。启蒙运动不容忍任何挑战其理性主义、还原论目标的人,因此造成了帝国主义和现代种族主义。这些指责并非毫无根据。启蒙运动让西方人感到人类独立取得了智力成就,他们由此获得了自信,感到自己负有文明使命。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人从暴君和征服者手中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就有义务帮助世界各地受苦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被解放的意愿,那只能是因为他们的教士和国王蒙蔽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有理由强迫他们解放出来。但西方人伤害其他地区的人的真正原因是:扭曲的民族主义和打着科学旗号的种族主义、让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工业革命、基督教的虔诚和传播福音的狂热,而这些都是启蒙思想家们深恶痛绝的。”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奥利·库森认为帕戈登最后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帕戈登认为,启蒙之所以仍然很重要,是因为世界主义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但他的启蒙观比传统的启蒙观更成问题。他认为,启蒙发现了之前被宗教蒙蔽的永恒的真理。他毫无异议地认可启蒙的这一信念:文明是全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得出了这一结论,西方人仍在等待世界其他地方赶上来。
“几百年前在欧洲的几个角落发展出来的世界主义是最受限制、最褊狭的世界主义。在支持全球教化过程时,它是帝国主义的。帕戈登热切地支持超国家机构如联合国,他对这些机构的信念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切实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在探讨联合国的意识形态起源时说,20世纪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超越主权的世界主义的理想和机构会带来更多战争、更多屠杀、更多不稳定。即使解决21世纪的一些问题需要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为什么一定是18世纪欧洲的世界主义?那些非欧洲文化有它们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遗产。”(文 / 薛巍) 启蒙工程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斯多葛主义法国启蒙运动启蒙思想世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