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割裂的过去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大卫·坎纳迪内 )
( 大卫·坎纳迪内 )
从宗教到文明的六种集体认同
坎纳迪内在《未曾割裂的过去》一书中,挑战了所有历史就是冲突的历史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冲突是忽视我们共同的人性,虚幻出宗教、民族、阶级、性别、种族、文明上的差异导致的。
他写道:“我们和他者之间的对立,体现在一系列几乎毫无共同点的范畴、集体和认同上。在有记录以来的大部分历史中,两种最主要的认同是宗教联系和民族忠诚。只是到了比较晚近的时期,它们才被世俗、国际化的阶级意识、性别觉醒和种族团结超越。自‘9·11’事件之后,以前被爱德华·吉本和汤因比援引的文明这一更大的认同、更宽广的范畴又回归了。”
这六种认同虽然有质的差别,但都围绕着一种独特的兴趣和觉醒而构建:宗教凝聚力是信仰的表达,关心来世;民族认同依赖的是共同的记忆和地理归属感,并受到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强化;阶级意识是人们跟生产方式不同的关系造成的,导致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敌对;性别和种族部分是生物学特征的结果,也是源于建构和投射到某一群体特有的解剖特征之上的意义和对立。文明也许是最灵活的集体形式了。虽然这些集体认同完全不同、不可通约,但它们都是通过对立、斗争和冲突来定义、强化的:跟其他宗教、敌对民族、敌对阶级、其他性别和种族、异己文明的对立。结果世界被分成相互冲突的群体,一方是善的,另一方是恶的。
坎纳迪内说,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坚持认为,认识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很重要。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使世界转动的是差异,尤其是政治世界的差异。”许多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差异、他者的产生、运作和意义,结果过去被简化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角逐。法国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对野蛮人的恐惧》中说:“光明与黑暗、自由世界与蒙昧主义、甜蜜的宽容与盲目的暴力这些肤浅的二分法,透露的是作者的傲慢而非当代世界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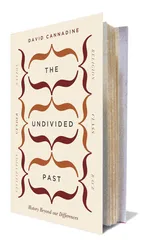 ( 他的著作 《未曾割裂的过去》 )
( 他的著作 《未曾割裂的过去》 )
坎纳迪内认为,民族之间的对抗不是西方历史的主要特征,因为民族的产生是比较晚的事情。直到18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还都是君主之间的战争。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属于同一个民族者的号召力超越了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号召力,但当时德国和奥匈帝国也都是多民族帝国,而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国家之间的分隔,许多都是在帝国的碎片上建立起来的,人群被随机划在一起。意大利政治家马西莫·达泽里奥说:“我们已经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该制造意大利人了。”19世纪和20世纪确实出现了作为集体认同的民族,但几乎民族刚一出现,全球化就开始再次瓦解这种认同。
至于宗教,在历史上,宗教总是广泛地相互借鉴。贸易把不同信仰的人带到了一起。犹太人和基督教在巴格达都有立足之地。十字军东征人尽皆知,但我们往往忘记了有一些人,如16世纪的旅行者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轻松、频繁地穿越不同宗教的地盘。宗教认同跟阶级和民族认同一样,也不是固定的、不可化解的。共同的宗教认同只是一个借口,代表的是其他更强烈的因素,如王朝的野心、民族对抗、经济竞争、领土争端。吉本写道:“早期的基督徒内部分歧很严重,以致他们相互之间造成的伤害比异教徒对他们的伤害还要大。”
文明冲突论由来已久。弗雷德里克·梯加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说,文明是一个组织跟另一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引发的刺激造就的。同一年,衰落论者斯宾格勒反对一个组织刺激另一个组织的说法,但他并不反对文明冲突的事实。他在《西方的衰落》中写道:“两种文化的灵魂之间的屏障是穿不透的。”爱德华·吉本说,是野蛮人和基督徒推翻了柔弱的罗马帝国。霍布斯鲍姆的20世纪史题为《极端的年代》。
1772年,约翰逊博士决定不把“文明”一词收入他编的词典。从一开始,“文明”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认同,其背后是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所说的启蒙的精神。它很早以前就在法国通行,后来被英语吸收,所以爱国、保守的约翰逊博士对它没有动情。但它很快就成了英语中的日常语汇,用于表示人类集体认同的最高阶段,把他们的文明成就和认同区别于野蛮。西方基督徒说他们自己很文明,有教养、高级,外族则粗鲁、暴力、低等、缺乏教育。
20世纪初,出现了另一种看待人类集体认同的观点:不再围绕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是围绕文明的多元化这一概念:除了西方或欧洲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文明,西方或欧洲文明也不再是其他社会朝它迈进的顶点或终点。霍布斯鲍姆在《野蛮:使用者指南》一文中说:“在凡尔赛合约与原子弹被扔到广岛之间,文明远离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野蛮在兴起。”伯纳德·瓦萨斯坦在当代欧洲史《野蛮与文明》中引用本雅明的话说,文明的记录无一不同时是野蛮的记录。因此,文明和野蛮不是处于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方,而是在同一个人和社会中。
阿玛蒂亚·森说:“当我们审视世界历史,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审视的不是不同的文明相互泾渭分明、相互隔绝的历史。文明之间有大量接触、相互联系。我一直认为世界历史,不是各个文明的历史,而是世界文明以类似方式演进的历史,总是相互作用。”
人性,太人性的
在反对把历史简化为冲突的历史方面,坎纳迪内有两位盟友,他们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一位是捍卫世界主义的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一位是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罗杰斯在2011年出版的《分裂年代》中考察了许多认同的瓦解。
但《未曾割裂的过去》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指责和嘲弄。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艾伦·沃尔夫说:“坎纳迪内认为,团结形成了他者,从而为暴力手段辩护。但这六种认同并不统一。性别是一种真实的生理属性,种族是人为的区分。宗教包含普遍的神学和哲学主张,文明与野蛮只是评价性判断,阶级则是源于经济结构。‘认同’一词不能统摄这些不同的现象。”
阶级、民族、宗教和性别认同也不是知识分子的虚构,而是源于真实的权力和地位差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里希特说:“综观全书,占据舞台中央的是词语而非事件、是文绉绉的观念而非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各章很少提及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书籍好像比炸弹更重要。对于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教派,爱德华·吉本真的比教皇负有更大的责任吗?对于种族主义,写书为奴隶主压迫奴隶辩护的罗伯特·诺克斯真的要比奴隶主负有更大的责任吗?对于伊拉克战争,亨廷顿的责任比布什的更大吗?坎纳迪内指出他写到的作者关于对立的观点过于简单化,这确实是对的,但是那些作者描述的对立无疑也是真实的。对立之所以成真,不是因为描述它们的人,而是行使权力使它们成真的人。”
“就像诗人需要春天一样,历史学家需要冲突。”“只要够血腥,就能上头条。”没有冲突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马克·马佐尔说:“确实有许多历史学家有时会想,他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描述人类的肮脏,花那么少的时间描述德性和美丽的事物呢?带着社会向善论的计划编写的世界主义的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性史》——没能证明这条道路的活力。相反,1965年历史学家杰克·普拉姆就说,这套书是失控的百科全书,好像是不完善的电脑整理的。”
马佐尔说:《未曾割裂的过去》提出,唯一可接受的团结是人性的团结:比这偏狭的团结都会把我们区分开,区分意味着冲突。但勾销这些曾经使人们动员起来的概念不是有些寂静主义吗?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是坏的,有时正义需要冲突。
坎纳迪内看上去就像一个天真的嬉皮士,希望人们融洽地相处。当纳粹入侵时,你怎能要求波兰人不要诉诸民族主义?亿万富翁以穷人为代价变得越来越富又该怎么办?你能对失业的人说,以我们共同的人性为中心吗?对坎纳迪内来说,动员的过程是中立的:社会动员有的是为了一些高尚的事业,但也造成了不好的结果。坎纳迪内说:“我不是说不该动员。他们动员时使用的主张不能那么膨胀。”他呼吁的是,群体的身份认同要更加精准、不要那么极端,要增加对话。 过去未曾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