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波拉尼奥积累的素材
作者:孙若茜(文 / 孙若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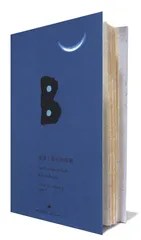 (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
(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
我们得以见到,是因为他的家人及出版人的挖掘、整理,集结成集。与波拉尼奥的长篇巨著《荒野侦探》、《2666》相比,这样的短篇集在他的作品中或许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没有在他生前发表的作品,除了时间上的来不及,更可能是他自己认定的不成熟之作。又或者,它们只是波拉尼奥为自己的长篇创作所积累的素材而已。
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一个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曾先后出现在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里,之后才成为《百年孤独》中的一个成熟的人物形象。同样,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中散落的众多人物和情节,也被很多评论者认为与《2666》、《荒野侦探》密不可分,甚至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在波拉尼奥身后发表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以及中文版即将发行的《护身符》等短篇小说集的文学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展现了波拉尼奥的一路走来。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文版不久前出版,依然由《2666》的译者、翻译家赵德明翻译。书中的14个故事,几乎都在书写于流亡生活中理想破灭的一代人,挣扎于边缘,困于梦魇。“这里面墨西哥的事儿多,文学圈子里的事儿多,很多的的确确就是他的生活场景。”赵德明形容这个短篇集给人一种镜头感:“一个特别的场景说一个具体的人,用具体的特写镜头成为这个集子的特色。”
三联生活周刊: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里,有很多情节、线索与他的长篇有着联系,甚至说是重复。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他的这些短篇作品,它们是否还是独立存在的?
赵德明:现在看来,这本短篇集里的很多小说都像是当时写出来,准备将来写长篇用的,不像是为了马上发表而写的短篇。短篇小说集并不是波拉尼奥自己弄出来的,而是文学代理人、出版方、家属,在他去世后不断发掘他的作品。这个过程应该是,《荒野侦探》、《2666》两个大长篇推出以后,他名声大振,后人觉得他以前积累的东西有价值,他的代理人和财产继承人,他的夫人、儿女从电脑里、抽屉里翻出的很多东西,然后仔细研读,发现这些东西和(他创作的)大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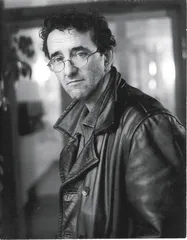 ( 罗贝托·波拉尼奥 )
( 罗贝托·波拉尼奥 )
这个需要资料,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的创作时间表,没有发言权。但整理后如果发现:比如某一篇短篇作品是出自2007、2008年找出的资料,而没有正式发表过,那么肯定就是素材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发表与否,对于这些短篇小说是否为素材,还有没有别的判断依据,像这本书里收录的作品,其本身的写作模式、语言等方面有没有这样的显现?
 ( 赵德明 )
( 赵德明 )
赵德明: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从文字、结构以及故事上来讲都像是有感,然后赶紧写下来,不像一个完整的(作品)。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通话》(《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的一篇)开头就是这样:“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B跟X吹了。……”这显然像写作提纲:时间、地点、日期谁和谁。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作为长篇小说的创作素材积累,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集,当然也包括这本《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其文学价值也就不能独立地看待了?
赵德明: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波拉尼奥的一路走来。要从文本分析的价值上来讲,就是那时候写的东西和后来长篇里的故事的重复性。比如这本集子里面的一篇《安妮·穆尔的生平》,故事看起来是比较完整的,但它和《2666》里面的那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人物名字都换了但故事架子还在,比如他是在哪儿长大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等等。
2003年波拉尼奥去世,这个作家没有了,《2666》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了。那出自哪儿呢?一找,在这篇上呢。他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护身符》也有这个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凭借这些相似、重复把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理解成《2666》、《荒野侦探》的创作雏形么?
赵德明:这么说就像是有计划的说它了,其实它都不是。在那段时间里,波拉尼奥觉得有东西可写,就写了。他白天老老实实给人打工,照常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他还很想写,而这些就像是素材的积累和准备。《2666》问世的时间是2003年,这些短篇被发掘出来是在2003年之后。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这样的大作家在前期准备了什么。
刚才谈到过要列出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哪个短篇的工作,这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那个时期他的那个遭遇,比如他在莫斯科境遇不好,在家庭、生活、与朋友的相处中遇到很多具体的事情,具体什么触及了他,因为这些短篇的的确确是他在那个时期的心情。
三联生活周刊:你用“全景式写作的小说”评价《2666》,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里,是否也展露了一些“全景”的视野?
赵德明:是的。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他见得多,读的书也多。虽然是短篇,有一个具体场景,但陪衬这个场景的很宽,他的视野、思想跑来跑去经常会有,法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他太熟了,这个经历造就了他的宽。等他写一个具体场景的时候,又写得很深,这就是他的功夫。好作品必须有深度的刺激性的细节,人、心、场景,要细到头发丝的颤动,心里的瞬间都能写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在可读性上,把它们纯粹当作一般的短篇小说,不去管它是否为素材,也是不错的作品?
赵德明:是的。他写得很碎,但是不得不碎。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是素材,但也是闪现着文学味十足的东西。虽然还是个框架,里面还没有丰满。其实,包括《2666》也有这个问题,如果《2666》真的要加工、修饰,整体上再打压,那就更不得了了,但是来不及做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赵德明:特别需要关注波拉尼奥短篇里暴露出来的,是人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到里面去读的,是一种人类的疯狂,人类的偏执,是人类在各种“欲”背后驱使出来的邪恶。“波拉尼奥们”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容易,不是靠书本,而是需要血的残酷的教训。很多问题,波拉尼奥不是简单地归结于政府、社会,不是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的问题,而要比这个深刻得多。如果要停留在政治层面,那就没有看到北欧又如何、美国又如何,没有看到那里面的肮脏、龌龊。没有绝对美好,都是相对的。
比如他写德国纳粹,也写苏联红军,按照过去的文学路数,文学评论家会指责他的立场,现在不会。你可以拿出史实,苏联红军那会儿进入柏林、进入东北时候的烧杀和德国法西斯进入一个村庄时候的烧杀有什么不一样?纳粹杀犹太人,苏联红军对波兰的战俘就没杀?我们作为读者看到这些的时候目瞪口呆,能说正义或非正义?波拉尼奥就直接指出这两种都是邪恶,本质都是杀人而无法有辩词,革命的杀人和反革命的杀人只是名义上的不同,你只要掌权,历史就由你来书写。他反对这个。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这本集子里的故事,激情、失败,整体的伤感和无奈,也都归结到这里。
赵德明:他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揭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以及精神道德危机。他从不转弯抹角:21世纪全球人的势力、实力、功利,这几个词是不分国家种族的。
翻译了他五六本作品之后,我现在的看法是:他太悲观。他觉得人类就是这么邪恶,有权了就贪,没钱了就急,有点儿钱没点儿钱的人就混。他认为,不管什么人都是受利益驱动,大有大邪恶,小有小邪恶。不管高贵还是卑微,他都往人性骨子里的复杂性扎一针,在这点上毫不客气。这就是他让很多人受不了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曝光,让太阳晒一晒,但他又不告诉你希望在哪儿,没告诉你出路。 素材夜晚地球最后波拉尼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