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委托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林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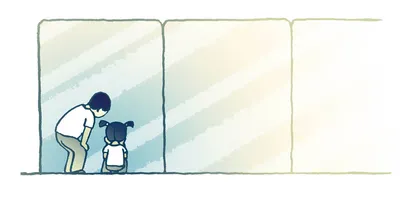
深圳喝酒时和连襟的弟弟讲说天津的黄家花园,都掏出了遥远记忆。他们幼时也住过,还记得一个可能是大教堂后来改成了大合作社,里面卖什么的都有,主要副食、水产干鲜等等。“文革”时都属于国营买卖,很热闹,很集中!它坐落点就顺着委托店往东走吧,不远的,没到拐弯的“玉华台”那里。我还清楚记得:跟我姨排队买厚皮的“三白”西瓜,不怕耗费时间,就嗜吃这口儿。
那时我央求姥姥放我下楼玩,说好的地方一个是新华书店,一个就是对面委托店,不敢也没有别的目标。我曾经躬下身,或者蹲下来看那三间门脸的玻璃橱窗里的宝贝!其实都是古色古香的红木箱、梳妆台、旧怀表、座钟、毛笔架什么的,还有玛瑙翡翠、珐琅瓷瓶、印章字画……因为姥姥只许我在近处玩,我太熟悉委托店了,几乎每周登门。它后院小二楼上,收东西的房间和交易画面乃至来客话语,我都熟悉和旁观过……其实在黄家花园,我可能也结识过短暂的玩伴,就在委托店一溜儿的某个里弄中,相对狭小的必然是平民的屋子里,我翻看了奇妙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小儿书。只是我很快就离开了,反而那新华书店,我流连的时间更多,我还不知深浅地要求舅舅给我买书,他拒绝了,没义务给姐姐的孩子花钱。
古老色彩商店,黄色牛肉铺,糕点房,邮报亭,边道一侧有卖炸糕小豆粥的,都没了。这叫迷失在自己的家乡。参照物全荡然无存。当年西站通往河北大街那条路没拆的时候,我总见“猫不闻”饭馆的招牌,它证明这天津人跟对联一样起哄架秧子的风格。冠军只有一个,后面的跟屁有什么可美的?但是也奇妙了,故意跟“狗不理”别苗头的“猫不闻”在天津存在了更多年。忍不住回忆俗语:穷梆子,浪评戏,杂巴地听曲艺。我在西安道的早点铺,就是靠着委托店一溜儿的粮店前面跟人打过架,粮店门口的打架,不在乎他们人多,潜意识想我来自武术之乡怎么可以输给你们?
那时红桥区的人以彪悍著称,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三条石所在地,也是三级跳坑所在地。“文革”期间,解放后的痕迹没怎么变化(才十几年),有钱人一般住市内,和平、河西区什么的,而平民百姓聚集在红桥南开河北了。还记得我技校的老师老魏在东门里古旧书店昂然坐凳子上跟卖书人聊到兴奋忘记了,不自觉地手就伸向裆部挠痒痒——他一口的方言显然上代人是农村来的。吃大饼干嚼,就着鼻澄呢;朴素而辛辣的口语,特别有互相讥讽的意味。
红桥区,和平区,两个区的高雅粗俗对比那时心里默默在搞,没和别人讨论过也没在别处怎么读过。戴眼镜的王老师领小学的孩子们远足去参观展览,在和平区的宽阔马路边休息,指着远处楼上的木质防阳光的双层窗子说:“那叫鱼鳞板,为挡阳光的,里面人能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还补充一句:“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当时在学生群体中,我默默不语,仿佛异己分子。
夏日的下午,我在阳台上看书,清楚听见楼下“义达里”小胡同内传来查抄物资的拍卖声,是马路对面委托店的人把用汽车拉来的东西直接推销了,喊得很热闹,和现在各种马路上的推销没什么两样,那时也讲赚钱的。虽然以“破封资修”名义。
姥姥带我去街道开会,提前装扮得很庄严,路上有问话:“这是白眼啊?当姥姥的拐棍了。”其实听了街道的通知是阳奉阴违的,不得不去,就应付人家而已,我们坐在挤仄小空间里,听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西安道的居民,曾是最神秘最安静也最矜持的一族人吧!
成都道与西安道相交,还有个圆茅房,连襟也记得,因为它雄伟。夏天夜晚大马路上还曾演过宣传《红灯照》的木偶戏,也难忘了。委托店特别例外,属于童年记忆里一桩神秘的暗示,侧面展示着更豪华或者更陈旧更坚实的生活方式,不值钱的东西谁敢往委托店送呢?距离我姥姥家那么近,几乎是被漠视地存在,那时我也没研究过它的兴衰。
现在我找不到委托店了,同样瞧不到鱼鳞板,我的王老师也不知哪去了。我用伤残的手臂抚摸你,这还似前人诗句,我默默像个路人甲走过我童年的土地,留下无限回忆的土地,已经与它格格不入。我憎恶雄伟的大超市,但是它造福于当地人,没理由为了“小资”情绪排斥变化的景色。还记起了穿越长长河北路到民盟去听课,我太爱成都道了!它附近的民园体育场被拆,不少人骂街。
委托店几乎是,必然是所有关于黄家花园的最深刻印记。如今它没了。谁叫我早就告别姥姥家。在十字街同学家帮助盖房后,沿着曲里拐弯的胡同直到海河边,我们去洗掉一身的脏土和汗水,那时觉得自己可主宰未来。 消失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