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动物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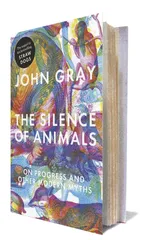 ( 约翰·格雷的作品《沉默的动物》 )
( 约翰·格雷的作品《沉默的动物》 )
进步神话
直到11年前,约翰·格雷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学者,虽然他是名校教授,且成功地预测了全球金融危机、伊拉克战后的灾难。2002年,格雷在出版《刍狗》一书后一举成名。他在书中说,人类没什么特别,跟其他动物一样;社会和道德进步并不会必然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来;自我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理性的。“人类是制造武器、热爱杀戮的动物。”由此格雷被认为不但能够预见未来,而且能够看透我们的灵魂,透过文明的外表看到其后嗜杀成性的兽性。近来格雷又推出了《刍狗》的续作《沉默的动物》。
约翰·格雷曾担任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教授,现在是一位全职作家、哲学家。64岁的他身体依然健壮,跟他的日裔妻子美惠子一起住在巴斯。他的著作包括《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刍狗:关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思考》、论文集《格雷的解剖》。畅销励志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也叫约翰·格雷,但两个人的观点分歧很大,尤其是在幸福问题上。写“男人来自火星”的格雷相信幸福就在拐角处等着你去抓,写《刍狗》的格雷认为寻找幸福是浪费时间。“把幸福当作目标会让人变得不那么爱冒险。最后是努力获得有趣、充实。”
传说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拒斥他那个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甘于贫穷,住在一只桶里,靠吃洋葱为生。他还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徒劳地寻找诚实的人。约翰·格雷有点像第欧根尼,虽然他没有桶和洋葱。他的新书对一些目前被珍视的信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文主义和进步信仰是轻率浅薄甚至是危险的。
他写道:“神话的力量在于从意义的碎片中制造意义。神话不是冻结于时间中某处永恒的原型,它们更像是脑海中播放的一段音乐。好像是无所由,它们跟我待在一起,随后就消失了。”他指出神话有许多种,有好的,有不那么好的,还有的非常有害。令他为之着迷的是,看上去对立的神话被现在一些专家平滑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一点在进步这一概念上尤为明显。“当代人文主义者援引进步概念时,他们融合了两种不同的神话:苏格拉底的理性神话和基督教的救赎神话。”现代人傲慢地以为,在进化过程中的某一个点,人类做了一个奇迹般的飞跃,超出了动物状态,成了半神半人,不仅控制了地球,还控制了命运。但人权方面的进步如宗教自由、种族平等等都是可逆的。格雷说:“我们以为我们不会退步,但是我们会。一直都是这样。最近的例子是虐囚。像廉价的音乐一样,进步神话令人精神振奋,但同时令大脑麻木。”
 ( 约翰·格雷 )
( 约翰·格雷 )
进步神话也许是欺骗性的、很危险的,但格雷承认神话、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最高虚构”的必要性。没有这些神话,我们如何自处?为了破解DNA的密码,克里克和沃森就得相信他们的研究有着宏大的目标,如果药剂师没有坚持研究麻醉剂,我们看牙医的经过就会更加难以忘怀。
格雷不加分别地使用“相信进步”和“未来会更好”,好像它们是一回事。但是它们当然不是一回事。你不需要相信明天必然会更好,也能努力让明天变得更好。萨特半个世纪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人不需要为了完成他的工作而怀抱希望。”放弃良好的意愿必然会获得成功这种妄想正是为了取得进步而诚实劳动的前提,而非其障碍。
 ( 丁尼生 )
( 丁尼生 )
格雷说,人类不是热爱自由的动物,我们寻求的往往是专制,因为专制能免除清醒的重负,为仇恨和暴力等被禁止的冲动颁发许可。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赫尔岑认为,说人生而自由,简直有如说“鱼生来就是要飞的,但它们处处在游”。对自由的渴求不是我们唯一的冲动,也不是我们最强大的冲动。当生活变得艰难时,对自由的需求就会让位给其他的需求。这可能纯粹是为了安全,或者是为了攻击、边缘化甚至是消灭他人。
格雷真的认为一切改善的计划都是徒劳的吗?由于他的批判完全是消极的,人们很容易假定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走到公开赞同虚无主义那一步。从行动上看,格雷跟他取笑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站在和平、繁荣、理性、法治这边。如果他真的认为一切改良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那就无法解释他为何信奉沉思而非享乐主义甚至自杀。
不可信的语言
在全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格雷开始探索如何生活这一问题。传统的回答包括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理解自身的完整都被他弃绝了。他认为,它们都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因为它们都以人性本身为中心,在他看来,人性正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克服自身。格雷受到了“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的吸引,从人类思想逃到单纯的存在。他在否定神学和动物的沉默中找到了线索。
格雷说:“传统宗教和现代世俗宗派的罪责部分源于对语言的崇拜。真正的怀疑论始于、终结于对语言的不信任,往往在诗人、神秘主义者而非哲学家中能找到这种怀疑论。”他称赞了英国诗人托马斯·休姆,不是努力用词语表达公共的、不存在的东西,而是描述个人的意识加以过滤过的世界的客观事实。“伟大的目标是准确、精确、明确的描述。”英国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批评丁尼生用精确、详细、动物学的方式描述一只飞翔的蝙蝠,他应该做的是谈论飞翔的蝙蝠给观察者留下的印记。
瑞士神学家马克斯·皮卡尔德说动物的沉默是“尚未得救的、坚硬的、凝固的沉默”,而人类的沉默是“透明的、明亮的,因为它面对世界”。格雷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虽然动物缺少人类建构其自我形象的内心独白,“这怎么就使人类处于更高的水平了呢?为什么打破沉默然后大声努力地重启它是一项成就?人类忍不住要透过语言的面纱来看世界”。
沉默对其他动物来说是一种自然的休息状态,对人类来说,沉默是逃离内心的喧闹。其他动物逃避的是它的同类制造的噪声,人类是唯一逃避内心的噪声的动物。我们把沉默当作自我的庇护所,积极地逃离无休止的意义建构,动物则只是简单地闭上嘴。“用语言来克服语言显然是不可能的,转向内心,你发现的只会是作为你的一部分的词语和图像。但如果你转向你之外,转向小鸟和动物,你就能听到超越词语的东西。”康拉德在《文明路上先锋站》中提供了一种动物的视角,两个脱离了其文明的比利时人“生活在这个大屋子里,像两个盲人似的仅能辨别顺手摸到的东西,而无法窥知事物全貌。河流、森林、孕育着生命悸动的莽原就像一片巨大的旷野,即使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也不能将事物展示得清晰明了。眼前事物的出现消失飘忽不定,毫无关联”。
牛津大学学者彼得·康拉德讽刺了格雷的反人文主义立场:“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1766~1817)曾经说,我看到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格雷前一本书叫《刍狗》,指涉的是美国导演山姆·佩金法的同名电影,片中一群暴徒欺负一位数学教授。《沉默的动物》让人猜测它演绎的是不是电影《沉默的羔羊》,但作者说,这个词源自瑞士神学家马克斯·皮卡尔德,他说动物的沉默不同于人的沉默。”
“皮卡尔德感伤的评论唤起了格雷的共鸣,这令人迷惑。虽然他蔑视自己的同类,但说到带羽毛的或者四条腿的朋友他就变得很柔弱。他就没被狗的狂吠、发情的狐狸的叫喊惹得无法入睡过?他一页又一页地引用贝克对游隼的赞美,而忘记了抓兔子的老鹰。每当我看到黑色的、凶恶的乌鸦撕破垃圾袋吞食里面的剩菜,我就对人类感到好受些。我担心格雷最终会像斯威夫特笔下疯疯癫癫的格列佛一样,人类令他感到作呕,以至于他要去马厩跟他的马在一起生活。” 动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