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负鼠”托·斯·艾略特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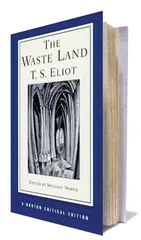 (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与他的诗作《荒原》 )
(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与他的诗作《荒原》 )
现代主义革命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说:“你也许跟艾略特的评论搏斗了很久,但仍然终生迷恋他最好的诗作。《荒原》和《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空心人》、《三圣人的旅程》等,艾略特最不朽的诗作的名单上,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小老头》和《小吉丁》。但刚才列举的5首诗是他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成就。”
艾略特令人难忘的诗句包括:“历史有许多捉弄人的通道,精心设计的走廊、出口,用窃窃私语的野心欺骗我们,又用虚荣引导我们。想一想,我们注意力分散时她就给,而她给的东西,又在如此微妙的混乱中给,因此给更使人们感到乏。”(《小老头》)“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荒原》)“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声响,而是嘘的一声。”(《空心人》)美国艺术评论家罗杰·金博尔说:“艾略特的诗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心智装备,它们唤起的现实是我们的现实。他的诗句回响在20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它们不仅是令人难忘的演说,还是存在的路标和里程碑。”
艾略特早期的诗歌是都市的、反讽的,充满高雅的倦怠(警觉、烦忧、彷徨)。这种风格惹恼了不喜欢反讽的乔治王时代的趣味。《荒原》因为怀疑时代、为迷失的一代代言、对前辈感到幻灭而受到右翼的憎恨。但这首诗发表后,艾略特已经告别了诗中绝望的态度。《荒原》主要是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干预的结果。庞德把这首诗从原来的大约1000行删到433行,修改了几个重要的措辞,还弱化了其宗教成分。庞德的编辑工作终结于《空心人》。艾略特诗歌和生活中的宗教维度变得越来越突出,他拒斥了现代主义,转向了中世纪性质。他后来的诗歌在结构上是现代主义的,但在态度上背离了现代主义者的预设。1928年,艾略特在文章中说,现代主义是“心智的枯萎”。《四首四重奏》受到信徒们的欢迎和人文主义者的谴责。艾略特的诗很容易成为批评者的目标,其语句和语调非常特别,甚至有些矫揉造作,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戏仿。《空心人》的最后一节是:“在思想和现实中间,在动机和行为中间落下了阴影。在概念和创造中间,在情感和反应中间落下了阴影。在欲望和痉挛中间,在潜在和存在中间,在精华和糟粕中间,落下了阴影。”有人戏仿道:“在神秘和欺骗,在繁殖和分化中间,伦敦塔倒掉了……停止流血……停止呼吸……嘭!”
《荒原》发表于1922年1月24日,一个多星期后,2月2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哈佛大学英语教授路易斯·梅南德说:“庞德认为,艾略特给他们的运动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这是一场怎样的革命?现代主义作家们把文学引向了内心和下半身,引向头脑中和腰部以下发生的事情。这是读者体验到的现代主义,也是现代主义著作招致审查的原因。”对现代主义作家来说,现代主义主要是技巧问题。现代化不是制造出新的东西,而是使旧的东西跟上时代。《普罗弗洛克》是一篇戏剧化的独白,一种标准的19世纪的诗歌类型。这种形式有着内在的紧张,独白者的呈现和读者看到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在《普罗弗洛克》中,紧张是由语调变化创造出来的:标题本身,出其不意地从《地狱篇》中引用的意大利文,诗的开头把黄昏比作一个被麻醉的病人,两次说到“房间里女人们来往穿梭,谈论着米开朗琪罗”,它们像是属于另一首诗,被没来由地拿过来的叠句。它像一幅立体主义肖像。艾略特取了一种原始的东西,用当代的习惯用语加以改造,就像毕加索用非洲面具画妓女的肖像,乔伊斯将奥德赛置于尤利西斯之下。在庞德和艾略特看来,重要的是能看到当代皮肤下面旧东西的骨头。
艾略特写诗时经常引用他人的诗。《伯班克》一共32行,许多地方借用或暗指了其他10多个文本。这些文本大多跟《伯班克》的背景威尼斯有关。艾略特只是把挂毯翻了一面,把背景放到了前景中。他写的关于威尼斯的诗,也是关于威尼斯的诗的诗。经常有人指责艾略特剽窃,这让他开心,他还加了一些批评家看不出来引自何处的引语。
《荒原》中引用的就更多了。这首诗是指涉、引用、附和、挪用、杂糅、模仿、口技的大杂烩。它用了7种语言,包括梵语,结尾有好几页注释,讽刺学术引用的格式:“引自佛教的《火诫》,其重要性相当于耶稣的登山宝训。全文见亨利·克拉克·沃伦的《英译佛教》(哈佛东方丛书)。”很快,这些注释就被当做真正的注释,当做有用的注解和理解其含义的钥匙。在《诺顿英语文学文集》中,艾略特的注释不是被放在诗的结尾,而是印在每一页的下方,成了脚注,散落于编辑加的注释中。但这些注释不是阅读该诗的指南,而是全诗的一部分。它们没有解释诗中的谜,它们是又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谜。《荒原》是对战后欧洲状况的报告,《尤利西斯》是三个都柏林人一天里发生的故事。但它们都是意义的魔方,挪用了多种风格和传统。艾略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尤利西斯》捣毁了整个19世纪。它使乔伊斯本人写不了第二本书了,它显示了所有英文风格的无效。”它好像穷尽了文学,是一个终结,他希望他的诗也一样。
好奇与思考
艾略特在他的职业生活中写的文学批评多于他的诗歌和戏剧,甚至比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加在一起还多。在成为著名诗人之前,他已经是著名的批评家了。一生中他不停地转变取向和立场,比如他创造了“感性的脱节”、“客观对应物”等颇具影响的批评术语,后来又认为这些概念不太站得住脚。30多岁时,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银行职员,就大胆地撰文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一部“在艺术上失败了的作品”。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他阐述了一种重要的诠释学观点:我知道我正在看的是一幢房子,因为我已经熟悉那些看上去跟它有点像的东西是房子,所以我可以说我正在看的房子是很大、很丑、很现代。我读一首诗时也是这样:我把它跟我读过的其他诗联系起来,过去的诗决定了我们对新诗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新的诗也决定了我对以前读过的诗歌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普罗弗洛克》之后,《地狱篇》读起来就不一样了。艾略特说,一位诗人越是沉浸于全部的文学之中,他写的诗越新,越能影响旧的诗歌。
艾略特说:“我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但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时代要求的是文学上无形的主观性,政治上的平等主义,宗教上的低教会或无教会浪漫主义。所以,在70年代中期,艾略特的地位仍得到承认,但人们这样做时很不情愿,开始强调他在政治上反动、保守,在文化上持精英主义立场。艾略特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1月去世,他的名誉好像是牢不可破的,但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萌发。他不再受人推崇的重要原因是,文学与文化的严肃性消失了,这显示了难啃的现代主义与松软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隔。
罗杰·金博尔说:“艾略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赞同他对女性、犹太人、教育或宗教的态度,而首先是因为他写的能引起人们共鸣、好奇的诗。”《荒原》中有这样几句:“今晚我心情很乱。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你总不说话。说呀。你在想什么?想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想想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写道:“诗人之所以能引人注意,令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感情,他特有的感情尽可以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他诗里的感情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能以罕见的激情和信念鼓舞所有他接触到的东西,他用他的诗歌和评论讨论重大问题。读艾略特的著作能培养严肃的态度,但并不是说艾略特总是很阴郁。他也写过一些戏谑的作品,如《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老负鼠”是庞德给艾略特取的绰号,意思是装傻充愣、大智若愚)。读艾略特的作品会让人感到强烈的活力和漂浮感,这是因为艾略特不停地去发现,因为他渴望把握现实。
(文 / 薛巍) 艾略特负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