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盐与光,加上想象——追寻“慢下来”的古老摄影术
作者:孙若茜(文 / 孙若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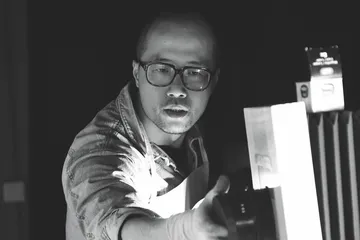 ( 摄影师郑雨 )
( 摄影师郑雨 )
把桌子上瓶瓶罐罐的药剂摆弄一番,举起用特殊制剂擦了两三遍的清透的玻璃板,对着光线仔细检查,戴着防毒面具的郑雨,在准备把这玻璃底片涂上火棉胶之前高举起一只手,示意影棚里各自忙着手头工作的助理,众人随即达成默契,停止走动,甚而屏住呼吸。郑雨这才拿起经几天时间过滤沉淀而得的火棉胶,涂抹在玻璃底片上,并走近自己制作的相机前……
那瞬间坠入异常安静的周遭,看似过分小心翼翼的举动,仿佛是在进行某种精密的实验,而近乎显得有些庄重的氛围,又仿佛是在经历某种朝圣的仪式,这些都绝非摄影棚里惯常出现的拍摄前奏。
可这确实是一场拍摄的前奏,这一年多来,这样的“慢”,经常出现在这个过去通常用来拍摄商业广告的摄影棚里。而这种采用银盐与光成像的、古老的叫做湿版摄影的技术,其完全纯手工的、繁复的漫长操作过程正是让郑雨迷恋的关键所在。
1851年,英国伦敦的雕塑家阿切尔(Fredrick Scott Archer)发明了这种摄影方法:将硝化棉溶于乙醚和酒精的火棉胶,再把碘化钾溶于火棉胶后马上涂布在干净的玻璃上,装入照相机曝光,经显影、定影后得到一张玻璃底片。火棉胶调制后须立刻使用,干了以后就不再感光,所以称为“湿版法”。湿版法操作虽然麻烦,但比起更早的达盖尔银版法,成本缩减为原有的1/12,曝光更快,影像清晰度也更高。于是,此后的近30年,湿版摄影一直统治着摄影界。在此期间,肖像摄影艺术得以迅猛发展。直到19世纪70年代,火棉胶湿版法才受到玻璃干版的竞争,并在1880年前后被工业生产的溴化银干片取代。
中国摄影史和世界摄影史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交集,在此之前的古老工艺和技术在中国都没有被广泛实践过,我们使用了便捷的胶片,而胶片之前的化学成像历史却一直鲜有人问津。
 ( 郑雨的湿版摄影作品 )
( 郑雨的湿版摄影作品 )
2010年时,湿版摄影在国内摄影圈里最多不过被十余人掌握和把玩。两三年后的今天,随着国内三两位摄影师以湿版摄影为手法拍摄、制作的影展面世,湿版摄影才被更多人熟知。目前,北京已形成有三五百人规模的湿版摄影圈,在南方一些阳光充足,即拥有更好的曝光条件的城市也逐渐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即便这个领域在当下与数码摄影相比,依然显得极为小众,但是湿板摄影的队伍确实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已成二三十倍的增长。
也许就像郑雨说的,在这个图片泛滥的年代,我们的视觉被太容易得到的各种图片、照片充斥甚而污染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审美可以被吞没,也可以反而变犀利,人们对成像的画质越发挑剔。而太易得到又索然无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逐过程,古老的摄影技术就这样被重拾。
( 郑雨的湿版摄影作品 )
除了是商业广告摄影师,郑雨还在一家摄影学校里任教。讲课的时候,他经常能看到学生对着数码相机的照片预览,相互讨论着把照片在后期上用PS调成什么颜色、什么状态,拍摄前却并不谨慎思考,按取快门更毫不吝惜。“一个好的摄影师不在于后期把照片修成什么样,而在于拍成什么样。”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如此在摄影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样的话。
郑雨更是希望有一天能专门开设湿版摄影的课程:“重点不在于学会的人是不是真的用湿版摄影的方法拍摄什么,而是大家都太需要时间慢下来反思自己过去的激进。回到化学成像的时代,体会每次按下快门时充满的未知和期待,确是个美妙的过程,从中体会成像的来之不易。而湿板摄影无法用后期对图像加以弥补,更能使人习惯谨慎,让人即便是做数码、胶片的拍摄也会变得三思而后行。”

但这也只是个愿望而已,在习惯不用过程论英雄的速食年代里,学习摄影的人更多地也只是把手里的相机和技术当做谋生的手段,希望用技术带来效益。即便有零星对艺术的追求,大多也是期盼在飞快且不计其数地按下的快门里,总有那么一瞬灵光一现,捕捉到天时、地利、人和,好光线、好角度、好神韵,进而好作品可以拿来换更强大的器材。不用说湿版摄影,就连胶片如何冲洗,个中所需讲究、把握的水温、时间以及其他,能愿意去玩儿明白的,已是寥寥无几。
确实,湿版摄影的拍摄过程本身就非常繁复,再加上前期相机的制作,多种药剂需要的精细配比调和,以及后期用茶、咖啡或者玫瑰花汁、蓝莓汁作为调色剂所进行的,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个星期的同样古老的照片洗晒工艺,光是时间成本已是不少。
更不用说拍摄过程里有诸多需要经验才能拿捏准确的节点,此前都需要经过10次,甚至20次地反复试验也同样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再者拍摄中每个细节都需要全神贯注、屏心静气,哪怕只是往玻璃底片上涂抹火明胶,都要禁止所有周遭人走动,以免底片沾染灰尘而影像拍摄等等。
平衡利益,成本终究还是很高。往往专业的商业摄影师都更懂其中所需要耗费的精力财力,也更容易以利益得失来衡量和看待一张照片的出炉。于是,他们干脆选择不碰这个领域,即便湿板摄影能够带来胶片、数码都无法比拟其细腻程度的成像效果,以及无法复制的独特属性所可能带来的更高的艺术价值。

郑雨用湿版摄影赚过杂志的稿费,他希望慢慢将湿版摄影技术引入广告界,希望能让它自给自足,但同时又极端地不把湿版的作品作为常规的商品出售。原因是,不管多少钱,他都依然觉得卖得廉价。他最常和朋友说的是,你要喜欢,我就给你拍,送给你,别来谈这一张是3000块还是5000块钱。花了如此多心力的东西,实在很难定价。当然,前提是只能给志同道合的人。
遍地形形色色的影棚里,高声播放着快节奏的音乐,不管你是摄影师还是模特,都需要高度兴奋起来。但是在进行湿版摄影的棚里,你需要慢下来。他说,在每个步骤都需要在缓缓安妥的过程里进行,摄影师如果不首先静下来,周围的人,那些在数码时代养成快节奏工作习惯的模特、化妆师、编辑就更不可能把速度降下来。“即便是他们催我,我也要求自己慢下来。”在基于湿版技术本身要求的操作程序都结束后,郑雨还要再次检查模特的衣领、头发等等细节,“一个眼神的角度都是需要慢慢调整的”。
如此繁复斟酌的缓慢前奏,再加上技术本身由感光度极低的特性所要求的长时间曝光,使得这种古老摄影术在摄影师与被拍摄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微妙的关联,也使得摄影师更加可以在“临产”前,与自己的作品如母亲与腹中胎儿一般在心里进行细细地攀谈。
而被拍摄者的状态被迫地保持,使得人在面对镜头时瞬间造作出的躯壳形态得以自然垮塌,等待还会掐灭造作的神色,使内心的灵光升腾于表,呈现出自我最本来的状态。一个好的摄影师不只是可以和被拍摄者沟通,还更将引领他进行深层的自我沟通,带他返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瓦尔特·本雅明曾在他的《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里说:“长时间的曝光过程使得被拍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间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长时间的曝光过程里,他仿佛进到影像里头定居了。”这也正是为何早期肖像摄影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一抹灵韵,而匆匆快照遍及天下的时候,相片里多是同一张浓妆艳抹的庸俗面容。
这一年多来,郑雨用湿版摄影的方法拍摄过人像、静物,动态、静态,也曾用骷髅作为模特,造出巴洛克式的发型,戴上珠光宝气,传达一种皮囊都已逝去,而依然有美存在的主题,拍摄的内容可以说,很杂。与一般摄影师把自己以拍摄主题归类于风景、人像或是景物等等摄影领域不同,他并没有过多执著于镜头前的某一种形态,对于他来说,用湿版摄影的手法呈现出来影像,这个呈现方式,才是他所拍摄的真正主题。 摄影术想象加上追寻慢下来古老银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