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恨,我吃掉
作者:陆晶靖(文 / 陆晶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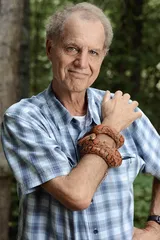 ( 哈尔·赫尔佐格 )
( 哈尔·赫尔佐格 )
“蛇跑到别的地方去觅食了……她加完班,提着两只沉重的褐色纸袋回到家,一个装满了外带的印度菜,另一个装着两只白老鼠,宠物店老板告诉她那是某个高中实验用剩的,它们刚跑完迷宫,还有点恍神。她温柔地唤它出来,把灯逐一打开,到每个房间去巡视,最后发现它在沙发上蜷成一团,睡得很熟,身体中间隆起一块,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这是汉娜·亨蒂的小说《动物怪谭》中的一段。蟒蛇不是一种常见的宠物,在美国,蛇、蜘蛛和老鼠是最令人害怕的三种动物,但令人意外的是,有40万人选择了蛇作为宠物。西卡罗莱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尔·赫尔佐格在实验室里养了一条研究用的蟒蛇,在一段时间内不停地有朋友和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给他打电话:“听说你用小猫喂蟒蛇?”
美国西卡罗莱纳大学的哈尔·赫尔佐格把这个例子写进了他的书《我们爱,我们恨,我们吃》。他找到了谣言的来源,最早散布的人家里养着好几只猫。在美国,生活着约940万只猫,这几乎是人类之外的第二大肉食动物群体。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每天平均要吃55克肉(猫罐头里含有牛肉、羊肉、鱼肉甚至马肉),以这个数字计算,全美国的猫每天要吃掉500万公斤的肉,约相当于300万只鸡。除了吃肉,家猫和野猫也是很好的小动物杀手,每年有约100万只小动物(鸟类、兔子)死于它们之手。哈尔·赫尔佐格估计,每年死于小猫之手的动物数量是实验室使用的动物数量的10倍——那么为什么要责备养蛇的人?蟒蛇虽然体型庞大,但它们很少剧烈活动,也无需能量保持体温,一年只需要吃2.5公斤肉,而一只猫的消费至少是20公斤。虽然不太容易接受,但显然猫对肉的需求更大,也更残忍。
哈尔·赫尔佐格说,在人和动物以及那些和动物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充满了误解。我们对动物的爱与恨以及食欲,都不是想象中那么直观,人们经常丧失理性听由情感操纵。即使是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也很难在一番细究之后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是个充满了矛盾的领域,心理学、医学、行为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哲学在其中纠缠。即使是数字也会互相打架,盖洛普公司最近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70%的美国人是爱狗人士,可家猫的数量却远远超过狗,另外,狗也是排在蛇、蜘蛛和老鼠之后第四大令人害怕的动物。
这个例子至少说明人们在动物问题上经常言行不一致,不过猫、狗都还是幸运的,它们得到了人类的庇护。这是因为它们的样子比较可爱,动物的长相决定了人类对它们的态度。这对于有3亿年历史的中国小鲵这种濒危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1986年,中国小鲵与大熊猫一起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但如今连认识它的人都没有多少。而大熊猫则被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选作了会标。在全世界约6.5万种脊椎动物、鸟、鱼、爬行和两栖类动物里,人类只喜欢其中极少的一部分。那些有黏性皮肤和有太多腿的动物则让人看一眼就感到嫌恶。而如果动物的脸长得和人类有相似之处,则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这是一种本能现象,哈尔·赫尔佐格说,小动物的脸和婴儿的脸非常相似,大脑袋、宽额头、大眼睛,面部曲线柔和。相似度越高则越受欢迎。迪斯尼在制作动画《小鹿斑比》的时候,瓦尔特·迪斯尼要求动画师按照这个原则来修改他们的作品,缩短鹿的鼻口部分,增大头部和眼睛,让观众甚至能在近镜头的时候看到鹿眼里的细节,结果这部动画刚一推出就大受欢迎。米老鼠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对比米老鼠的初稿和现在的差别,人们会发现头部的比例被放大了很多,如今米老鼠的头已经有躯干的一半大了。有时候长得可爱也能帮助动物多活几天。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海豹捕杀业很兴盛,但也因其血腥程度一直受到非议,1987年,加拿大政府迫于压力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捕杀出生14天以内的海豹。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海豹的皮毛还是白色的,太容易让人想起婴儿。海豹的皮毛之后就会慢慢地变黑,幸好加拿大的黑人数量很少,否则这种理由也会遭到民众抗议。在谈论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时候,人类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同样的动物在不同的文化中会遭到不同的对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瑟普尔(James Serpell)教授研究伦理学和动物权利,他提出了一个十字范式,横轴是动物的可爱程度,纵轴是动物对人类的实际功用。在这个坐标系里,即使是狗这样普通的动物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区域。在欧美,狗当然又可爱又有用,但在沙特狗却是遭人厌恶和有害的。刚果伊图里森林中的俾格米人唾弃狗,经常打和踩踏它们,狗只能翻垃圾找吃的,但同时他们在狩猎时又需要狗。即使是同样的族群,对于动物的情感也会变化。美国纽约大学的科林·杰尔马克(Colin Jerolmack)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篇叫《鸽子是怎么变成老鼠的》,150年前鸽子在纽约人的心中是“可爱但无用的”,如今已然完全是“讨厌且无用的”。2007年甚至有一个议员提议立法,对擅自喂鸽子的人罚款10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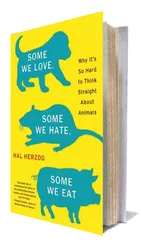 ( 作品《我们爱,我们恨,我们吃》 )
( 作品《我们爱,我们恨,我们吃》 )
哈尔·赫尔佐格还提到了人和动物关系的另一个困境:科研。每年有大量的动物在实验室里被注射各种药物甚至解剖,其中有些需要饲养的动物甚至有自己的名字,这让研究人员也颇感不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1859)中写道:“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在活体解剖的时候狗一边忍着痛,一边还舔着手术者的手;只要这个人的心不是石头做的,那么他生命中余下的时光都将带着悔恨。”三年后他在修订版中加了一句:“然而,科学上的收获会为这种行为正名。”1881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相信,一个人在生理学研究上犹豫,就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笛卡儿认为动物没有感情,这种观点已经完全过时,达尔文通过解剖证实动物在某些生理机能上和人类相似,大象或者猴子为同类的死哀恸的表情也被相机记录下来,科学家下刀越来越困难。一项调查显示2/3的英国人赞成拿小白鼠做活体实验,但95%的人反对在实验中使用猴子,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猴子比小白鼠更合适。与人体越接近的动物,往往科研价值更高,可是却越容易遭到动物保护人士的反对。人类对于动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但这种认识的结果却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和动物的相似性,反而在情感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如果在《变形记》里主人公的家人知道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的甲虫还具有人的感情,也许会不那么嫌恶他。
目前具备可操作性、又能被大多数人的情感所接受的实验动物是小白鼠。1966年,美国通过了《动物福利法》,其中鼠类不属于被保护的范围。2006年,全美科学界消耗了6.6314万只狗、2.1367万只猫、20.4809万只天竺鼠用于研究,而小白鼠的量没有记录,因为数目太大了。缅因州的杰克逊实验室每年培育出250万只小白鼠供全美使用,其中包含4000个品种,如果买家对基因有特别的要求,实验室还能用一年的时间定制新品种,只是要加收10万美元的育种费。这些小白鼠进入全美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和课堂,因为这些实验室都从国家财政中得到拨款,因此可以说,小白鼠已经成了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的一部分。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明人对动物的感情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老鼠因为传播疾病和样子丑陋几乎人人喊打,而经过无菌环境培育的小白鼠有着粉红的爪子和温顺的脾气,还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贡献。哈尔·赫尔佐格说,小白鼠和一般意义上的老鼠已经成了两种动物。但这种界限也并非时时清晰,一旦小白鼠的脚接触到笼子外的地面,它就成了邪恶的老鼠,人们对它的看法也会立即改变。曼联球迷为朴智星写过一首歌:“你们国家吃狗肉?那也没关系,总比吃老鼠的利物浦队员好。”不少时候,英国人可以暂时把吃狗肉的事情放一边,但是老鼠?一定要是实验室外面的那种。这也印证了哈尔·赫尔佐格的判断,人们在遇到和动物有关的问题时,情感会凌驾于理智之上。 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