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困境和未来的诺贝尔奖
作者:陆晶靖(文 / 陆晶靖)
 ( 4月16日,一位中国书法家根据观众的名字创作汉字书法作品 )
( 4月16日,一位中国书法家根据观众的名字创作汉字书法作品 )
今年的伦敦书展开了,许多英国的出版商们很高兴。就因为主宾国是中国,不同的研究者和出版商就兴奋地说,中国是个大市场,中国人有钱有野心,最乐观的是中国人极其爱看书,不止一个人提到他们去王府井和西单图书大厦,人多得挤都挤不进去。书架上的书都是两年内出版的,3年以上的书大部分都要下架。4月15日在伦敦,中英出版传媒产业投资论坛上洋溢着非常乐观的情绪。会议厅在议会大厦对面,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大本钟,仔细一点还能看见丘吉尔塑像的背影。塑像下面有些人在抗议,说美国和英国不应该对全球霸权这么迷恋。
伦敦书展始于1971年,由英国工业与贸易博览会公司创办,1985年起由英国励展博览集团主办。每年一届,是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世界第二大国际图书版权交易会,又因为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出版商们没人敢小看它的影响力。展厅在伦敦西部的伯爵宫,离西敏寺和海德公园都不远。今年中国代表团组成了一支大军,短短3天的展会来了近千人的代表团,在展厅的中央包下了2000多平方米的场地,据说总共安排了300多场活动。这阵势大大超过去年的主宾国俄罗斯,今年俄罗斯的展台算是大的,大约七八十平方米,德国的展台也有五六十平方米,最小的展台可能来自伊拉克,四五平方米的展台有几个书架的阿拉伯语书,放不下的在地上铺着。展会分两个厅,一号厅集中了哈珀·科林斯、兰登书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阿歇特和西蒙·舒斯特等著名出版社,非英语语种和数字展区则集中在二号厅。因为中国是主宾国,所以在二号厅的中央位置到处可见汉字。
在书展前半年,英国媒体就开始关注中国在伦敦书展中的主宾国身份。《卫报》承认英国对当代中国文学所知甚少,于是开辟了专门的版面把毕飞宇、阿乙等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在书展期间,伦敦希思罗机场和市区的数家连锁书店也出现了中国图书展销专架。伦敦大学的朱莉娅·洛弗尔教授中国文学史,也翻译过鲁迅的小说、张爱玲《色·戒》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她说要让英国人花更多时间来关注中国人的写作绝非易事,英语在世界出版业里占有绝对的强势,每年在英语国家的所有出版物中,所有翻译作品只占到可怜的2%。在这热闹的书展里,中国迫切要做的只是让汉语的份额在这2%里尽量大一些。《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带着他的《路灯》杂志来到伦敦,这是一本英文文学杂志,也可以看成是《人民文学》杂志的海外版,选载了中国最主流作家的一些短篇作品的英文翻译,每本定价8英镑。这不便宜,英国本地的《智识生活》一本才5英镑。《路灯》为伦敦书展专门做的一期特刊登了铁凝、阿来、冯唐、徐则臣、刘慈欣等13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和韩东、翟永明等诗人的作品。首发式在一号厅二楼一间会议室里进行,因为位置偏僻又语言不通,莫言、阿来和刘震云在大厅里转悠了40多分钟才找对地方。李敬泽说,中国的出版市场如此之大,对中文写作感兴趣的英国读者想要找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无异于大海捞针,《路灯》的意义就在于引导外国读者最快接触到中文写作的优秀作品。不过,这份杂志如何推广自己,如何建立便捷的购买渠道,李敬泽说,他还没有想。
绝大部分的英国读者甚至是出版人对中国乃至汉语写作还处于非常陌生的地步,即使是莫言、余华这样成名已久并且早有英译本的作家,一本书在经过几次重印之后也只能达到1万本左右的销量。更多的作家虽然有了英译本,并且这些译本无论翻译质量还是书的装帧都很精美,但因为出版方规模不大,译本的销售利润也很低,无法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淹没在书的洪流里。因此尽管中国作家们在书展的各个会议室谈论乡村和城市、网络写作、女性写作乃至文学杂志的未来,用英语问出的问题许多还都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你们的写作和政治是什么关系?事实证明,如果有好的推广和译介渠道,英国人也很乐意阅读汉语文学作品。毕飞宇可能是这次伦敦书展最受英国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去年他的《玉米》译本(英文名为《三姐妹》)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个奖的赞助商也赞助英国布克奖,主要以英文译本来评判当年的亚洲文学最佳作品。书展三天,每天都有一位“当日作家”来做讲座,毕飞宇是唯一的中国人,许多英国读者甚至在讲座结束后排起长队买书找他签名。
在刘震云看来,如果诺贝尔奖用汉语来评,很多中国作家都能得奖。这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我们总还是会不断听见类似“民族的”和“世界的”这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参加书展的中国作家对此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铁凝说,一个作家如果总是在考虑如何写出所谓“世界的”文学,这是一种做作。毕飞宇则觉得这个问题显得自卑而扭曲,似乎世界化成了写作的一种义务。他曾经与很多青年作家聊天,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抓住自己的区域文化来写,这样的小说他都很难喜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是个抒情句子,什么也没有表达。一个好的作家只需要写他喜欢的东西、他关注的东西,那个“像烟瘾一样吸引你的东西,离开它你就不舒服。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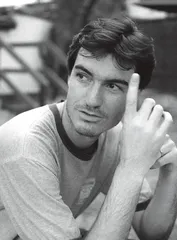 ( 埃里克·亚伯拉罕森 )
( 埃里克·亚伯拉罕森 )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在书展的不同场合被问起,所有的答案都无法让人满意,可以预计的是,追问还将持续下去。因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全世界都迫切地想了解这个国家,人们阅读报纸、访问网页,越来越多的人也来到这个国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甚至有人知道中国社会集中了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一切特征——然而这样仍然难以了解中国,因为通过这些途径无法了解中国人的情感。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学又迫切希望被世界所了解,已经成名的许多作家出生于60年代甚至更早,他们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向世界发出声音,他们必须依赖译者。《路灯》杂志的英文编辑、翻译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说,全世界在从事把汉语作品翻译成英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加起来只有30人左右,翻译类似《蛙》这样的长篇小说,至少也需要半年时间,按照这个速度,每年翻成英语的汉语文学数量就非常有限。伦敦书展期间,铁凝的代表作之一《大浴女》终于在英文世界找到了归宿,哈珀·科林斯和西蒙·舒斯特分别买走了英国和美国的版权,这时距《大浴女》的法文版已经过去了10年。
在一个名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出版”的研讨会上,朱莉娅·洛弗尔说,汉语写作里的短篇小说更容易得到研究者和翻译家的关注。同样发言的还有英国主流文学杂志《Granta》的编辑艾拉·阿尔弗雷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的文学经纪人玛瑞莎,苏童、严歌苓和韩寒都与她合作。在许多英国研究者的视野里,中国的生活充满了碎片化和断裂的体验,短篇小说无论在写作还是阅读节奏上都契合这种社会现实,而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宏大叙事的野心则很容易让英国读者感到厌烦。场内坐着的基本都是英国人,朱莉娅遗憾地说中国许多作家从事几份工作,只在周末写作,依然年年出书,而像朱里安·巴恩斯这样的大作家两年之内别的什么也不干,才写出一本薄薄的《终结的意义》。玛瑞莎好像没听见,滔滔不绝地向在场的英国读者和出版商介绍韩寒在中国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误解总是存在,李洱在一个会上抱怨,西方研究者和译者倾向于选择对他们来说具有夸张效果和样本意义的小说,而许多中国作家又喜欢迎合这种趣味来写作。对于绝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文学是了解中国的渠道,可是参加书展的大部分中国作家都不喜欢这样的看法,刘震云说小说是情感的记录,这个情感超越了语言的界限,如果打算透过小说来看中国的现实,那就离文学很远了。事实也是如此,在伦敦书展上,对“中国”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文学”的关注,这种关注让作家们又爱又恨。《人民文学》的编辑、作家徐则臣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日语等几种语言,他遗憾地说,虽然这些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在西方读者中,猎奇心态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这不是一个好的对待文学的态度。
伦敦书展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意义是不同的,铁凝把自己的代表作卖给了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出版社;莫言见到了写《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柳薇卡;毕飞宇对英国读者说,在作家内心的激情面前,外在限制根本不值一提;阿乙见到了自己的译者,承诺以后写出的东西第一时间就发给她看;而徐则臣在伦敦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的几个分店里,没有找到一本中国作家的书。在另外一家水石书店里,本刊记者看见一个桌子上面放了很多书,还专门立了一个“China”的牌子,走近细看,不同国家的作者用英文在谈论中国经济和他们恐惧中国的理由,甚至还有一本齐泽克论毛泽东思想,但同样没有一本来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喧嚣的谈论,中国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出版商都在关注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虽然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总体上却还是很微弱。但有些英国人却意外地有信心。朱莉娅·洛弗尔说,日本文学也曾经在西方默默无闻,但经过作家和翻译家们的长期努力,日本文学已经在英语世界生根发芽,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甚至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也许中国文学在海外也会有同样美好的未来吧。
“如果中国能有一个马尔克斯”
美国翻译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从2001年来到中国,写过教材,当过记者,翻译过王小波的作品,编辑过《人民文学》的英文版,还给《纽约时报》的网站写专栏。他组建了一个叫“翻艺”的公司,忙于中英出版界在文学上的对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读的第一本汉语文学作品是什么?
亚伯拉罕森:是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那时候我的汉语水平还不高,但是这本书非常吸引我,于是我尝试着翻译,但那个译本不太令人满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作家们的写作水平和英美一流作家相比有多大的差距?
亚伯拉罕森:我个人感觉在技巧上还存在一些差距,大部分中国作家几乎从来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而在美国,专门的写作课程非常多,内容也很成熟。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对这种写作班非常不屑,觉得这种课程会带来一身工匠气,但这种写作班至少能够告诉你,如果你的小说写到3/4时崩溃,你该怎么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会被教坏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英美读者来说,中国文学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亚伯拉罕森:现在英语世界里关于中国的新闻越来越多,很多人会因此对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感兴趣,但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应该从哪里看起和看什么。哈金和李翊云有一些读者,他们可以用英语写作和中国有关的事情,可是他们不住在中国,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好的文学翻译有多重要?
亚伯拉罕森: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是在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的译本之后开始写作的,光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翻译的重要性了。中国许多出版社给译者的稿费低得难以置信,又要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简直是笑话。很多作家都对美国文学非常了解,他们中有人问我,为什么最近50年美国文学几乎没有出什么有分量的作品,我很奇怪,就找来译本和原文对照,这才发现是因为很多书的翻译都难以令人满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翻译的过程吗?
亚伯拉罕森:“磨。”翻译是一个非常缓慢又辛苦的过程,译者需要不断地和作者联系,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不管多么细小,也要问清楚。第一稿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还要对照原文至少修改一次,总之这是一个很琐碎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汉学家顾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其质量不高的根源之一是作家们几乎都不懂外语。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亚伯拉罕森:中国作家的整体外语水平确实不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了解世界文学,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作家对于世界文学的熟悉程度要超过他们在国外的同行。他们都读了大量的翻译作品,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但外语水平确实对他们造成了影响。比如他们在美国宣传的时候,读者就会觉得有个翻译很别扭,在他们的世界里,作家们都是会说英语的。这些作家们也因此丧失了在广播和电视节目里宣传的机会,没有一个电视台会在节目里加一个口译的。另外,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对谈也变得困难,这本来是极好的互相交流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有些人会对诺贝尔奖产生误解,去抱怨翻译。
亚伯拉罕森:我们就被当成替罪羊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翻译经验里,存在着“不可译”的东西吗?
亚伯拉罕森: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小岛上,有个奇怪的国王,不知为何他特别憎恶字母“O”,于是下令全国人都禁止说和写所有带字母“O”的词。我想这个故事应该是不可译的,在中文里你可以说所有“草”字头的字都不许用了,但“O”是个元音字母,会影响到日常的发音,而“草”字头就不会。有些语言障碍实在难以翻越,还好这种把整个文本都建立在语言现象上的小说特别少。
三联生活周刊:你经常把中国作家介绍给英国出版界,对于他们来说,海外版权意味着什么?
亚伯拉罕森: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可能想这样就能发财了,但一般来说销售情况都不会很好,能卖掉5000本就很了不起了。出版社卖中国作家的书时,都没什么把握。我经常和“企鹅”还有兰登书屋的编辑说某一本小说如何如何好,可是他们回到公司还是要看销售部门的脸色。现在海外版权对于多数作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成就感的来源吧,我感觉中国文学界还是比较沉闷,作家们急需得到外界的承认。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出版社怎样到中国市场挑选图书?
亚伯拉罕森:“企鹅”已在北京建立了办公室。许多其他的出版社则比较迷茫,他们很难确定在中国那些得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最好的,同时也无法从书店销售榜上得到什么信息,那些榜单基本都是垃圾。我经常给他们推荐书,可是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我。这很正常,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出版市场,最好是建立起多个相对可靠的渠道,一两个人的意见是难以服人的。
三联生活周刊:距离英美大规模拥抱中国文学还有多久?
亚伯拉罕森: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作家还需要继续努力。只有当中国文学在英美市场上有足够的译本时,才谈得上形成热潮。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有一个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那么几乎不需要宣传,英美读者也会自动来关注中国文学。 读书文学作家人民文学出去翻译专业艺术未来诺贝尔奖困境三联生活周刊翻译文学语言翻译中国文学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