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伦理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 《为什么要孩子?伦理辩论》 )
( 《为什么要孩子?伦理辩论》 )
人没有生孩子的义务
《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考伯特说,美国医生查尔斯·诺顿是“人有不生育子女的权利”这一观念的先驱。1832年,诺顿出了一本很薄的书,书名却很长——《哲学的果实:一位医生给年轻已婚夫妇的私下指南》。31岁的诺顿是一个特别爱冒险的人。在医学院就读时,因为太穷上不起解剖课,他从墓地偷了一具尸体,因此被指控为盗墓贼,被监禁60天。182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他的不可知论思想,自费印了1000册带到纽约去卖,结果因为无证行商而被捕。在《哲学的果实》中,诺顿讨论的是人口增长问题。跟托马斯·马尔萨斯一样,诺顿担心繁殖会造成危险。他用19世纪的生育率预计,地球上的人口每一个世纪会翻三番。马尔萨斯认为除了瘟疫或禁欲,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诺顿则认为有一些更能令人接受的办法。他在书中向读者提供了海绵、注射药物等避孕方法。《哲学的果实》一书又让诺顿吃了官司。第一版出版后不久,他被指控出版淫秽读物,被罚款50美元。审判还没结束,他又受到新的指控。这一次,诺顿被判了3个月的劳改。部分是因为诺顿惹上了官司,他的《哲学的果实》火爆了起来,20年间在美国出了9版。该书也在英国出版了,40年间每年卖掉大约1000册。《哲学的果实》被认为改变了历史。就在这本书刚面世之时,美国的生育率开始下降。诺顿的书对传播“性与生育可以分开来”这一消息起了一定作用。换言之,对于是不是要孩子,人们可以加以选择。
在《为什么要孩子?伦理辩论》一书中,加拿大女哲学家克里斯廷·奥弗奥尔对是否要孩子的决定做了严格的道德分析。她认为,生孩子并非自然而然、不需要理由的问题。我们的很多生理冲动都需要去选择是否遵从它们,如果想要孩子,我们也应该给出理由。人们给过了很多理由,奥弗奥尔一一做了反驳。比如,说生孩子会给孩子带来好处,这好像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采取避孕措施,孩子不被生下来,他就失去了一切,享受不到生命的乐趣,如吃冰淇淋、骑车等。对此,奥弗奥尔提出了两点反驳:首先,没被生下来的人没有任何道德感,有无数没被生下来的人,你没听到过他们的抱怨;其次,如果说生孩子能够提供世界上的幸福总量,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父母们生的孩子越多越好,但结果世界上的人口太多,到最后每个人的幸福会几乎为零。这一论证是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最早提出来的。如果一个孩子吃冰淇淋代表一份幸福,两个孩子吃冰淇淋代表两份幸福,4个孩子吃冰淇淋代表4份幸福,有8个孩子的家庭的经济能力使得他们吃冰淇淋的次数只是有4个孩子的家庭的一半。
奥弗奥尔发现,大部分其他要孩子的理由从哲学上来说也不够充分。有人说,为了家族的延续或基因的传递要生孩子。奥弗奥尔问:“谁的生物学成分重要到必须延续下去的地步了?”有人说,公民有义务维持群体的延续。奥弗奥尔说,这种义务会把女性变成生育的奴隶。还有人说,人们应该生孩子,这样老了才有人照顾自己。奥弗奥尔说:“所有为了养老而生孩子的人也许都上当了。”
奥弗奥尔说,决定是否生育是一个道德决定,因为它会影响到很多人,不只是未来的父母,还有未来的孩子,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社区成员。通过生孩子来增强自信、挽救婚姻或满足长辈的期望都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相反,如果一个人出于自私决定不生孩子,这一决定并不算坏。它对当事人之外的人没有多少影响,除了有时会感到不快的本可以做祖父母的人。她特别反对的是把生孩子说成对国家或群体的义务。是否生孩子应该由个人自主决定,不然就是把人的身体当做实现生育目的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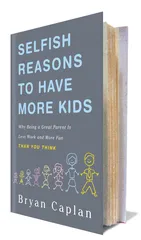 ( 《要更多孩子的自私的理由:为何做伟大的父母比你以为的干得要少、乐趣更多》 )
( 《要更多孩子的自私的理由:为何做伟大的父母比你以为的干得要少、乐趣更多》 )
奥弗奥尔自己有两个孩子,她在书的结尾描述了抚养孩子和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给她带来的满足。她认识到,人口限制论往往是厌恶女人的。“最好没被生下来这种观念的含义是,女性怀孕、生产、哺乳和抚养孩子的努力给地球带来的是总苦难的累积。”但人口限制论并不是当今的主流,认为应该尽可能地拥有孩子的观念还很强大。奥弗奥尔的书是一个受欢迎的解毒剂。她写道:“孩子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生育孩子也不是成为好人所必需的。再者,有很多没有子女的人支持、喜爱、照看和教育别人的孩子。”
生三个孩子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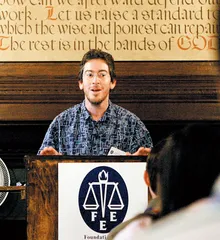 ( 布赖恩·卡普兰 )
( 布赖恩·卡普兰 )
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戴维·博纳塔也用哲学来确定理想的家庭规模。他在《最好没降生到人世间:成为人的害处》一书中说,假如有甲、乙两对夫妇,甲年轻、健康、富裕,如果他们生了孩子,什么都给孩子最好的——学校、衣服、电子游戏设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说甲有生孩子的道德义务。乙也年轻又富裕,但夫妇二人都有遗传性疾病,如果他们一起生孩子,孩子会遭罪。我们会说,乙有不生孩子的道德义务。甲、乙的情况表明,我们对享乐和遭罪有不同的态度。没被生下来的人没有享受到幸福不算受到损失。但避免苦难却是好事,哪怕被遭罪的人不存在。对甲、乙有效的对所有人都有效。所有人的人生都包含享受与苦难。如果没被生下来的人放弃享乐,没人受到损失。但如果带来不必要的苦难,世界就变得更糟了。博纳塔说:“我的论证的含义之一是,充满了好事但也包含一点坏事的人生比没有被生下来更糟糕。”按照博纳塔的逻辑,如果所有人都认为生孩子是造就苦难从而不再要孩子,不到100年后全世界的人口就会降到零。在博纳塔看来,我们应该期望这样的结果。“人类的特点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和危害性的物种。如果没有人,世界上的苦难数量就会急剧减少。”
博纳塔的虚无主义令人觉得不能坐视不管。既然应该希望人类有朝一日灭绝,博纳塔是否计划自杀呢?他没有说,但他区分了出生和继续活下去。最好不要被生下来,但一旦我们来到人间,就应该继续活下去。你活着就有可能享受到乐趣,开枪自杀会很不愉快。他的“苦乐不对称”论证并不可靠,因为对于苦乐都有的人生来说,乐可以弥补苦的不足。博纳塔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的乐,以及极地探险、写一首好歌、恋爱和观看新生儿漂亮的脸蛋这样更大的乐趣。
 ( 克里斯廷·奥弗奥尔 )
( 克里斯廷·奥弗奥尔 )
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写了一部《要更多孩子的自私理由:为何做伟大的父母比你以为的干得要少、乐趣更多》的书。卡普兰认为,年轻夫妇应该从长计议,不仅要考虑现在他们想要几个孩子,还要考虑他们年老、孤单时希望身边会有几个孩子。“假定你是30岁。自私点说,你认为30到40岁之间最好只有一个孩子。40多岁时,你希望最好拥有两个孩子,因为孩子独立后你的空闲时间更多。到你50岁时,你的孩子都会忙自己的事情。这时,有4个孩子定期来探望你岂非很好?最后,一旦你过了60岁,准备要退休了,你有很多空闲时间跟孙辈待在一起。有5个孩子能保证你不会没有孙辈。”经过计算,卡普兰认为,最好生3个孩子。孩子小时候很烦,当父母努力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时,也是孩子最需要照顾的时候。结果很多人还没有生够3个孩子就不再生育了,“很有远见的父母比中等远见的父母希望要更多孩子”。
卡普兰说,可能有人会因为没有时间和资源去养更多的孩子感到遗憾。让一两个孩子过上体面的生活不比让三四个孩子过得潦倒更好吗?卡普兰说,不用担心,他引证了许多对双胞胎和收养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对于孩子的健康、智商乃至入狱的概率来说,先天因素的影响远超后天的养育。不必盯着孩子吃多少炸薯条,带他们去上音乐课,或教导他们要守法,只要不把他们锁在衣橱里,他们就会没事。父母们意识到下多大的力气教育孩子没多大影响,就会省下很多力气。这样会降低生育成本,从而提高生孩子的吸引力。“如果孩子是商品,消费者的逻辑依然适用:更划算的话就多买一些。”至少多生孩子还能提供更多消费者和劳动力。 伦理生育诺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