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中国味的美国梦
作者:石鸣(文 / 石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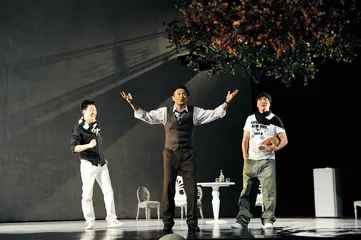 ( 《推销员之死》剧照 )
( 《推销员之死》剧照 )
此次人艺《推销员之死》上演之际,纽约百老汇也正在演出新一版的《推销员之死》。百老汇的这一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舞台完全复古,1949年首演时的舞台设计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用,与阿瑟·米勒原剧本中的指示完全一致:“面对我们的是推销员的屋子。我们意识到屋子后面以及四周密密层层的都是高耸入云、有棱有角的大楼轮廓。只有天际泛出的蓝色清辉洒落在屋子和前台上,周围地区呈现出一种橙红的炽热灯光。随着灯光越来越强烈,我们看到一排公寓房子那结构坚实的拱顶围着这幢外表脆弱的小屋……厨房里有一张炊桌,三把椅子和一只冰箱。可是看不到别的厨房用具。厨房后面是门口,挂着门帘,通起居室。厨房右边,高出舞台平面两英尺的是间卧室,家具只有一张铜床和一把靠背椅。床头上方一个隔板上搁着一个体育比赛的银质奖杯。一扇窗子正好朝着公寓房子的侧面……”
这也基本描述了1983年“人艺”上演《推销员之死》时舞台的样子。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在舞台上“复制”美国梦。当年在阿瑟·米勒的指导下,人艺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对布景和灯光做了种种校正以求逼真。事实上,在剧本完成之际,并没有这么详细的舞台指示,阿瑟·米勒不过将舞台想象成三个简单的黑色平台,以完成场景在不同时空间的顺畅转换。然而,舞台设计师乔·梅尔齐纳(Jo Mielziner)为这个剧做了堪称美国戏剧史上“标志性”的布景设计,并附上了一份设计说明。阿瑟·米勒对他的设计极为满意,据此重新撰写了剧本中的舞台指示,细化到规定了洛曼家的厨房用具应该是什么牌子,还修改了一些表演动作。
“什么样的舞台奠定什么样的表演气氛。”人艺新版《推销员之死》的导演兼舞美李六乙说。这一次排这个戏,他完全摒弃了阿瑟·米勒原作中详尽的指示,采用了“空”的舞台:一堵高耸至屋顶的水泥墙将舞台斜向分割成明暗两片,所有表演都在明亮这一半完成。道具不过是一张桌子和散落的几把椅子,原本属于厨房的冰箱被远远地置于舞台深处。用上了剧院里所有能用上的灯,打出的光线方向专注,色彩单纯,不过红、蓝、白几色,将镂空的家具投影到墙上,加上演员的移动,在斜墙上形成了另一场戏中戏。乐池处被布置成前台,放满了巨大的白色圆球,左前方白球让出空间,放了一把木制花园长椅。“我们把所有能扔掉的外部手段都尽量扔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演最大化,好的表演可以在舞台上创造一切。”李六乙说,他不否认中国戏曲的舞台美学给他的启示,“一桌二椅,变幻无穷,随时交叉共存,这是戏剧的蒙太奇,让观众来剪辑这个空间,比电影蒙太奇更加要求想象力。”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戏剧史上第一部大量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做戏的作品。“我们今天是如此熟悉一个戏中某个人物在心理层面上时空来回跳跃的戏剧手法,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剧本当初的巨大贡献。”《纽约客》评论道。阿瑟·米勒写作这部戏缘于他与一个远亲的邂逅,那是1947年,他刚刚因《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一剧在百老汇崭露头角,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他在剧院外碰见了10多年未曾谋面的“曼尼叔叔”,其职业正是个推销员。他刚想寒暄几句,曼尼叔叔却谈论起自己的儿子、米勒的堂兄弟的现状。“我突然被击中了,这个人好像同一时刻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米勒回忆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他心里,我和他的儿子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和比较,跟30年前一模一样。原来人的大脑能够如此运行在两条完全不同的时空轨道之上。”
于是,剧本就在这一点上架构起来了。主角威利·洛曼可以一边和邻居查理打牌,一边和25年前就已死去的某人对话。“在《推销员之死》中,现在时中充满了过去时。这些手法有时被误称为‘闪回’,但其实这部剧中并不存在闪回,而是过去和现在的‘共存’。这是不同的。”阿瑟·米勒在200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按照他的说法,《推销员之死》就是对“时空共存性”的一次集中展演,“试图用刀切出一个时间流逝的横截面”。
 ( 《推销员之死》剧照 )
( 《推销员之死》剧照 )
这种“时空共存性”给导演在舞台表现上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最多的时候有5个空间共存,首先要同时将这5个空间在舞台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找到每一个空间的表现方法。5个空间,有不同的态度,从而有不同的节奏,带来了不同的内容和变化,最后还原到真实的那一个层面。”导演李六乙说,“这要求在写实和抽象的边界进出得自由,和自由之后准确的表现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你第一次做一个戏的舞美设计,这次的舞台也非常特别,你一定有特别明确的表达意图?
李六乙:不知你有没有注意那面墙,其实是一边白色,一边黑色,舞台也因此被分成了黑白两个颜色。第一幕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白色的,而第二幕又回到家里之后,所有的家具都变成黑色的了,冰箱也变成黑色。这是试图通过对色彩的感觉传达出一种戏剧的概念。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这个戏当然是要中国味道,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戏剧?这个戏,我觉得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谈谈那把红椅子吗?它一直在那里。
李六乙:整个戏我都是选择非常单纯的颜色。红色或许会给观众很多不同的联想,这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去确认。而那把红色椅子永远有个空间在那儿,随时有人进去打破它,随时又可以变成空间的一部分。有人说,研究李六乙的导演就是要研究他的椅子。餐馆那一场戏,不需要有人,其实每一个椅子上都是有人的,椅子的不同方向,也就是确定了人的不同方向,位置、方向变了,可能态度就变了。这个戏没有花里胡哨的导演的痕迹和处理,但是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戏尽管中国味儿非常浓,但是还是保留了很多美国元素,比如第一幕的收尾是美国国歌,第二幕全家人去看球赛时每人拿着一面美国国旗,这样一来,观众情感进入的同时也时时被提醒着保持距离,你似乎在有意追寻一种“间离”的效果。
李六乙:实际上这种间离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是那样的开场?5分钟的舞台调度,大提琴的声音,从拨弦到混乱,甚至到呐喊,又回到一个极其孤独的状态,便走出了主角威利一生的历程。你再看我的说明书,多间离,很多人没发现,特失败,这是国贸,中国吧?反过来一看,多纽约啊,曼哈顿的夜景。我挑的这两幅图。还有音乐,其实全剧的配乐暗合了美国音乐史发展的一条线索,从爵士到摇滚,我个人觉得这些音乐很符合阿瑟·米勒的思想,音乐的这些变化和美国人的生存状态是非常紧密结合的,暗合了所谓的美国精神。排练时我还希望演员去了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诗歌,要毁灭、要反叛、要呐喊,这和阿瑟·米勒的精神气质很契合。美国国歌的使用,可以正面理解,也可以反面理解。但是服装上完全没有美国元素。其实所谓美国梦、美国元素,并不是要还原到美国某个具体的时空,阿瑟·米勒的“美国梦”经过蔓延之后,已经不局限在美国了,但是这种提示仍然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舞台前台那些白色的球,非常具有象征意味。你认为它们有什么含义?根据原剧本,那里应该是威利·洛曼家的后院,他种菜时去的地方,也是威利的心理空间,他陷入回忆的地方。
李六乙:那个地方是威利独有的一个栖息地,很干净、很童话的一个地方。白球一放,很超现实,空间立刻可以在抽象和写实之间来回变换。威利为什么要种地?那是他希望的一种美好,这个是阿瑟·米勒的解释。过去剧评家还有一种解释,种地是一种希望。总之那是一片净土,只有威利可以到那里,琳达曾经在最后下去过一次,其他人没下去。其实威利心灵当中有很多很纯洁的东西。查理有句台词,你什么时候才长大,你怎么老长不大。其实这句台词给我的印象蛮深的。那个白色的球,你可以说它是永远飞不起来的气球,那个理想是永远飞不起来的。也有人说是泡沫。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能有一点美好,有点童话。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很多舞台处理非常大胆,比如第二幕中,两个儿子从酒馆回来给母亲送玫瑰花,剧本里说是一束玫瑰花,你的舞台上就只有一支。
李六乙:其实那个舞台,别看那么大、那么空,有一个小细节就足以散发魅力。设想一下,一束花,就显得没有一枝玫瑰有力量。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舞台,像这种舞台我就特别地惜墨如金,特别在意一点点东西,因为它很珍贵。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争论威利·洛曼到底是一个悲剧英雄,还是一个可悲的小人物,你对此怎么看?
李六乙:首先我不觉得这个人物的生活是特别悲的。他应该是非常阳光充满希望,不应该有半句悲腔,半句自我怜悯。当年阿瑟·米勒来排的时候,英若诚给他介绍阿Q,他就觉得威利特阿Q,阿Q从来不觉得自己很悲,他和吴妈碰了一下之后就已经产生了幻觉,他已经觉得和女人在一起了,很幸福了。其实威利是应该对生活充满着幸福感,我觉得这样更具悲剧性。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不是琳达早年总是纵容威利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威利也不至于一直沉湎于幻想之中而不自知吧?
李六乙:其实不仅是威利,琳达也有美国梦,威利的梦的存在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琳达给他的。威利有相当的因素是要去实现琳达的梦想。所以这不单纯是一种呵护,两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两个儿子也都有梦想。哈皮是又一个威利,他会在他父亲不在的时候说他父亲会说的话,他不可能挣脱这个父子循环。而比夫则是另一个自我的悖论,他希望一种田园的生活,要卖力气,要阳光,要光着膀子干活儿,这好像是一种很自在的生活。但是,人永远脱不掉孤独。这是阿瑟·米勒的,他解释不了。人会觉得孤独,会觉得寂寞,一生就和6匹马待在一起,觉得不对,却也改变不了。没人能真的去“桃花源”。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你排这个戏想表达的主题,你会怎么说?
李六乙:其实我倒觉得是推销员为什么死,推销员怎么死的,让他推销的是什么?
这个非常有意思。推销员推销的到底是什么?深入到阿瑟·米勒的剧本里,这个应该是让所有观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这才是这个戏的根,真正的魂。我从阿瑟·米勒的剧本里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个戏现在放在中国这么演,比29年前更合适。这里面有一个对待生命的态度的问题,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到底如何评判,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说这个戏让我还有一点冲动的话,就是这一点。
(感谢实习生孙若茜协助整理采访录音) 李六乙推销员美国推销员之死之死人艺中国美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