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林为何重要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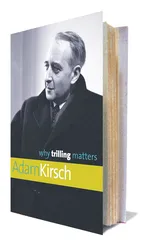 ( 亚当·柯什所著《特里林为何重要》 )
( 亚当·柯什所著《特里林为何重要》 )
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美国《新论衡》杂志评论说:“对于一部关于特里林的书来说,《特里林为何重要》是一个很奇怪的、辩护性的书名。”特里林的重要性曾经是不言而喻的:他是纽约知识分子圈中的一位明星,其主要论文集《自由的想象》自1950年出版以来,一共出过六个版本,其平装版卖了十多万册。”
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一生中撰写了一百多篇关于各种主题的论说:论奥斯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济慈和艾略特,吉普林和亨利·詹姆斯,卡夫卡和弗洛伊德,这充分表明了他对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感知力。他不仅评论文学,还涉及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做了大量思想史研究。他关于马修·阿诺德的论著提到了许多通常不会被认为跟阿诺德有关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等等。他后期的著作同样广博:讨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思考现代性状况下道德生活的复杂性。除了关于华兹华斯的论文之外,特里林的论文都不是对文本的逐字逐句分析。他感兴趣的是抽象的大词:心灵、自我、现实、意愿、快感、天才、真诚、真实。他用文学评估读者头脑中这些概念的状态。特里林认为,人们的文学喜好表明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表明他们的道德和政治观念。
柯什认为,特里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致力于把他的自由主义者同道从各种形式的没有想象力的、教条的意识形态中拯救出来。在特里林看来,各派自由主义共同具有的信念是,人类的改进是可能的,有一条通往健康和幸福的笔直的大道。自由主义者相信,恰当的经济制度、恰当的政治改革、恰当的本科生课堂和恰当的心理治疗将消除不公正、势利、怨恨、歧视、神经病和悲剧。而文学告诉我们,生活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公正、势利、怨恨、歧视、神经病和悲剧恰恰是文学的主题。他在《自由的想象》的序言中写道:“一直以来,我觉得那种以自由主义利益作为核心的批评应该发现,它最有用的工作并非在于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在于对当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观点施加一定的压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充斥着极为兴盛的进步主义思潮,特里林对此展开论战。天真令他感到厌烦,纯洁遭到他的拒绝,神圣超越了他的接受范围,他信仰的真理就是复杂性:“对于自由想象的批评的开展,文学有着独特的相关性。因为文学是最充分、最准确地描述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人类活动。”特里林在论文中坚持以赛亚·伯林阐述的多元主义。他从亨利·詹姆斯那里学到,所有的善不能同时实现。特里林相信,保存人类的差异、以同样的同情心想象对立的性格的能力是对爱情最伟大的表述。他践行了他所倡导的多元主义。特里林认为,他的学生金斯堡的诗《嚎叫》不但不令人感到震撼,而且很沉闷,但他仍然支持和鼓励金斯堡。
193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特里林撰写了一篇评论,说这本书很荒唐。但约这篇书评的杂志《新自由人》倒闭了,这篇评论一直没发表过。1950年之后,他开始迷恋《文明及其不满》,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这一概念,它指的是对人类会变得更好这一观念先天的、生物性的抵制。这一概念被用于推翻马尔库塞等人的主张,他们认为,正确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能够消除不满及神经病。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说,弗洛伊德的论证就像“一头雄踞的狮子,挡住了通过激进地修正社会生活实现幸福的一切希望。”
 ( 特里林 )
( 特里林 )
自由与保守、革命与反动
1964年,在《自由的想象》新版序言中,特里林说,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唯一占主导地位,而且是唯一的知性传统,没有广泛存在的保守主义观念。美国虽然没有保守观念,但有很强的保守主义冲动。对于保守主义观念,要去英国寻找。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鼓励他的自由主义同道去了解柯勒律治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心智,以纠正自由主义的弱点与洋洋自得。密尔虽然不同意柯勒律治的政治学与形而上学思想,但他认为它们很重要,因为它们能让自由主义者意识到对知性和政治很必要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或者他的另一种表述,复杂性、模糊性、偶然性、悖论、反讽,这些词语贯穿于特里林的全部作品。它们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非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想象的特征。
在1950年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特里林把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延伸到了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几乎所有趋势,写出了关于斯诺与列维斯的两种文化辩论、巴别尔和乔伊斯书信的重要论文。但有人批评他完全放弃了自由主义。约瑟夫·弗兰克1956年评论说:“现在他感到他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保卫自由,而是保卫承认必然性这一品德。特里林从一个自由想象的评论家变成了保守主义想象最不好斗但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人。”欧文·克里斯托尔说,特里林是对他的新保守主义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之一。但特里林的夫人戴安娜·特里林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最坚定地认为他不会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之一,他的思想中没有一点支持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分。”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最初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成为政治倾向的标签。它们的意义与用法在党派辩论中发生过变化,但二者之间哲学上的区别在19世纪中期前已经固定了,这主要归功于埃德蒙·伯克。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真正区分他的党派与其对手的不是无神论与信仰,民主制与贵族制,或平等与等级制,而是两种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伯克认为,既然人类降生到一个通过他人才得以成长的世界,社会便先天地先于个人,政治生活的单位是社会而非个人。保守主义保守在他们从伯克的社会观中引申出来的含义,他们总是把社会看作我们继承的、我们要对它负责的东西,我们对那些我们之前和之后的人负有责任,且这些责任优先于我们的权利。
保守主义者还假定,这一承继最佳的传承方式是风俗和传统缓慢的变化,而不是通过政治行动来改变。他们不反对变革,只是反对使用暴力改变既有的观点和建制。哲学上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宗教战争,但它最早成为党派标签是直到19世纪初,西班牙宪政主义者启用的。后来在与保守主义的对立中,自由主义才变成明晰的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密尔赋予个人优先于社会的地位,他们认为,社会其实是由个人的自由建构出来的,不管我们承继到什么样的社会,它们总是由个人的行动重塑的。这一态度使自由主义者怀疑援引风俗或传统的做法,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给特权和不公作辩护。自由主义者跟保守主义者一样,认识到需要做一些约束,但他们认为约束必须源自超越特定社会与风俗的原则,原则是对我们的自由唯一合法的约束。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在于不同的人性论,革命派与反动派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历史观。美国人现在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都认为人生而自由,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自称保守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接受《独立宣言》的表述。但美国现在有一些危险的反动派,他们认为唯一的前进道路是破坏掉历史给予他们的东西并等待新秩序从混乱中出现。马克·里拉说,“认为他们知道通过革命想创造出何种新世界的人就够麻烦的了;那些只知道他们想破坏掉什么的人简直就是祸害了。每当我听到新反动派的言论,我就想到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的耶稣会士纳夫塔,他在瑞士的疗养院的走廊里徘徊,咒骂现代的启蒙运动,寻找信徒。令纳夫塔感到愤怒的是,历史无法逆转,所以他就梦想着报复它。他说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一段残忍的清洗时期,之后人们最初的无知将复归,新的权威被建立起来。托马斯·曼塑造纳夫塔依据的原型不是埃德蒙·伯克或俾斯麦等传统欧洲右派,而是匈牙利哲学家、既憎恨自由主义也憎恨保守主义的乔治·卢卡奇。” 文学文明及其不满特里弗洛伊德重要政治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