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钦思:我只是怕我不能写作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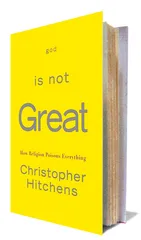 ( 作品《上帝没什么了不起》 )
( 作品《上帝没什么了不起》 )
直到《上帝没什么了不起》出来之前,希钦思还很小众,读他的人深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犀利头脑和磅礴笔力,但圈子之外,书卖得不多。可是只消扫一眼他作为“刺客知识分子”的履历,这种默默无闻就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在他欲加谋害的偶像清单中,赫然列着:甘地、特蕾莎修女、克林顿、基辛格、戴安娜……随便挑个“凶器”:“甘地让犹太人用非暴力来‘融化’希特勒的心,这听上去只是愚蠢,但他还写信给元首,说:‘作为一个没有动用战争而获得了一些成绩的人,我的吁请您愿不愿意听呢?’这就不但显得自负,而且似乎在暗示希特勒借鉴他的方法,更能达到目的。”又如,他称特蕾莎修女不是关心穷人而是热爱贫穷,是独裁者的好朋友,而基辛格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战争犯,克林顿是说谎成瘾的性罪犯。这些本来就意在煽动的棒喝,好像成了希钦思的标签,谈起他就不能免俗地罗列出来。
舞文弄墨者,总是或多或少反感标签的,虽然写过《致一位愤青的信》,教导青年人“异见”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但希钦思自然不认为自己只是个“反调演唱者”,整天四处寻觅挑衅对象。愤怒和尖刻往往都是由爱生恨的故事,他的张牙舞爪、毫不留情,在他看来,是理性、自由、公正,或语言的神圣和美妙,这些他热爱的东西不能容忍任何伤害践踏罢了。他说人们不会谈论他其他的书,比如他的三本专著,讴歌托马斯·杰弗逊、乔治·奥威尔和托马斯·佩恩。
声名鹊起,是希钦思终于找到了让他称心如意的对手:上帝。2007年,无神论者纷纷揭笔杆而起,半打的反宗教书籍出现在了书店的显眼处,一时间风起云涌。《上帝没什么了不起》的副标题是“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意即除了要清算以神圣为名的种种恶行,本身这种毫无条件的臣服就是人类最可鄙可弃的一种品性。他喜欢说:“上帝就是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器,你一出生他就目不转睛盯着你,而真正的好戏,还是你百年之后:这是天上的朝鲜,而在朝鲜,你至少他妈死了总行了吧。”希钦思说人生在世,最好的东西是面对世事时一种反讽的姿态,没有这个,活不下去。
正如他的偶像奥威尔强调的,不要以为你讲的道理重要,就可以牺牲掉艺术上的考量。希钦思的文章,用词考究,句法跌宕,虽然不时见得生趣,但又出乎自然,并无意让每一句都要强作窈窕;他的文气,只觉得作者就牛哄哄坐在桌子对面不动声色地朝你言谈,从容透彻,而其中的韵味节奏,直承莎士比亚、狄更斯、伍德豪斯、拉金这一路英文文脉,推着你向前,停不下来。
希钦思感谢上帝让这本书成了畅销书,《纽约时报》“好卖榜”,第一周就跃居第二,被另一本名著《哈利·波特》压在身下也没什么好说的,但第三周便成了冠军。宣传《上帝没什么了不起》,希钦思像个歌手一样巡回美利坚,每个星期都要和宗教人士辩论。这些辩论,不只安排在“异教横行”的海岸,也有很多是在耶稣“粉丝”甚众的美国腹地,但依然无比叫座。有来给上帝队加油的,有半出柜的无神论者终于找到组织出来过节的,但观众大多知道,光听希钦思说话,看他如何驱策辞句,摆事实讲道理,出口成精致文章,你至少不会想到提前退场。不久前出版的《你不得不引的希钦思》(The Quotable Hitchens),他的钟子期——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挎刀作序,称希钦思为历史上最让对手恐惧的雄辩家之一,不管什么话题,就算对手是西塞罗,是狄摩西尼,他也会把筹码推向希钦思这一侧。麦克尤恩说所有希钦思读过的书,见过的人,听过的事,好像都在他脑中铺展着,随时待命,扑向对手,俘获听众。
 ( 希钦思 )
( 希钦思 )
希钦思的博闻饱读,正如他这些朋友所说,几近无理/礼,听他讲话好比在读维基百科,每一句都有几个链接指向其他页面,他以为别人知道的跟他一样多,结果大家都在暗恨自己光阴虚度,没有知识,只能悻悻然假装点头。但或许对于作家来说,博学是次要的,真正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将任何话题占为己有、涉笔成趣的功力。希钦思不只写政治,也写文学,写世情,写趣味;任何话题,只要是希钦思署的名,那样的文字和见地,模仿起来不容易。
去年6月,他的回忆录《Hitch 22》出版(注:Hitch是朋友所唤希钦思(Hitchens)的诨名,“Hitch 22”戏仿《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是他和至交萨尔曼·拉什迪文字游戏的产品)。上来讲的是一张1979年在巴黎拍的照片:从左到右是希钦思、芬顿、艾米斯;2009年有个“马丁和他的朋友们”的摄影展,这张照片也出现在宣传这个展览的图册中,底下的说明文字:马丁·艾米斯当时任《新政治家》杂志的文学编辑,与他共事的有朱利安·巴恩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思……此老兄是酒精不离手的,把自己最喜欢的饮料“Johnnie Walker”称为“沃克先生的琥珀色提神剂”。
他把“提前的讣告”作为回忆录的开头,希钦思解释:一直觉得写回忆录还为时尚早,但读到自己亡故的消息,明白写回忆录总是“尚早”的,这本书的截稿日期不打招呼、不由分说,“交稿迟了”就不用再交……
然而,没有比这更浓烈更让人唏嘘的一语成谶了。这时希钦思已文名嘹亮,世界百大公知榜居然排到了第五。《Hitch 22》一上架,好比是迪卡普里奥要卖电影,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在纽约站,希钦思被抬进了医院。可视肉身为无物惯了,他不听劝阻又跑了佛罗里达、芝加哥、费城三站,直到再次倒下。食道癌,四期。正如他自己说的,没有第五期这一说。
就在纽约,还不知道患了绝症的他上“每日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出场时的寒暄“How are you?”他总是喜欢回答:“现在还早,不好说。”他母亲从小就教育他,世间最大的恶是无趣,所以希钦思从不会给你陈词滥调,但这次“没什么了不起的上帝”开的玩笑有些过分。希钦思病危消息传开,文坛同悲,最脱口而出又毫无破绽的惋叹便是:“这是何等样的一生呵……”不得不说,此君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活着,如同你明天就会死去”的人物之一。牛津毕业之后,他给舰队街的报刊写写书评,和一众新交旧识过着张扬而温饱的文青生活(他们那个传奇团伙里除了马丁·艾米斯,还有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詹姆斯·芬顿等一堆青年才俊,是70年代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但他天生是写政治的,他开始走出国门报道世界大事,曾从将近60个国家将报道发回伦敦的《每日快报》。如同小说或者影视里那些案发时他总在现场的名侦探。70年代,这个星球上何处有动荡和不幸,希钦思就会偷偷隐现在那个陌生国度的陌生群众之中,直到1981年效仿他所景仰的托马斯·佩恩,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用文字指点江山、动摇国事。
在诊断出癌症之前,有15本书在希钦思的名下,每个星期四处奔波去辩论、演讲之余,还轻描淡写经营着三个专栏。有人常疑惑他每个星期那些信息量巨大且行文考究的绵密长文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名利场》(Vanity Fair)的著名写手、编辑卡特(Graydon Carter)回忆,希钦思有次去他们家做客,前一天刚做了化疗,他们一些朋友吃饭聊天喝酒又晚了,希钦思突然说:“我还要发个专栏。”卡特说:“不用吧,我想他们应该能体谅,你昨天刚……”希钦思扬了扬手,从包里抽出个笔记本电脑,坐到一边敲了半小时键盘,又回到酒桌旁边。卡特说他第二天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去做做化疗。
现在希钦思回答“How are you?”的时候会说:“我快要死了,仅此而已,但你们不也是吗?只不过我现在心里记挂这件事稍微更多一些罢了。”他说他治疗期间有时不能写作,除了孩子们的丧父之痛之外,这一点最让他担心:“因为如果不能写作,恐怕我坚持活下去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在《致一位愤青的信》中他有一句话乍读到如醍醐如惊雷如被踹中小腹,以后也经常想起:“我只能活一次,滚他妈的,可鄙的妥协让步就是一秒钟也不行——有时候这样告诉自己,还挺有用的。”如果允许用一些矫情的辞藻:希钦思是一个打定主意和生命抵死缠绵的人,在烟酒熬夜上面,他绝不退让分毫。抵御癌症挑衅死神期间,希钦思接受采访,问他现在有没有觉得过去生活得太忘我,太压榨自己的身体了(英文里常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为把蜡烛两头一齐点着),希钦思说他自己向来是这样一根蜡烛,这样光芒更曼妙一些。
(希钦思现在正接受一个刚研发的治疗方案,效果未卜。当然对他来说,几个肆虐的晚期癌细胞绝不是偷懒、不看书不写字的理由,近期依然可以不时读到他的专栏文章,看到他演讲和辩论。)■
(文 / 陈以侃) 写作不能只是希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