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放弃了所有的明天,成全了我们的今天”
作者:李菁 ( 1944年,史迪威在缅甸战区 )
( 1944年,史迪威在缅甸战区 )
回家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史迪威家族的代表来参加远征军遗骨安葬仪式,你有什么感受?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我认为这个仪式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中国政府终于把他们的“儿子”迎接回来,让他们终回故土。我最感动的一刻,就是当19个中国士兵的骨灰被捧进国殇墓园的时候。那天碰巧还下起了雨,我想这是上天也落泪了。我知道,这里面有政府的努力,也有许多民间人士的努力。
那天在国殇墓园,我还特地给那里的美军烈士墓献了花。不过准确地讲,那是个纪念碑,因为战后美国政府把那些美军战士的骨灰移到了美国。这也让我们记住战争期间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密切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未来这种互相理解与合作的精神对两国仍然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相对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远征军这段历史的遮蔽,现在这段历史成了当下的一个热点,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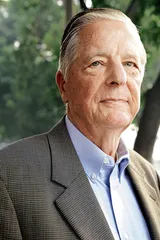 (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
(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回避它,正在进行的历史就会有一个大“洞”。对我来说,最温暖的感觉是两岸人民现在都对那些付出巨大牺牲的老兵都有了认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些抗战老兵实际上都是为中国人而战的,他们是与政治最不相关的人。他们被命令该去哪儿、该怎么做、该怎么打……但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知道对手日本人做的是不正义的事,他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
你知道这一次被接回来的遗骨,都是知道确切部队番号的。或许有一天,在缅甸其他地方还会发现许多中国战士的遗骨,他们没有名字,没有番号,能不能给他们建一座无名烈士墓,就像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那样,这样,很多远征军后代会想:我的父亲,或是我的祖父就在这里。这对远征军家属们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在太平洋战争中牺牲的一名美国士兵的墓碑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当你回到家,告诉他们,我放弃了我所有的明天,成全了他们的今天。”我是想说,在一切战争中,普通军人往往是付出最多而得到最少的人,我们欠他们的债永远无法真正偿还。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所能做的就是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且让历史记住他们为什么放弃自己的明天。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一位英军将领的后代也受邀参加这个仪式,而中国方面对当年的英军负面评价较多,认为他们对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应该负很大责任,你的看法呢?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参加那天仪式的,有很多身份特别的人,包括杜聿明的女儿、戴安澜的儿子,还有一位叫安德鲁·菲斯廷,他的父亲是英军皇家陆军第36步兵师师长菲斯廷,当年他带领部队与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缅甸;日本投降时,他任英国驻香港的陆军司令。
很多年前我就在研究中缅印战场。我有一次偶然发现,任英国皇家肖像画师学会主席的安德鲁·菲斯廷正是菲斯廷元帅的儿子,我通过网络与他建立起联系。他也很愉快地接受了云南方面的邀请并出席。我知道中国方面对当年的英军有很多批评。但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当时对他们来说确实很艰难,他们在欧洲开战,在非洲开战,战线拉得很长,可能确实力不从心。
冲突
三联生活周刊:珍珠港事变发生后,中美联手对抗日本,马歇尔决定挑一位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将领来中国协助抗战,可恰恰就是史迪威这位“中国通”与蒋介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被召回国,你怎么理解这个结果?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外祖父被派到中国,与马歇尔关系密切。1926至1927年他们一起在天津服役(注:史迪威任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及参谋,当时代理团长为马歇尔),他们互相了解。1930年前后,马歇尔在本宁堡步兵学校任职期间,史迪威任战术科主任,马歇尔对史迪威了解得更多,认为他是“教练的天才”。1941年,美国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有3个集团军、7万人参加。史迪威在所有参加演习的步兵司令官中名列前茅,一年内从一星将军升到二星将军。史迪威当时也被认为是美国9位陆军军长中最好的一位。
美国宣布参战后,马歇尔起初准备派史迪威到北非作战,后来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决定派他到中国来。我的外祖父被派到中国时,他以为他会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也答应让他指挥中国军队,但实际上并没有。蒋介石直接向中国军队发号施令,而这些命令常与史迪威的指挥相冲突,最终矛盾越来越激烈。
我的看法是,蒋介石非常愿意看到珍珠港事变的发生,他知道这样美国可以加入进来。蒋介石的一种想法是,让美国人打败日本人,他要保存军队的装备和实力,等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所以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防守。而史迪威是一名军人,军人最希望的是进攻,所以两人的想法肯定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对史迪威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史迪威过高估计了中国士兵的实力,不顾中国军力的实力,过分强调进攻,他对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我外祖父一直对中国士兵评价非常高。1942年,他在纪念卢沟桥事变5周年的广播讲话中说:“中国军人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好写照。他们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坚忍顺服的忠诚……他们忍受了无数困苦却从不悲戚。他们要求很少,却随时准备付出全部。”他说:“如果有好的领导、好的食物、好的训练、好的医疗、好的装备,中国士兵不亚于盟军的任何一支队伍。”当然,任何人只要处于负一定责任的位置上,都会被批评、被指责的。不管是当时,还是在后来,总是会招致批评。
在“二战”中,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致同意这样的战略:欧洲第一,太平洋第二,其他事务第三位。所以他们在缅甸战场最大的策略是坚持。
三联生活周刊:在飞虎将军陈纳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中,也发现他对史迪威的不满?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陈纳德将军一直认为,单凭空军自己就可以击败日本,所以他认为他应该是中国战区司令。众所周知,他和蒋介石夫妇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后来他和史迪威也有矛盾。
当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往中国运输物资的唯一线路是驼峰航线。但是驼峰的运量有限。史迪威认为打通地面交通线更重要。陈纳德想把力量集中于空军,史迪威想集中于地面部队,但不可能两方面都投入,矛盾最后闹到罗斯福那里,罗斯福最终决定给陈纳德更多支援。这就意味着,中国部队得到的支援会少一些。事实证明,1944年,史迪威的想法是对的——日军在一次袭击中几乎击溃了陈纳德的空军基地,但是那时已经太晚,没有人愿意听到这些。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主流的“二战”研究者对缅甸战场怎么评价?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在美国,缅甸战争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实际上关注的人也并不多。当然近些来这方面的书越来越多,但是更多注意力还是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近些年来也有一些美国人找到我,要写我外祖父的传记,可是我一看到他们的资料,就知道他们了解得太少,甚至完全不对。比如有人说,史迪威撤退时,他的部队死了多少多少人,可实际上,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史迪威拒绝了美军专门派来接他的飞机。他知道如果自己乘飞机先撤退,将永远失去中国士兵对他的尊敬。当时他已经59岁。他带着一个由美国、中国、英国、缅甸军人以及老百姓组成的114人的队伍强行军,穿过丛林撤到印度。是所有部队中唯一一支走出缅甸而没有伤亡的。
见证
三联生活周刊:史迪威对中国的了解源自何时?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我外祖父一生一共来过5次中国。第一次是1911年11月,当时他是一名中尉,在菲律宾服役,利用假期到中国来看看。他在中国待了17天,正好观察了中国刚刚发生的那场革命。第二次是1920年,他来中国学汉语,在北京生活了3年。当时他们在北京住的房子是北总布胡同3号。我妈妈的童年也是这里过的,她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昨天我和妻子还特地回到那里去看了看,虽然3号现在没有了,但是我们相信这里仍保留有他原来生活过的痕迹。90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去看一看,还是有很多感慨。
1926至1929年,他在天津任职于美国第15步兵团;1935到1939年他作为一名美国武官在北京任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是一名在北京任职的美军武官,事变第二天,他就赶到现场。从那时到1939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观察中日两军对垒。1942年被派到中国是他第五次来这里。
三联生活周刊:史迪威是1944年被召回美国的,而1946年他就去世了。他在美国的最后两年是怎么样的?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他被召回美国后,被告知不能谈论中国。因为他回国的一个星期后正好是美国大选,罗斯福担心他说出在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他的选举。
那时候,蒋介石在美国有强大的支持者,中国政府的游说团也非常强大。他们总是批评我外祖父,说所有的过错都在他身上。他不够“外交”,他不是政治家……说他错了又错。是的,我外祖父是军人,不是政客。1946年,有人想游说他竞选加州州长,他把那个人赶出了办公室。他做不了政客,他太诚实了。日本投降后,史迪威要求回中国探访他的老朋友,但被蒋介石拒绝,这对他是一种伤害。他一定非常伤心。
三联生活周刊:你毕业于西点军校,也曾是位职业军人,从一名军人的角度,怎么评价史迪威?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从我的角度,我的外祖父最特别的一点是,他与普通士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着很深的感情。不仅是与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也是这样。比如他专门为残疾军人建立了一个康复中心,帮助他们在退伍前学到一技之长。美国士兵对他都非常亲切,称他为“乔大叔”。他在战场上,也喜欢不戴军衔,冲在第一线,所以很得普通士兵的拥戴。
三联生活周刊:我也注意到,史迪威家族的好几位成员都参加过印缅战争。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我的父亲在美国陆军服役36年,“二战”期间,他是史迪威的执行助理。他先是在兰姆伽基地工作,1944年滇西反攻时,他指挥475步兵团在缅甸战场作战,配合卫立煌将军从云南向外打。不过我父亲对于战争回忆得不多,这一点,他跟我的外祖父有点像。在我们家族中,除了我外祖父,史迪威的长子、他的两个女婿——包括我爸爸,都到过缅甸战场,与中国人并肩作战过。可以说,我们家族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文 / 李菁)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成全所有今天马歇尔陈纳德蒋介石放弃他们明天三联生活周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