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地怀旧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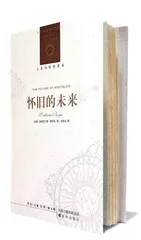 ( 《怀旧的未来》 )
( 《怀旧的未来》 )
流行病般的怀旧热
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2001)一书中说:“最近,cyber(赛博,计算机的)这个前缀本身已经变成了怀旧的,南贝格指出,新的前缀是e,例如e-world。赛博空间有开放空间和政府边疆的意思,而e-则更多地涉及标示领地,得到了大公司特殊的喜爱。这些公司想要把你固着在他们的地点上,限制你的计算机漫游。”
《智识生活》上的一篇文章说,e今天仍很常见,“电子书”(eBook)和“电子书阅读器”(eReader)的流行就说明了这一点。但i-和YouTube的强势表明,随着更先进的技术能向我们每个人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你我他的世界聚在一起变成我们已经成为过去。在1998年苹果发布iMac时,cyber已经不再流行,差不多被代表Electronic的e取代了。乔布斯说,iBook,iPod、iPhone和iPad等名称中的i代表的是Internet。他扭扭捏捏地不愿指出,i其实跟网络什么的无关,它跟你有关。它的用意是让你感到iMac是为你而造的。到1998年,E-mail已经出现好多年了,它的流行导致e被拆下,又安到了所有跟网络有关的现象头上,如eBay。
英国乐评人西蒙·雷诺兹在《怀旧狂热:流行文化对其过去的瘾头》一书中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如此沉迷于其刚刚过去的文化产品的社会。”1967年,贾格尔唱道:“谁想要昨天的报纸?谁想要昨天的姑娘?”在60年代,答案显而易见,没人想要。但时过境迁,现在我们想要的正是读昨天的报纸、挽着昨天的姑娘。在YouTube的“推荐”选项中,你可以直接从60年代的布鲁斯摇滚跳到80年代的电子乐和90年代的饶舌音乐,所有年代的歌曲并排在一起。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选择方式,以至于都忘记了以前我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文化的现在时态,过去只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很难说这是谁之过。在网络空间中,当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同时被放在你面前,今天的东西最打动你的概率还有多大?”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中,一位好莱坞编剧午夜乘坐出租车就能回到30年代的巴黎,当面聆听海明威和斯泰因的教诲。他还遇到一位毕加索的女友,而这位姑娘一心想回到更早之前的“美好年代”(1910年代)。艾伦希望我们从中学到一条教训:我们应该珍惜当下,不要怀旧,不要想着逃避现实。他曾经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生活的时代糟糕透顶,总以为如果能够回到过去,自己会更快乐。但在我们如今认为是身处黄金年代的那些人看来,他们当时所处的世界同样是苍白无力的。”电影中有一处表现了回到过去的一个好处:在大画家还没有出名前,多买几幅他们售价低廉的作品然后待价而沽。在《20年代回忆录》中又写了回到过去的风险:跟海明威玩拳击被他打破鼻子。

美国《新共和》杂志说,美国15岁的时尚博主泰薇·盖文森受到成年人的热烈追捧,这是因为,90年代的一代人刚刚到了感到自己小有成就的年纪,但也开始受到怀旧的折磨,他们把泰薇当做他们成长岁月里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代表。对这些成年人来说,泰薇代表了重新来过,是抓住自己青春的最后机会。她成了时尚作家和设计师们的玩具。
反思型怀旧
美国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说:“怀旧并不是新鲜事物。至少从荷马把奥德赛放到卡里普苏的岛屿、让他渴望返乡开始,怀旧就一直是艺术和文学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博伊姆认为,现代的乡愁和古代神话中的返乡差别很大。“奥德赛的故事不是个人感伤思念和终于返乡的家庭价值观,更是关于人类命运的一个比喻。奥德赛的返乡是一种礼仪性质的事件。现代的乡愁是对神话中的返乡无法实现的哀叹,对有明确边界和价值观的魅惑世界消逝的哀叹。怀旧与现代本身是同时期的,怀旧和进步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形象。怀旧是对缩小的经验空间的怀想,怀旧的表现是进步目的论的副作用。全球流行病般的怀旧是对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中对于延续性的向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
英语中的“怀旧”(Nostalgia)源自“返乡”(Nostos)和“怀想”(Algia)这两个希腊单词,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在17世纪,怀旧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医治的疾病,类似普通的感冒。瑞士医生都相信,鸦片、水蛭,外加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远足就能对付怀旧的病症。在21世纪,本来该须臾过去的失调却变成了不可治愈的现代顽疾。20世纪始于某种未来主义的空想,终于怀旧。”
博伊姆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现代怀旧: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修复型的怀旧强调怀旧中的旧,提出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反思型的怀旧注重怀旧中的怀,亦即怀想与遗失,记忆的不完备的过程。第一类的怀旧者并不认为自己怀旧,他们相信自己的研究所涉及的是真实。这类的怀旧是全世界民族主义复兴的特征,它从事历史的反现代神话创造。修复型的怀旧表现在对于过去的纪念碑的完整重建,反思型的怀旧则是在废墟上徘徊,在时间和历史的斑斑锈迹上,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的梦境中徘徊。
修复型怀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复原传统。在19世纪,由于工业化和世俗化,社会意义和精神意义出现空白,群体与凝聚力丧失,为了给个人怀想提供安慰性的集体稿本,有的社会通过新近创造的全国性的纪念实践,重新确立社会凝聚力、安全感和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比较健康的怀旧是博伊姆所谓反思型的、“外现代主义”的怀旧传统:既批判现代对求新的迷恋,也批判同样时兴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明。反思型的怀旧多限于怀想本身,推迟返乡——有惆怅、嘲讽和绝望之感。反思型的怀旧不避讳现代性的各种矛盾,修复型的怀旧维护绝对的真实,而反思型的怀旧对它提出疑问。反思型怀旧能够提出某种伦理的和创造性的挑战,而不单纯是午夜愁绪泉涌的借口。
博伊姆为反思型的现代怀旧找出了三个范例:波德莱尔最后一瞥的爱,尼采的永恒回归于阿尔卑斯高山上的忘却,本雅明与历史天使的对峙。波德莱尔回顾城市的幻影,尼采回顾宇宙和狂野,本雅明回顾历史的残破遗迹。怀旧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在托尼斯那里是传统的社群,在韦伯那里是迷醉的公众生活,在齐美尔那里是创造性的社会交往,在早期的卢卡奇那里是古代的整合文明。卢卡奇在《小说理论》的开篇就写了一首史诗高度的挽歌:“那是欢乐的时代,星空就是全部潜在的道路的地图——那些时代的道路都得到星光的照耀。在那样的时代,万物皆新,却又熟悉,虽然充满奇遇,自己却能够把握。世界宽阔,但是又像家园,因为灵魂里燃烧的火焰本性与众星一样。”
在浪漫主义时代,怀旧之风更甚。康德在忧郁、怀旧和自我意识的结合中看到了某种独特的审美感,这一审美感没有把过去客观化,而是提高了人对于生活与道德自由困境的敏感性。忧郁者不受驯顺堕落之苦,高贵的胸膛呼吸自由空气。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对于某种更好的世界的思念。怀旧是人们所共有的,它不该把人们分开。对于浪漫的哲学家和诗人而言,思念变成了人类处境中的一股驱动力量。诺瓦利斯说,哲学的确是一种乡愁,这是一种希望所到之处都是在家的要求。
博伊姆指出:“怀旧似乎是一个消极的词语,是离弃个人责任,某种伦理学和美学的沦丧。怀旧者从来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被放逐的人。”另外,更加危险的是,人们在怀旧时往往对地方习俗的前现代空间概念加以理想化,而这些习俗各有其地方的传统的残酷。现代性的超社团语言不仅是官僚行政的,而且也是人权、民主和解放的语言。“怀旧者把地方的和普遍的区分内在化,他没有争取普遍性和进步,而是限于回顾过去,渴望特殊性。”以度量标准的名称为例,前现代的空间常常是用人体的各个部分来度量的:我们可以把物品搁在一臂远,凭手指经验,记录步数。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不无怀旧之情地写道:“我们现在倾向于把距离称为客观的,而且度量的时候将其和赤道的长度比较,而不是和人体器官尺寸、躯体的灵活性或居民的好恶比较;其实在米尺金属杆这个非人格和解体象征物被放在法国塞弗勒接受世人的尊敬和服从以前很久,距离原来都是依靠人体和人类的关系来量度的。”■
(文 / 薛巍) 如何怀旧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