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勇进:洗白水浒
作者:王小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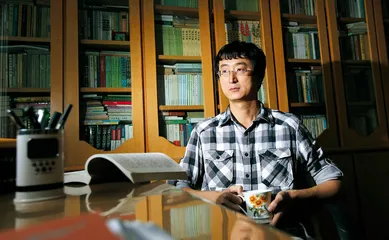 ( 孙勇进 )
( 孙勇进 )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因为故事里塑造了多个绿林好汉,在民间的影响力甚广,但同时由于它写作上和对善恶美丑等价值观念的局限,也常常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甚至不同时期出版的《水浒传》,内容也有千差万别。它就像一个开放式源代码一样,被后人不断改变着。而这种改变,从民间故事到各种曲艺版本,尤为明显。所以,当《水浒传》被拍成两个版本电视剧,都要对原作整容,但仍无法避免争议。相比之下,出现在曲艺、戏曲作品中的水浒故事,无论如何改编,人们都能欣然接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孙勇进,一直从事水浒民间曲艺版本研究,他认为,民间曲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水浒传》的缺陷和不足。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水浒传》你看了吗?
孙勇进:我看了一部分,关于电视剧的评论也看了一些。现在对这个电视剧批评比较多的,实际上上一版就有,这一版被人诟病得特别多,说它过分地洗白了,就梁山好汉的这种行为来说,就是他们除暴安良的色彩比原著要多得多。原著里有一些和现代文明比较冲突的内容,比如李逵劫法场,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砍倒一片老百姓,为了让朱仝上山把那个4岁小衙内杀了。这一类内容原来《水浒传》里非常多。
“五四”那一代,包括鲁迅、周作人,他们实际上对《水浒传》是比较反感的。周作人说得很严重,说《水浒传》是“吃人的文学”;鲁迅对李逵也没什么好感。“文革”时毛泽东和鲁迅的说法被印了出来,但是鲁迅对李逵的那些嘲讽文字都是见不到的,因为那时候李逵被定性为“农民起义的代表”。我最早用电脑的时候,是用的智能ABC输入法,我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里头有很多历史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名,能不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出现,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里面。比如说《水浒传》,因为当时我输入一些文章的时候会发现“李逵”、“武松”、“林冲”、“宋江”没有,但是有“方腊”。为什么呢?方腊是坚决的农民起义反抗者,而宋江是个反面形象。像“吴用”、“公孙胜”这些都没有。武松有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武松在民间文化中影响太大了,没有武松就没有山东快书这门艺术。那么李逵这个人地位很高,跟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如果看《水浒传》原著,这里有相当多血腥、野蛮的内容。所以这几年,我也看到网络上一些对《水浒传》的评论,而且一些网友也结集成书,很多人对《水浒传》基本是全盘否定的。第一,人们从《水浒传》中读出很多阴暗色彩的东西,这个确实存在。第二,实际上我1998年写的《漫说水浒》,也是这种思路来写的,从中看出很多负面的东西。这种思路,实际上是从“五四”的那个传统留下来的,你要反思国民性就会从里边看出很多阴暗色彩的东西。这种观点这几年在年轻人一代又比较流行。回头来看这个电视连续剧,就会觉得它在抹粉或者在歪曲这样一部经典。
 ( 山东水泊梁山即景 )
( 山东水泊梁山即景 )
比如呼延灼上山去打青州的那一段,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这两个形象跟原著差别非常大。你要是看原著,李忠的形象,如果说他“猥琐”可能重了一点,反正他不是很有英雄气概的一个江湖卖艺人形象。到了新版连续剧里,李忠是大大加分了,本来《水浒传》里他是个三流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四大名著里有两个是从评书、民间故事中整理来的,《三国演义》参照《三国志》,但是《水浒传》参照的史实不多,更多依赖民间流传的各种故事,所以民间故事和曲艺给水浒人物丰富了不少内容。
 ( 无锡水浒城风景区内表演的演员 )
( 无锡水浒城风景区内表演的演员 )
孙勇进:《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由传统民间故事演变而来,如果用专业名词叫“世代累积”,就是一层层累积起来。《三国演义》的累积形式,相对来说简单,是一种滚雪球,最早由《三国志》的核越滚越大,在滚的过程中,随着史料丰富,后面有些民间传说,艺术血液加进去了。《水浒传》是几个板块衔接而成,再后续加工。最早在山东,有关于水浒的“梁山好汉”的故事,然后在山西有关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在江南也有。比如说方腊故事、宋江发配江州等等,跟江南的分支有关。你如果看《水浒传》,在江州那一段是完全可以摘出来的。
《三国演义》演化过程比较简单,到《三国志平话》,跟今天的《三国演义》比较像了。但《水浒传》不是这样,你看到的元代的那些关于水浒人物的传说,跟今天你看到的《水浒传》差别非常大,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就是《水浒传》这个书成了以后,民间流行的各种水浒传说仍然跟它差别非常大,这是一个特点。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刀关胜这个人,你看元杂剧,关胜出场是在干什么?关胜出场是卖狗肉,他是被宋江派下山去执行任务,一时非常落魄,就偷了一条狗宰了,然后把狗腿剁下,卖了三条,正在卖第四条,是写这么一个故事。这就不是什么“义勇武安王关羽之后”这个形象。李逵的形象更复杂,李逵有一部分,你还能看到像浪子燕青、风流浪子这样一种味道,而且人也比较聪明,他有莽撞的一面,但他也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计策。那么到了《水浒传》以后,他就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定型。所以,它在元代那些传说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相当大的改变,这个和《三国演义》的差别比较大。
再看宋江,宋江在元代是“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一出场就是这种态度,完全一个强盗头子,到《水浒传》就变成一个类似于书生的形象。在《水浒传》初步几个板块拼接成型后,它后边还在演化。包括征大辽、征方腊的故事,这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还有征田虎、王庆的故事,完全是明代后期书商为了竞争塞进去的。但问题是,这种东西完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后来的民间传统曲艺也留下来了。王少堂的扬州评话里有“征四寇”的内容,明清时期的水浒戏,戏曲的变化过程就能看到今天的电视剧变化的一些苗头了,能看到通俗文学、艺术改编自经典有它固有的规律。比如我们上一版电视剧《水浒传》,被人骂得比较多的是燕青跟李师师的爱情故事,观众觉得无中生有。但是在明清戏曲里,给梁山好汉配家室的戏很多,武松也有妻子,林冲的娘子自杀后没死,上了梁山。这完全符合民间艺术的特点,通俗艺术一定要追求这种团圆。再有就是这个“洗白”的过程。从最早的“山东版”《武松》,到上一版《水浒传》,这个现象都存在。一开始我不太能赞同这种做法,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太缺少一种“历史的原貌”,即使不是真实的历史吧,在那个时代,那种人应该有的历史信息经过这样大幅度改变以后,很多东西会丧失。但是这两年我看了很多民间曲艺,包括扬州评话,我看出它那种改变是有合理成分的,不是说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才改的,而是洗白过程一直在发生。《水浒传》中有一段被现代人批评得比较厉害的,就是武松“血溅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小孩。王少堂说的武松这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武松已经不再滥杀无辜,他是有区别地杀,他如果杀了这个马夫,也说这个马夫如何欺负老百姓。最后张都监的夫人没杀,为什么张都监的夫人没杀?因为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张都监要陷害武松,她还跟张都监吵了一架。武松知道这个事情,是比较感动的,就没杀夫人。它就有这样一种“洗白”的过程。
杭州评话《宋江演义》,已经经过今人改编了,它做了一个“不彻底的洗白”。《水浒传》里面宋江为了让霹雳火秦明上山,弄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今天看起来太恶毒了。他派人假扮成秦明带着官军把一个村子给屠了,然后一个村子的人逃出来见太守,说秦明带人屠他们这个村子。结果太守一听,就把秦明一家都杀了,秦明就被逼无奈,上了清风山,跟宋江在一起了。这个故事今天的人看,绝对没办法接受。你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说评书,都不能照原样来,所以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处理。我看杭州评话的处理,它也是说“扮官军”,但它是把老百姓赶走后再烧的屋子,接着说宋江就没有想到秦明这一家子会被太守杀掉。实际上今天的人来看,把老百姓赶走也是不对的,但是杭州评话毕竟已经有洗白了。
昆曲是非常高雅的艺术,包括京剧,从清代开始,戏曲里的水浒戏,戏份最多的是武松,还有杨志、林冲。然后最多的是另外三个人: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女人戏特别多。今天我们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就觉得潘金莲又改了这么多的戏干什么?从上一版就在骂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改编过程,实际上几百年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定符合这个通俗艺术的某种特点,只有这个它才能引起大众的一种趣味。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的历史阶段价值观的变化,人们对某个人物都会有一个重新理解,通俗艺术的表现可能就更明显一些。
孙勇进:通俗,它也有些固定的趣味所在。明清,尤其清代,水浒戏里,这几个女人的戏份就多起来了,现在来改编的时候编导也会对她们比较感兴趣。但是另外一方面,即使同样是老百姓,随着时代变化,价值观也会改变。就清代来说,她们的戏是比较多,但是老百姓评判的角度还是比较接近原著,把潘金莲当做淫妇来审判。到今天,这种判断就可能会被颠覆,但是关于潘金莲颠覆比较早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魏明伦的川剧,当时轰动也比较大,那个剧本我看了,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实际上,对经典的阐释永远是随着时代变迁,对人物的评判在不断地变化。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电视剧改编这么大是很容易被人骂,但是实际上评书早就有非常大的改编。像袁阔成的《水泊梁山》,因为只保留了“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外壳,它和原来《水浒传》差别非常大,而且里面基本上都是好汉,都是替天行道的,没有哪个非常丑恶的,包括矮脚虎王英。在袁阔成这个书里,围绕王英这个故事讲了很长时间,跟他老母相依为命。那么为什么评书的听众没有对此大加挞伐?这真是值得讨论、值得琢磨的一件事。
三联生活周刊:评书有一种为了吸引听众而把一种平均审美观和价值观表达得比较充分的特点,你喜欢我就多说点,随时可以往里面加一些东西,所以自圆其说的空间也就很大。
孙勇进:像王少堂的这个例子就非常典型,最初是能说20多天,然后是说到50多天,最后能说80多天。就是经过王少堂、王丽堂深度加工,关于武松的故事就有80万字,石秀、宋江、卢俊义,都有几十万字。有不断加工的过程,根据什么来加工,或者向哪个方向来加工?这就是一个问题。像扬州评话,包括乔郓哥的故事增加了很多,但是它对整个的水浒故事结构没什么影响,价值观也不会改变,对人物的评判也不会改变。袁阔成的《水泊梁山》完全另起炉灶。但是如果听田连元和单田芳的评书,这两个说书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都说到了招安、征方腊,单田芳多说了一个征大辽。说到这个招安过程,田连元他有一处改编非常精彩,就是在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下山前,林冲死了,而上一版电视连续剧林冲被气死了,这个改编我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古典小说有个缺点,写人物心理活动特别粗糙。如果完全忠实于《水浒传》,那就是高俅被押上山,看着林冲、杨志对他怒目而视,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实际像林冲这样的血海深仇不是“怒目而视”就算完事的。古典小说写心理不是强项,写心理强项在戏曲上,戏曲大段大段的唱词表现人物心理,林冲夜奔时候的心理,非常非常动人。小说里不行,包括像秦明全家被宋江弄诡计陷害了,被押上山了,然后宋江说服了他让他入伙,那秦明是怒气冲天,最后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这么一句话就给打发了,这个今天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一到电视剧这里你不改是不行的。田连元说林冲下山前死掉的过程,整整说了半小时,非常动人,比电视剧还要精彩,那么这个改编绝对是胜出了《水浒传》原著,他看到了《水浒传》这个缺点。实际上,原著一改成评书或电视剧,文学作品的毛病就出来了,包括金庸的《天龙八部》也是这样。我记得香港无线回忆拍《天龙八部》,一拍才发现到处都是漏洞,你读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出来,所以说肯定有一种修补,这种修补是一种合理的修补。
单田芳说《水浒传》也有他的强项,他把《水浒传》原来最弱的那一环说出味道了。《水浒传》最弱的那一环,就是征大辽,那个情节实际上粗糙得一塌糊涂,地名、人名也是乱七八糟。我们看电视剧有“垃圾时间”,《水浒传》征大辽这一段绝对属于垃圾段落。而单田芳说书,他能把这个说得很有味道。征大辽实际上价值极低,情节非常荒唐。单田芳说起来就很好,本身说书的传统就有这么一个套路专门讲征番邦的,他把那套他多年的艺人功底全部搬过来用来说这个。一部经典作品完成后,这个传播过程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完全忠实经典不太可能,《水浒传》就是这么一部作品。作为电视剧的编剧也好,它永远是处于一种两难之中。整个《水浒传》,武松的故事非常特别,有武戏,文戏也很丰富,不像鲁智深,基本上是武戏的故事。所以武松的故事特别适合说书,因为说书要讲很多人情世故,武松提供了很多这种元素。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人物非常适合说书人发挥,并且很投入感情演绎。
孙勇进:听袁阔成说书我至少有几次我能很明显感到,他说三国人物真的非常非常有感情,田连元也是。我想那些好的说书艺人都有这个共同特点,到了自己能够和说的人物同喜怒共哀乐的时候,他说出来就容易打动听众,哪怕说的跟原著完全不一样都没关系。袁阔成的《水泊梁山》非常典型,与原著差别很大,但是袁阔成“在”这里面,而且他不是出于理念先行的改造。如果编剧、导演缺少这样一种东西,只是觉得他“应该”这样或那样,你靠这堆“应该”去改造,最后可能观众就不买账。人的思想理念是有差别的,但感情的喜怒哀乐是共通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评书艺人改编的《水浒传》版本,跟原著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孙勇进:袁阔成的和原著的差异,以前香港拍过一个电影叫《浪子燕青》,那个套路是非常像的。故事结构的一种大幅度的改变。以“三打祝家庄”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像擎天柱史文恭后期出场的人物都先出场了,包括花荣出场的故事跟整个的《水浒传》都完全不一样了,大量人物的特点、故事都不一样了。另外它表现的这种好汉的气势也不一样。矮脚虎王英在袁阔成的书里完全是正面形象,包括卢俊义上山的过程,《水浒传》原著里吴用使用了类似于下三滥的手段,那种东西在袁阔成的说书里都没有。
我听说书艺人说书,经常会听非常“古”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像袁阔成的《水泊梁山》,晁盖是在三打祝家庄的时候中毒箭死的,最早的元杂剧也是这么说的,是到了《水浒传》才改成曾头市死的。包括单田芳讲《三国演义》那段“三英战吕布”,最后讲到张飞抽出九节鞭,打了吕布的三叉紫金冠。《三国演义》里没有看到张飞使鞭子,但是元杂剧里张飞使鞭子次数非常多,张飞就是用鞭子打的。
我有一种推测,说书艺人讲的一些东西,可能有从他的师傅那里甚至更早传承下来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大的改编,这个改编肯定是适应当时民众的价值观。而袁阔成那个时代,他讲《水泊梁山》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的文化总体来说非常多元,80年代基本来说还是对劳动群众进行一种歌颂、肯定,是一种社会共识。所以在袁阔成的书里,他做这样一种大幅度改变,也可能跟它产生的时代有关。那么到了田连元这里,他是基本按照原书框架来的。《水浒传》第一回是从“洪太尉误走妖魔”说起,田连元和单田芳说书都从“高俅故事”开始说起,“误走妖魔”这个东西没有,因为现代人他已经不太能接受这种东西了。田连元、单田芳说书,比较忠实于原著,按照原著的脉络来,有演义,也有“灭活”部分的处理,你没有办法,必须得处理。
清代,说武松“鸳鸯楼十五命”,那很正常。包括我很小的时候听评书,讲武松故事,实际上是从扬州评话改编过来,是用普通话讲的,还是讲武松杀15个人的事,那过程仍然是一种津津乐道的口气。但是随着发展有些东西越来越难以接受,所以洗白过程一直存在,洗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三联生活周刊:其他民间版本在处理上有什么特点呢?
孙勇进: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它一定是遵循通俗艺术和民间艺术一些共同的规律。比如武松跟西门庆打斗过程,有人问我,武松杀西门庆这么一个酒色之徒还用这么费劲吗?这个你不能赖编剧,民间说书就是这个样子,你看高元钧说的山东快书,也是西门庆一脚就把武松的刀给踢飞了,《水浒传》原著里也是西门庆一脚踢到武松的右手,刀飞到街心了。按照杭州评话的说法,武松的拳脚是不如西门庆的。扬州评话我看了王少堂、王丽堂整理的两个版本。王少堂那个版本应该是50年代的,按照自我教育删掉了很多东西。到了王丽堂的版本,她把很多删掉的东西又恢复了,就比较接近最初说出的原貌。王丽堂这个版本,过程也非常复杂,西门庆就是武艺高强,而且武松有心理活动,说幸亏这刀是在我手里,如果是在西门庆手里,那今天我性命就很危险了。这个捎带想说什么呢?为了争取听众,就要知道哪些地方我必须得延长。我看《回忆录》说王少堂讲《武松》,说武松“嗖”地拔出刀对着潘金莲心口要剜下去,过了一个月这把刀还没有剜进去,不断地往里加东西。所以说说书的特点,它一定是人情世故会编得特别丰富。说书人之所以这么说,第一,要考虑市场,我必须书说得足够长我才可以谋生;第二,就是对人情世故他有很细的体贴。这种体贴有一个优点,就会把原著的心理活动粗糙的弱点恰好可以给弥补过来了。
田连元说林冲下梁山,那时候林冲本来已经病了,梁山好汉都兴高采烈地招安下山,他自己就想:“我到东京去干什么,我这个老宅子要不要去看,也许都已经长满了荒草,也许换了旧主人。那么左邻右舍会说,哎呀,林教头回来了,您怎么回来了?您的娘子已经怎样怎样,一家都完了。现在您又要到仇人手下去当差……”这种痛苦这种挣扎,田连元讲这个过程非常动人。然后,怎么去给晁盖上坟,听到阮氏三雄给晁盖上坟,他们哥仨去了,他们也有惆怅和留恋,但是跟林冲的反应不一样。碰到林冲,然后林冲让他们带着三坛子酒,林冲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头,怎样不停地喝酒,怎样心理活动,怎样最后留一首诗,最后才死掉。这一段可圈可点,把原著很弱的一个地方给补上了。
《水浒传》很大的一个缺点是人物心理活动特别粗糙,而且极不合情理,今天一看就非常可笑。宋江老是对那个降将“纳头便拜”,然后“愿让座位”,你总玩这个,问题是呼延灼他站在一边看着,他什么心理反应?但是这种心理反应《水浒传》就不写了。但是说书艺人说这个,这个难题就摆在面前,你必须得处理,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要么你就别说宋江总这样,要说你就要说呼延灼什么心理反应?关胜什么心理反应?所以民间艺术它会有一个合理化的修补,就是一种细致化加工和传奇化加工的过程。■
(实习生付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王小峰) 读书文学宋江林冲四大名著武松水浒传评书田连元袁阔成三国演义评书水浒传单田芳洗白孙勇进袁阔成水浒传水浒传宋朝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