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艾滋器官移植事故:疏失后的讨论
作者:陆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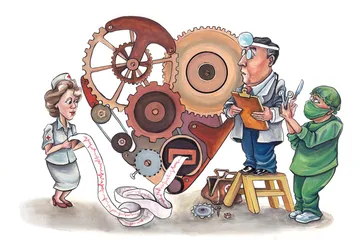
喜与悲
劝邱妈妈捐献儿子器官的,也是一个同样遭遇孩子坠楼的母亲,她捐出了孩子的器官,并参加了当地的器官劝募组织团体做义工。因为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主导,再加上台湾对地下器官交易的严格控制,虽然在台湾器官捐赠推行很久,却并不普遍,等待捐赠的人非常多,每一个捐赠器官的获得都会令医患双方如获至宝。
据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翠芬向本刊介绍,邱妈妈本人是社会慈济系统的志工,参与社会服务很久,家庭条件还算好,也是愿意助人的人。8月23日,儿子坠楼后转了几家医院后被送到台湾新竹南门医院,医生判定脑死亡。第二天邱妈妈就同意捐赠器官,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同性恋的儿子是艾滋感染者。台大医院和成大医院两家医院在接到有关器官捐赠的通知后派出医疗小组,当天就前往新竹南门医院摘取了各自需要的器官,台大医院器官移植小组取走了肝、肺、肾等4项主要器官,成大医院获得心脏,之后给各自医院的5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很讲究抢时间,迅速和高效,这意味着器官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
按照台湾器官移植的程序,首先是社会团体进行器官劝募。“劝募到一个器官捐赠,以前医院之间会抢器官,后来有一套规则,看各家医院的积分有多少,可能是能够劝募到的器官,移植效果怎样,一拿到器官就马上比,看哪家医院分数最高就给谁。台大本来心、肺、肾都要做,那个心脏病人本来分数比较高,后来因为比对的时候发现血型不合,成大就拿去做了。”一直从事公共医疗领域研究和报道的张耀懋向本刊记者这样介绍。各家器官移植医院的协调师会在医院接到器官捐赠消息后做大量的工作,包括确认捐出器官,协调怎么捐,捐到哪里,进入器官登录系统登记,安排医院检验,上传检验报告,通知受赠医院,还要安排移植手术的具体事宜。“协调师大部分是护士转过去,工作非常忙,像出事那两天,就有3台器官移植手术同时在进行。”在器官移植手术前,必须对捐赠者进行包括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等几项检验。“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反应者的器官都是不能捐赠的。”按照器官移植的标准化流程(SOP),在检验环节,检验师先将检验结果上传到医院病历系统,与协调师电话沟通,协调师登录电脑系统确认病历,通知移植团队后,主刀医师再次进入病历系统查看检验结果。
这套标准化的流程看起来的关键就是反复确认。“但是四五百页的SOP,你知道实际操作的时候是并不能完全拷贝的。”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董事长张苙云向本刊记者表示,“我们用这次器官移植作为例子,器官移植当然是重大的手术,而且等的人每天都在走向死亡。在做手术之前,整个器官移植团队,医生有主刀的,有麻醉医师,有检验师在后面做检验,有护理人员,有许多应该做的动作。主治医师应该看报告,不断地做确认,读病例,检验报告,确认病人就是你原来要的病人,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做“三读五对”。这是整个医疗团队有几位关键的人应该要做的。但是为了速度,工作量大了,有的步骤常常被省略。”
在移植手术48小时后的8月25日,台大医院才在器官书面检验结果报告中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测试为阳性的结果。事后台大经初步调查发现,导致5个病人被移植艾滋器官这样重大事故的关键环节,竟是检验师和协调师电话沟通中的失误。“原始检验报告结果的次序是B型肝炎抗体positive(阳性)、B型肝炎核心抗体reactive(阳性)、C型肝炎抗体negative(阴性)、B型肝炎抗原negative(阴性)、HIV抗体positive(阳性)、梅毒non-reactive(阴性)。因此就是positive、reactive、negative、negative、reactive、nonreactive字眼一再出现。”台湾移植医学学会理事长李伯璋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检验师说的是“reactive”,协调员说她听的是“non-reactive”,动刀之前,医生凭借对协调师的信任,没有再次确认,导致感染艾滋器官被当做一切正常植入了他人身体。
张翠芬告诉本刊记者,目前5位受捐者中,被移植心脏的患者已经检测到HIV抗体,其他也都在接受艾滋病疗法的治疗,大量用药,还要观察3个月再检查身体里有没有艾滋病毒,同时,47位相关医护人员也有感染风险。
“按照《人类免疫感染者权利保障协议》22条,检验出HIV阳性,进行艾滋器官移植,以至于有人感染艾滋病毒,将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目前检察官已介入调查。台大说一年以后才能确定有没有感染艾滋病毒,所以还要有一段时间。”张耀懋说。
陷入痛苦的不仅是被移植艾滋器官的病人和感染阴影下的医务人员。捐赠者的姐姐说,家里在决定捐赠器官时心里很挣扎,因为这是他们帮弟弟做的决定,全家人好不容易将弟弟死亡的悲痛化为做善事的欣慰,现在又要背负无颜面对受捐者的巨大压力,善事成悲剧。
责任追问
台湾有38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其中16家去年都没有做,14家做了不到5例,除了几家比较大的医院很多都不活动,这次“撞枪”的台大医院和成大医院都是做得最好的,因此也更让民众感到震惊。台湾《天下》杂志的医疗记者林幸妃告诉本刊记者,台湾的媒体一直在讨论到底是制度问题还是人为的疏忽,很多报道都在质疑是不是只能怪一个器官协调师,制度是不是还有要加强的空间,制度的流程是不是出了问题。
台大医院在两天后发现了问题,立刻通知院方通知“卫生署”,“卫生署长”当时在美国,也立刻赶回来。卫生主管部门对于这场“国际级的悲剧”的处理按照两个层面分头进行。一方面是危机处理,其中一部分是事故调查,“卫生署”立刻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事故实际是怎样发生的,责任在哪里,要求台大医院和成大医院都要提出报告,调查小组也很快去两家医院做实地访谈。另一部分成立了一个关怀小组,对于涉及医疗团队、捐赠人家属、被捐赠人家属和被捐赠人,由社工组成法律心理辅导团队。据张翠芬介绍,这些工作可能9月底有一个初步结果。
李伯璋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事故被披露后,医院一方面迅速组织对病人的关护,一方面做事故的检讨报告。“卫生主管部门想把责任归到开刀的医生,但这并不公平,移植的疏失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张耀懋说,“民众和舆论都没有把很多压力加在那个可能犯错的协调师身上,对病患、医师和可能出错的协调师,大家在愤怒和震惊之上是同情的。”并且台湾社会都倾向于认为,此次事故是制度和系统的问题。“一个严谨的制度应该是,有一个人出错,还有其他补救措施。医院平常的操作也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重复,每一个医师开刀前一定要看过所有检验报告,单纯一个人的错导致全部崩盘,一定是会归到制度问题。”
8月30日,“卫生署”医疗调查小组第一次会议后做出初步结论:将对台大医院与成大医院先开出第一张罚单,两家医院将被地方卫生局罚款15万元新台币。8月31日,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台大器官移植小组标准作业程序(SOP)的撰写者、器官移植团队负责人之一的柯文哲最先承认医院失误而辞职。张苙云对本刊记者表示,柯文哲说他在SOP里少写了一个动作,就是检验师在为了争取时效,在同协调师电话里口头说明检验结果后,应该再有一个确认动作,要求对方把听到的重读出来,再次确认。“但即便他没有写这个步骤,出现这种失误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举个例子,我今天看到器官移植报告,出现HIV有反应,表示说他是感染者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很冷静地报告,一定会有反应,说这个是不可以移植的,一个说讲错一个说听错,讲的人难道不会夸张一点讲?而且因为台湾的病例全是用英文写的,所以造成自然用英文回答,出现误差,以后可不可以改成用中文沟通?”
“大家都在谈协调师听错了,但是我们不认为关键在这里。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的医疗界在过去的将近30年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朝向利润先行,对于效率的要求、人力精简,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运转,在监督没有办法监管下,其实有很多基本动作都忽略了。所以这个事情很根本的问题是,医院应尽的义务这件事情长期以来都被忽略。”张苙云说,在医疗现场,如果检验师和协调师讲错了,已经摘下了捐献者的器官,要把它移到等待接受器官的病人的身上,那主刀的医师、麻醉医师、护理人员,整个团队总要有人看到,而且应该不止一个人看,大家都要看一下这个报告有没有搞错。“美国在几年前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子,是在半夜发生的,那次是因为血型搞错了,以至于被移植的人出现排斥死亡。因为器官捐赠这件事情,全球各地方都是稀有资源,所以一旦有人捐献,大家都很期待能把这个器官及时移植到需要的人身上,这个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基本动作不能忽略。”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台湾已经具备了相对严格和完善的器官移植制度,1968年,台大医院李俊仁与李治学教授完成亚洲首例亲属肾移植手术,1987年公布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赠与移植工作需经由移植医师、受赠者、捐赠者及其家属、器官劝募医院、器官摘取医院、器官移植医院相互配合建立合作关系,为使每一位等待器官移植病患皆能有公平机会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得到最佳器官捐赠与移植的成效。2002年,由台湾“卫生署”捐助设立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即捐赠器官分配平台,目前有10家医学中心与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签约为器官劝募网络合作医院。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从理论上,有完全责任要确认协调师在登录中心网页输入数据的正确性,更应该要确认文书准确无误后,才能进行比对安排那位等待者接受移植手术。“因此所有医院同仁都信赖中心提供的信息。”
在李伯璋看来,这次的事故暴露出台湾的移植器官界信息不通畅的问题。“‘卫生署’下面有‘疾病管制局’,针对一些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病人在‘疾病管制局’负责监控,这次的捐赠者长期受到‘疾病管制局’的监管,但是该局的工作还是有漏洞。”他举例说,一个艾滋病人在A医院接受治疗,如果到B医院去,B医院都不可能知道他是艾滋病人,因为在台湾每个病人手中的健保卡上,为了保护隐私,上面并不会特别记录有关艾滋病患的信息。“法律上也规定艾滋病人就医时要自我说明,但是实际上他不会说。这样的保障隐私权没有道理,其实对照顾他的医务人员很不公平,他们可能会直接跟艾滋病人有体液或血液的接触。”
更大的社会讨论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目前的艾滋管理体系也被拿出来检讨。台湾《商业周刊》的记者林郁怡向本刊介绍说,台湾目前的艾滋病患者有几千人,他们的名单由“疾病管制局”列管,并且法律上有所规定,艾滋病人的隐私受到保护。“艾滋病患者需要鸡尾酒疗法,是混合性药物治疗,在国外是昂贵的开支,但台湾是公共健保给付,所以患者只要不说,大致健康在不特别恶化情况下可以生活几十年,家属亲友也不会知道。”有此背景,首先邱妈妈并不知情。
“健保卡上是没有注记的话,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人权问题,这次事情出来后也在讨论,这样是不是为了保护HIV的患者,那我们要不要保护其他的病人,要不要保护医疗人员?在早期,就是非常单纯地认为HIV病人在就医时遇到了问题,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所以这次因为器官捐献的当事人在“疾病管制局”是登记有案,而且他在新竹当地的某家医院是追踪的病人。但是发生事情他没有送到那家医院,而是送到了另一家医院,另一家医院并不知情。”张苙云由此认为,艾滋病人的人权对应于他人的安全,要怎样去平衡,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议题,需要民众有共识。
张耀懋表示,由此而生的另一个讨论是关于医疗选择的问题,艾滋病现在不是绝症了,虽然不能治疗好,但是病情能被控制住,是不是查出来就不能用器官直接丢掉?“有些人提出,也许应该可以用,被移植者生命起码能延长几年,大害换小害,给你一个有缺陷的东西你要不要。”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器官移植部门临床主任阿比纳夫·胡马尔(Abhinav Humar)由此告诉本刊记者说,目前美国的情况是,艾滋病患者的不测病毒负荷和细胞计数超过200能够接受肾移植和肝移植,但是艾滋病患者不允许捐赠器官。“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正式讨论,我们当然支持。”台湾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宜慧对本刊记者说,“目前的情况是,如果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有器官移植需求,在名单上可能也比较靠后。”
根据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执行长何国章的说法,台湾器官移植的医疗技术已有相当成功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所需器官捐赠者的缺乏,“较之先进国家,台湾器官捐赠劝募相关作业仍在起步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李伯璋认为此次事故有可能会是一个转机,可以让政府和民众看清器官移植的重要性,台湾一年200人捐赠器官,这200个机会有6000多人等待,做器官移植要30年,而欧美国家等待的人只有一半满,3到5年就有机会得到。“台湾过去10年有2133位病人是到院外接受肾脏移植,2109人在岛内接受移植。目前有6981人等待器官,到今天只有140人的尸体捐赠器官,只有半数人会被移植团队摘取器官,意味着器官捐赠作业的复杂性。”
“台湾大部分是财团法人医院,也就是私立医院,器官捐赠的工作要有很多事情,人力不够时愿意做的医院就很少,因为不合算。医生做这个要投入很多心力,助手不够、协调师不够就会有问题,做一个移植手术,自己的其他很多手术也都会受影响。”李伯璋举例说,8月23日成大医院派出6位医疗人员前往执行摘取心脏,同时,又有21位工作同仁在台南同步进行受赠者手术,一切医疗给付完全来自健保,摘心手术费1.5596万元新台币是给予合作医院,心脏植入手术费是8.9317万元新台币,完全不敷27人的人事成本和交通费用,完全不符合医疗经济效益。
张苙云坦言:“要做器官捐赠事情大概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没有说应不应该捐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也就因为这个,台湾民众在这方面大家还蛮努力,一直在宣导,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人总有离开世界的一天,假如我们的器官还有人能用,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其实,台湾讨论死亡这个事情的风气已经蛮普遍的了。”■
(感谢实习记者叶雨青对本文的帮助)
(文 / 陆晴) 器官移植医疗台湾讨论疏失艾滋病艾滋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