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文学:像航海一样周游世界
作者:石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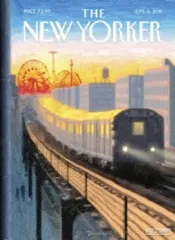 ( 荷兰“桂冠诗人”拿瑟尔 )
( 荷兰“桂冠诗人”拿瑟尔 )
“什么是你所认为的荷兰文学?”荷兰文学基金会主席亨克·普罗佩尔(Henk Propper)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而是话锋一转,讨论起了荷兰人的“旅行心态”:“荷兰周围被德国、法国、英国几大强势的文化传统包围,但是荷兰人并不故步自封。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航海的传统,出去四处游荡,我们不仅不愿意束缚自己,而且喜欢抢在别人前面一步去见识全世界。”
这段话大概可以解释这位主席2003年上任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荷兰文学的雄心壮志。“‘4’是我们的幸运数字。”他笑道,“在荷兰,专门支持荷兰文学发展的基金会组织主要是4个;2005年第一次参加北京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展台是4平方米。”他比划着,回忆着当年的“寒酸”,显然对眼下1500平方米、充满设计感的主宾国展台感到非常满意。“刚来的时候,在中国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荷兰文学译本只有10本,如今已有150本。”这次他带领的22位荷兰作家,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至少一本中文译本,“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荷兰文学在国际出版界发出声音的历史并不长,这是业内的普遍观点。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即便是在欧洲,荷兰文学也可形容为“默默无闻”。这一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首次成规模地展出了荷兰语文学,掀起了此后德国人对荷语图书持续性的阅读和评论兴趣;法国则举办了名为“美丽的他者”的荷兰语文学专展,一次性向法国人介绍了11位荷兰作家。这一译介潮流10年后在法国达到最高潮,2003年,荷兰成为法国年度书展的特邀国,在那次展览上,一共有55位荷兰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去了法国。
时至今日,德国和法国仍然是荷兰文学在欧洲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有地缘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亨克·普罗佩尔说,“荷兰语是最接近日耳曼语的一种外语,而两次世界大战也使德、法对荷兰这个小国分外关注。”
“荷兰作家光在荷兰出名是不够的,去德国和法国是第一步。”参展的荷兰作家之一赫尔曼·郭可(Herman Koch)对本刊记者说,“大多数荷兰人除了荷兰语,也会英语、法语、德语。我们的有些作家和西班牙、意大利作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也有一个更广义的欧陆文学的概念。”“欧陆文学”最直接地便和“英语文学”形成鼎立之势,而荷兰这样一个小国,对英语文学的挑战感受相当直接。“荷兰书店里卖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英、美图书的译本。”荷兰最著名的博客书评人朱迪思写道,“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荷兰语文学。就我本人而言,也是在专门开了一个评介荷兰语图书的博客之后,才开始从以前的一个月勉强看一本(荷语图书)到现在的每周一本。”而一位英国的出版商则更直接地宣称,荷兰的图书市场就是英、美图书市场的翻版。
 (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景 )
(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景 )
荷兰本国人口约1600万,加上周边的荷兰语地区,全世界说荷兰语的人口不超过2000万。尽管荷兰人是一个出了名的爱读书的民族,“荷兰本地的图书市场还是太小,而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收获往往让人喜出望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亨克·普罗佩尔说,“比如巴西,你能想象吗?我们的书居然在巴西大受欢迎。非洲的话,限于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我们主要关注南非,以及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等等。印度我们也在开始尝试,然后就是中国,我们很重视中国市场。”听着他描绘着设想中的传播路径,令人不禁联想起400年前,荷兰人经由海路的第一次殖民扩张,那一次,荷兰在远东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印度尼西亚都建立了根据地。“哦,进军印尼时我们会非常小心。”亨克·普罗佩尔一边沉思着一边说道,“当地的年轻一代的确非常敏感,强调民族自尊感和文化自主意识,我们在考虑译介什么样的图书品种和推荐什么样的作者时都得非常注意,不要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不要让单纯的文化传播绞缠到后殖民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争论中去。”
而翻译,无疑是荷兰文学在这新一轮的海外扩张中最为重视的问题。“20年前,这家基金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关于翻译的种种议题就成了工作的焦点。”亨克·普罗佩尔说,“比如应该把重点放在译出去,还是译进来?这是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出版商都要权衡的问题。大家都想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目前翻译荷语图书最多的德国,其想法之一就是荷兰语可算作德语的一个变种,荷兰文化仍属于日耳曼文化圈内,因此,多出版荷语图书等于间接增加了德语图书的产量。
而英语毫无疑问在世界图书出版界仍然具有霸权地位。亨克·普罗佩尔向本刊记者坦言,如果一本荷语图书能够被“纽约知识分子圈子”注意到,并由此引进“自给自足”的北美市场,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作为一个荷兰诗人,你一开始写作就知道你使用的语言是一个小语种,因此就会心怀谦卑。”此次参展的诺姆西·拿瑟尔(Ramsey Nasr)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以来,他一直是荷兰的“桂冠诗人”,也是亨克·普罗佩尔屡次在采访中提到过的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年轻作家。“而一个荷兰作家如果没有被翻译,就等于不存在。”诺姆西·拿瑟尔说,“翻译一方面扩大了声名,例如我的一本诗集最近被翻译成了英文,接下来我就收到了好几次参加活动的邀请。但是,在活动中,我又发现自己不时被人误解为我是英语诗人,而非荷兰诗人。”
荷兰文学的外译工作是“二战”后在公共基金的支持下起步的。起初一二十年间,翻译出来的图书在荷兰本国的文学界并不受认可,作家们认为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无法传达出原文的意韵。荷兰“文坛三剑客”之中个性最为激进的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ck Hermans)直接撰文申诉“被翻译作家的痛苦”,认为从挑选译者到定夺对方出版社都未能体现对文学性的追求,外国书商感兴趣的是借此机会能够获得更多的荷兰政府和基金会组织的出版补贴,而非推介荷兰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带来的是荷兰最好的出版社,也希望能够与中国最好的出版社合作。”亨克·普罗佩尔说道,“如今大量的荷兰语作品都是先有英文译本,再从英文转译到其他语言,比如中文,这样几经周转的翻译质量并不太好。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直接从荷兰语翻译到其他语言,因此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项目,来支持这一工作。”
他指的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翻译者之家”,这一只有三个工作人员的项目其中心服务对象就是荷兰语作品的外国译者,与荷兰文学基金会的前身——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同时成立,迄今历史整整20年。“我们邀请翻译者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居住,提供给他们翻译工作过程中各种必要的参考和辅助设施,例如图书馆、复印机、传真机,还提供配套的生活设施。”亨克·普罗佩尔说道,“对于一位译者来说,如果他译的书与阿姆斯特丹有关,而他自己从没有来过阿姆斯特丹,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遗憾。我们希望他能来,实地体验阿姆斯特丹,从而译出更好的作品。”
“与法国、俄罗斯等这样具有伟大作家的文学传统相比,荷兰文学可以说没有传统。”诺姆西·拿瑟尔说,“100年来,荷兰文学也可以说没有主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个人主义就是荷兰文学里最大的潮流。荷兰作家是‘自治’(Autonomy)的,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的创作和荷兰这样一个语境有什么本质关联,而只是一种个人化表达。”《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的作者黑特·马克(Geert Mak)则用了另外一个词:自由。“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共和’色彩浓厚的城市,但是这种‘共和’概念并非来自政治,而是来自商业。”他说,“商人追求利润,而利润来自于自由交易,核心是信息的自由流动。荷兰人追逐着风和海的脚步,这种自由一直延伸到文化的自我定位,以及人心的思想深处。”■
(文 / 石鸣) 文学一样周游世界荷兰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