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作者:薛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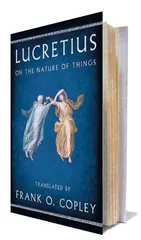 ( 长诗《物性论》
)
( 长诗《物性论》
)
诗人哲学家
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被视作古代拉丁文作品中最好的哲学著作,在知性的严肃性和论辩的力量上优于西塞罗和塞涅卡。但西塞罗把卢克莱修当做诗人加以崇敬,从来不说他是一位哲学家,塞涅卡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么好的哲学,裹着如此华丽的外衣,却完全不被当做哲学呢?很明显,坏就坏在了它的文体上,因为它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詹金斯说:“如果今天一位哲学家向学术期刊提交一份用诗歌或对句形式写的论文,他会被认为精神有问题。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用诗歌形式写的哲学作品如果不像现在显得那么怪异,也是相当异乎寻常的。在比卢克莱修早400年的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还有可能用诗句写哲学著作,卢克莱修敬佩的恩培多克勒和巴曼尼德斯都这么做过。但到了那个世纪的尽头,诗歌已经不再是历史、哲学和科学的天然表述方式。如果你想了解天文学,你会去读阿拉图斯的诗《观测天文学》吗?不会,你会去读欧多克索斯的散文论文。如果你被蛇咬了,你会从书架上取下尼坎德的《底野加》,在他优雅的六步格中寻找疗法吗?不会,你会叫一个医生来。也没人把维吉尔的《农事诗》当做它声称要充当的种地手册。”
为什么卢克莱修要冒着不被认真对待的危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他的哲学呢?詹金斯认为,关键在于他的学说的本性。“我们从一开始就被教导说,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做两种伟大哲学传统的根源;用柯勒律治的话说,每个人天生要么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要么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是两类人,几乎不可能想象出第三种人。企鹅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一本《遇见真正的自己》中问,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这是误导性的:更合适的图景是拉斐尔壁画《雅典学园》中描绘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肩而立,一起立于古典思想的顶峰。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二人对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方法是有共识的。粗略地说,他们的共识是,你应该从头脑开始,向外拓展,这是西方哲学自那以后的主导思想。但伊壁鸠鲁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念:你应该从外部世界开始。”第一步是理解物理学,研究了物理学之后,你就会明白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不存在别的东西。一旦把握了这一点,道德理论就随之而来:你将意识到死后没有生命,但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要紧;虽然神存在,但他们跟万物一样也是由原子组成的,在世界的创造和管制中不起任何作用;你唯一能够理性地追求的目标是你自己的快感。
原子论是一种特别适合诗歌体裁的哲学,因为它沉浸于我们感知到的物理世界,使卢克莱修能赞美宇宙的宽广和世界奇妙的细节——街上的水坑、远处山上的绵羊、晴天雨棚下水反射的光。
但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伊壁鸠鲁的哲学一定让人觉得是一种毫无诗意的学说。追求快乐,而不是像斯多葛派那样追求美德,应该显得不够高贵,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看上去缺少魔力、神秘性和令人向往的遗世独立精神。卢克莱修把伊壁鸠鲁哲学表述成有诗意的信仰,克服了它的这一缺点。在《物性论》的开头,他用雄壮的语言赞美能量和创造力的象征维纳斯。书中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但卢克莱修的语言却是宗教性的。
 ( 拉斐尔壁画《雅典学园》 )
( 拉斐尔壁画《雅典学园》 )
伊壁鸠鲁的学说是一个完整而融贯的系统,但是它有两个显著缺陷。他对死亡的断言非常有力:我们不仅不该畏惧它,而且它跟我们无关。但如果生活是美好的,死亡是最终的熄灭,那死亡一定是一种伤痛,哪怕你可以平静地面对它。另一个困难之处是利他主义问题。按照伊壁鸠鲁的理论,一个人没有理由考虑他人的快感,应该只管自己的快感,对他人的痛苦不为所动。《物性论》第二卷的开头写道:“当狂风中大海里卷起波浪的时候,自己却从陆地上看别人在远处拼命挣扎,这该是如何的一件乐事;并非因为我们乐于看见别人遭受苦难,引以为幸的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免于受到灾害。”卢克莱修的诗歌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要克服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这两个问题。他在诗中逐步建立起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家庭的一部分的感觉。“我们都源自神圣的种子,都源自同一个父亲,从他那里,大地母亲淋到了甜蜜的湿气。”个人天生地对自己的家人取得的成功和快乐有兴趣、感到高兴,如果能把整个世界想象为一个家庭,就会爱上整个世界,对它的力量和延续感到快乐。个体甚至会对自己的死亡感兴趣,因为伊壁鸠鲁教导说,新事物只能诞生于原子的重新排列,或如卢克莱修所说,一件东西的诞生总是另一件东西的死亡。世界总是新的,所有世俗的事物通过相互交替变化而存在,就像接力赛中的选手,把接力棒交给队友,以便让全队取胜。这个比喻使我们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团队的一部分。我们为世界上的胜利和永远鲜活而感到快乐,但这些快乐需要不断地出生和死亡,包括我们自己的出生和死亡。因此如果你能感到自己是普遍的亲属关系的一部分,就有理由关心身边的人,以及有理由接受自己的消亡。“一个人无法命令他人去怎样感受,于是卢克莱修要哄骗和勾引读者。他的目的是重铸伊壁鸠鲁的哲学,表明可以宗教、诗意地理解它,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一部诗歌体的著作。”
古今原子论
 ( 卢克莱修 )
( 卢克莱修 )
格林布拉特说:“卢克莱修比基督早出生一个世纪,显然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认为虫子自发地产生于潮湿的土壤,地震是风困于地下洞穴的结果,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总体上《物性论》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种惊人的对世界很现代的理解,每一页都表达了一种科学观点——原子在无限的宇宙中随机移动——充满一位诗人对奇迹的感受。”奇迹并不依赖于对来生的梦想,它源于认识到,我们跟星辰和海洋等万物由同样的东西组成。这是他的人生观的基础——不要害怕神,而是要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从这部著作到现代性之间有一条线,虽然不是一条直线。这部诗作遗失了,后来在1417年又找到了。人们禁不住要把这多少世纪之后的失而复得称作奇迹。但这部诗作的作者不相信奇迹,他认为一切都不能违反自然法则,他提出物质的运动是无法预测的,会突然转向。《物性论》被重新发现推动了一次突然转向,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转变的部分特征就是卢克莱修式的对美和享乐的追求,这一追求决定了宫廷的衣着和礼仪、礼拜仪式的语言、日常用品的装饰和设计,它弥漫于达·芬奇的科学和技术探索、伽利略的天文学对话、培根宏大的研究计划和理查德·胡克的神学中。这种否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放弃对天使和魔鬼的关注,转而关注尘世上的事物:开展实验而不必担心侵犯上帝的秘密,质疑权威,挑战既有学说。
当教会在努力查禁《物性论》时,年轻的马基雅维里在抄写这部书,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其居民说,人生全部或大部分幸福依赖于对快乐的追求。随着这首诗的传播,其思想渗透进了流行文化。在1590年伦敦的舞台上,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茂丘西奥对罗密欧说,春梦婆来看望过罗密欧了。“她是精灵们的稳婆,她的身体只有郡吏手指上一颗玛瑙那么大;几匹蚂蚁大小的细马(Atomi,原子)替她拖着车子,越过酣睡的人们的鼻梁。”而且这出戏的主人公并不期盼来生:“我要留在这儿,跟你的侍婢,那些蛆虫们在一起。啊!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初版于1580年的《蒙田随笔》中有近100条直接引用《物性论》,到17世纪,这部诗作的吸引力已经无法抑制。牛顿宣称他是一位原子论者,18世纪的托马斯·杰斐逊有至少5种《物性论》的拉丁语版。后来,古代原子论的直觉被经验观察和实验证实,达尔文可以依据他自己的作品证明他的观点。爱因斯坦给《物性论》的德译本写过序,他写到原子时,他的想法依据的是实验和数学而非古代人的猜测。但爱因斯坦承认,那种猜测引导出了现代原子论所依据的证据。“可以放心地放着古诗不读,它丢失和重新发现的故事渐渐被人遗忘。这都证明卢克莱修的著作已经被吸收进了现代思想。”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写道。■
(文 / 薛巍) 卢克莱修读书柏拉图哲学物性物性论文化伊壁鸠鲁原子论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