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明
作者:薛巍 ( 西塞罗(中)出席元老院会议 )
( 西塞罗(中)出席元老院会议 )
“文明是可耻的”
约翰·阿姆斯特朗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毕业于牛津大学,2001年移居澳大利亚,是墨尔本商学院的驻校哲学家。跟他的好友阿兰·德波顿一样,他一直在努力阐明爱情、美、人生等宏大的概念。近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寻找文明:翻新一个受到玷污的概念》。
阿姆斯特朗说,几年前,盖蒂研究所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一个会议讨论文明,有三位知名学者提交的论文都说,文明不能再被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这并不是一个激进或新鲜的主张,他们只是重申了一个早已有之的正统观念。”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康拉德发表于1899年的短篇小说《黑暗的心》是“对欧洲文明一次尖锐而彻底的批判”。1885年,俾斯麦召集起来的柏林会议宣布,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直接拥有并统治所谓的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通过其代理人所实施的统治是绝对化的和冷酷无情的,手段极其残暴。而这位伪善的国王却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世人相信,他所做的是一件文明教化的工作。故事的讲述人马洛一踏上刚果的土地就发现,实际上的恐怖无情的压迫与他们宣称的慈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比利时大贸易公司一家贸易站的代理库尔兹却一度认为,他的工作让这个国家沐浴在欧洲的文明之光中。
库尔兹是整个欧洲的产物。他父母的国籍是多重的,他是一个高雅艺术爱好者,多少有些天赋,是一个作家、画家、音乐家,他宣称信奉理性的利他主义。但库尔兹孤身一人沿着刚果河逆流而上去搜集象牙,成了当地一个部落的领袖,他的统治非常残暴。他在一篇关于土著人的报告中写了一句:“消灭所有这些畜生!”马洛却把库尔兹视作一位英雄,认为他是在为全人类犯罪——通过退回到野蛮状态,库尔兹触及了人们所能探及的文明构架的底层,触及了人性的最核心,他黑暗的心。马洛认识到文明是欺诈的、可耻的,他同时又热情地投身于文明。“《黑暗的心》是一个奇怪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故事。一方面,它认为文明就其本性而言是极其虚假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文明能够实现它所宣布的目标。”
阿姆斯特朗认为,不能因为文明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关联而抛弃它。伦敦会议上三位学者放弃文明概念的提议,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刻法罗斯的行为类似:刻法罗斯与妻子普洛克里斯相亲相爱,两人心中的爱火同样地热烈。妻子送了他一根标枪。一天清晨,他带着标枪去打猎,听到落叶中发出悉索声,他以为是野兽,就把标枪投去,但原来那是前去寻找他的妻子。“有些人因为没能认清他们爱的东西而毁掉了它。在伦敦那次会议上,我目睹了被掷出的标枪。但它射中了什么?那些学者认为文明这一概念是一种威胁,他们投出了飞镖。但我怀疑丛林中藏着某种珍贵的东西。看得更清楚的话,文明这一概念可能会是某种我们需要、我们珍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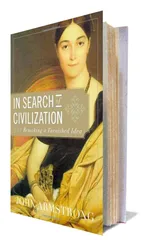 ( 《寻找文明:翻新一个受到玷污的概念》 )
( 《寻找文明:翻新一个受到玷污的概念》 )
普遍化文明中的低级文明
文明跟烹饪、保险、技术、风度、地缘政治、画廊、法律、交谈、考古、个人卫生、城市规划、伦理学、科学、购物、性、诗歌等都有关系。“文明是人类想出的最宏伟、最雄心勃勃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抵达文明的核心,揭示其秘密的含义,我们就能理解我们最深入、最重要的方面以及人类的境况。但什么是文明是一个难题,很难给出一个清晰、有力的答案。所有像公正、爱情或文明这样的概念都包含了多重关联,含义太丰富。”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也说:“文明是一个普遍的、隐蔽的、复杂的事实,一个很难描述、很难叙述的事实。”他概括说:“‘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它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
为了弄清“文明”一词的含义,阿姆斯特朗想象了一场类似于苏格拉底对话的讨论会,4位参与者分别陈述了一种定义。第一个说文明是各种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今天世界上有9种主要的文明,也有很多较小的文明,如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有独特、古老的生活方式。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其公民共有的一套假定、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文明跟整个社会共享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有关。它决定了属于它的人的内心生活的结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对自己人来说,这些方式是自然的、显而易见的,外人则会感到困惑。
第二个人说,文明表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水平,所以我们说最早的沿河的4种文明——尼罗河、恒河、黄河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地方是最早出现充足的经济和成熟的政治,能够开展大型工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驾车行驶到远离文明的、没有加油站的地方,文明就是能够找到加油站的地方。高更说文明是毒药时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现代都市生活持反对意见。
第三个人说文明跟对享乐的追求有关。美食和美酒是文明的胜利。文明跟漂亮的浴室和丰裕的厨房的关系多于它跟博物馆的关系。《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个小人物叫奥勃朗斯基,他点了文学史上最好的一道午餐,他说文明的全部目标是使一切都成为享受之源。
第四个人说,文明需要高水平的智力和艺术才华,文明显示的不是在社会中什么是正常的,它精心挑选出最壮观、最崇高的成就。肯尼斯·克拉克说,有史以来最文明的地方是文艺复兴时期乌尔比诺的宫廷,一群人发展出了相当优雅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文明在衰落,不是担心人们得不到洗碗机或医院的床位,而是担心文化最秀美的花朵太纤弱、太精致,以致存活不了。
阿姆斯特朗偏向于文明的最后一种定义,文明的英雄是那些教我们如何既致力于高贵的价值又接受世界的方式的人。比如古罗马的演说家、公职人员和哲学家西塞罗,他既欣赏古希腊的教化,又尊重古罗马人强劲的军事和行政能力。要做文明人,就要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需要我们关心目标而非手段。他说,手机也许能让我们更频繁地通讯,拍更多的照片,找到餐馆,但这些资源不会自动地帮我们达到它们应该达到的目标——有意义的谈话,密切的关系,愉快的夜晚和对美的欣赏。
阿姆斯特朗说,一个真正文明的世界应该是致力于真、善、美的世界。但多元主义者如以赛亚·伯林已经指出,文明推崇的各种价值之间也是相互冲突的。阿姆斯特朗也注意到,良好的社会达到物质上的繁荣之后,必须相应地在精神上也很繁荣才算得上是文明社会。但社会总是做不到物质与精神上的平衡,总是会偏向一方。不是偏向野蛮的深渊,便是偏向颓废的泥沼,如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中的一个贵族家庭。另外,我们都会有一种悲剧性的感觉:人生建立在并非所有的好东西都兼容这一事实之上。不可能既有幸福的婚姻又能风流韵事不断,既有收入丰厚的工作又能随意度假,或者不能住在你最想住的地方;责任艰巨而令人感到厌烦,但尽责又很重要。面对这种内在的冲突和人生的沉浮,文明应该帮助我们面对不可避免的失望和不幸,主要是通过注入斯多葛派的美德:延迟享乐的能力,做自己不愿做但又应该做的事情,忍受烦恼,不做无谓的指责。
在该书最后,阿姆斯特朗说商业应该做的是“欲望领袖”,广告业传递的信息是:你知道什么会让我们快乐,我们听你的。而英国评论家弗·雷·列维斯80年前就提醒人们警惕腐朽文明中广告的削弱力量。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一文中说:“我并不轻视消费文化,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得益于这种文化。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发展也有它的反面,这种唯一的世界文明对创造过去的伟大文明的文化基础具有腐蚀或破坏作用。除了令人感到不安的其他后果,这种威胁也表现在低级文明的传播。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同样的低级电影,同样的吃角子老虎,同样的塑料或铝制的怪物,同样的通过宣传对语言的扭曲等等。发生的一切像是当人类在整体上进入一种最初的消费文化时,仍然在整体上停留在一种亚文化水平。世界性和没有个性特征的消费文化的胜利,可能意味着创造性文化的结束。”■
(文 / 薛巍) 寻找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