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究竟在哪里
作者:苗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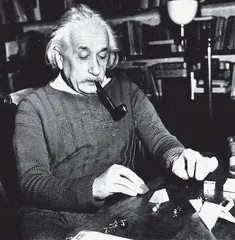 ( 爱因斯坦 )
( 爱因斯坦 )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里,有一天爱因斯坦在散步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转向和他一起散步的派斯(A.Pais)教授,问他是否相信,只有当人们在看月亮时,月亮才是存在的。
爱因斯坦作为一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大多数实验都是在思想中进行的。他从少年时就开始思考:一个人如果以光速前进,他会看到什么景象。这个问题最后衍生成为狭义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后来在一次爬山时,他问他的同伴,如果从悬崖上跳下去会是什么感觉?实际上他当时是在做另外一个思想实验,对于这个实验的深入思考后来使他得到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重力场与加速系的等效原理。抬头看一眼月亮也许可以算是爱因斯坦设计的另外一个思想实验,这是关于爱因斯坦终生都不能理解、也不相信的关于量子力学的论题,因为他相信月亮始终都在那里,这与概率无关。
“量子力学就是魔术。”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er)做出过这样的描述;被看做是量子力学领军人物的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也曾经说过:“如果谁没被量子力学搞得头晕,那他就一定是不理解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中最违反人们常识的地方就在于它突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实在性(Reality)与定域性(Locality),它用概率来描述世界:每一个粒子都具有一个波函数,至于粒子最终出现在哪里,具有什么性质则成为一个概率问题。每一次观测都造成波函数的塌缩,根据量子力学的描述,观测不仅影响了被测对象,而且创造了它:正是由于观测造成的波函数的塌缩,才使粒子具有了确定的观测量。
爱因斯坦不喜欢这种描述,他认为用概率来解释世界是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体现;他认为无论是否观测,物体都应该具有实在性,月亮应该一直挂在天上。为了表达这个观点,他还说过一句流传更广的名言:“上帝不是在掷骰子。”爱因斯坦也许无意表达他可能比别人更理解“上帝”,但这句话体现了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实在性与定域性的信心和他的物理直觉。
爱因斯坦是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形象已经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但是他对于物理学的困惑可能比发现更多。他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粒子物理学家的派斯教授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爱因斯坦,那就是“孤独”,而当爱因斯坦在面对量子力学时,这种孤独感则更加明显。爱因斯坦一生中大多数观点经常与主流相反,但大多并不消极。他认为量子力学很成功,但是不完整,正是他这种始终怀疑的态度促使量子力学不断地自我完善。从1926年开始直到去世,爱因斯坦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对量子力学持怀疑态度的人。爱因斯坦并非一开始就站在了量子力学的对立面,恰恰相反,他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三个创始人之一(他本人正是因为对于光电效应的研究,提出光量子假设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甚至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分支——波动力学的“教父”。但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量子力学“革命”,和相对论一样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电子不再有确切的轨道,一切都被波函数所替代,因此玻尔迅速转向了“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对于这个转向,另一个阵营中的爱因斯坦、薛定谔和德布罗意显然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非决定论”违反了实在性和光速是宇宙中最快速度的基本物理定律,这是量子力学自身的不完备性造成的。量子力学阵营显然不这样认为,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认为量子力学本身是完备的,它描述的就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实在性和定域性是不存在的物理性质,研究它们“就像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这样古老的问题一样”毫无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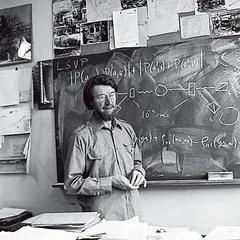 ( 约翰·贝尔 )
( 约翰·贝尔 )
为此,爱因斯坦与普林斯顿的同事波多斯基(B.Podolsky)和罗森(N.Rosen),在1935年写了一篇至今仍然在被不停引用的文章:《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是否是完备的?》(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他对于物理学的认识:他认为一个完备的物理理论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物理实在的每一个要素都应该在这个理论中有所对应物理量;第二是如果能以任何方式不干扰系统而能准确地预言一个系统物理量的数值,那么就意味着存在一个与此物理量所对应的实在要素。这正是实在性和定域性的体现。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情况:一开始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A和B,彼此在时空中分开之后不再相互作用,因此对于A的测量不可能对于B有即时的影响(宇宙中最快的速度为光速,信息传播也不可能快于光速),因此A的性质是实在的。这个情况以文章的三个作者名字的首字母命名为“EPR悖论”(EPR Paradox)。爱因斯坦之后在给玻恩(M.Born)的信中也写道:“很难把量子理论的描述当做对于物理实在的完整描述,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量子理论,他就必须承认对A的测量会对B的物理实在产生影响,我对于物理的直觉使我反对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这里反对的,是量子力学中描述的超距作用,也就是其非定域性。而两个粒子之间这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之后被薛定谔首次命名为“纠缠态”(Entanglement)。薛定谔也强调了用概率来描述微观粒子可能给宏观状态带来的问题:一个粒子是否衰变,在量子力学中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是衰变与否却可以决定一只猫的死活。在此处薛定谔把微观现象(粒子衰变)与宏观现象(猫的死活)联系在一起以显示概率描述的荒谬,当然这就是至今让人迷惑的“薛定谔的猫”,以至于霍金教授说:“我一听到‘薛定谔的猫’,我就去拿我的枪。”
尽管量子力学不断得到实验观测的证实,但是爱因斯坦的“EPR悖论”却一直困扰着量子力学,直到下一代的物理学家登场,才使这个科学史上最持久、也最有名的争论告一段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Bell)因此在科学史上留名,他提出的“贝尔不等式”被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尽管实验结果与贝尔教授最开始的预测恰恰相反。
贝尔一直是爱因斯坦坚定的支持者,他坚信物理的实在性与定域性。玻尔说,“任何一种基本量子现象只有在其被记录之后才是一种现象”,贝尔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说:“难道亿万年来,宇宙函数一直在等一个单细胞生物的出现,然后才塌缩?还是它得多等一会儿,直到出现一个有资格的、有博士学位的观测者?”他认为,量子力学中神秘的超距作用是因为尚未被理解的“隐变量”(Hiden Viriables)决定的。他为此提出了一个不等式,他认为对粒子的观测必定遵守此不等式,以此可以证明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不等式并非是一个思想实验,它是可以真正被实验证实的。一系列的漂亮的实验证实,“贝尔不等式”被突破了,这说明量子力学的描述是正确的,事实驳倒了爱因斯坦和贝尔。
贝尔实验的结果使人们明白,要么这个世界是非定域性的——这违反了相对论,说明相对论只是描述性的理论而非一个基本理论;要么客观实在是不存在的——这更像是“唯我论”的一种表述,“只有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卡尔·波普尔曾经尖锐地写道:“只要想起在广岛和长崎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原子弹爆炸),任何基于量子力学的对于真实性的质疑都应该保持缄默。”相对于“唯我论”,人们显然更容易接受对世界非定域性的描述,就连爱因斯坦的支持者贝尔也是如此。
世界是否真的像玻尔描述的一样,只能用概率来描述,由观测行为来决定被观测量?虽然突破“贝尔不等式”只是量子纠缠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大多数科学家都已经对于量子力学的描述深信不疑,基于量子纠缠态所做的研究比如量子计算机、量子密码学都是现在热门的研究课题。不过,是否存在非定域性的隐变量,上帝到底玩不玩骰子?月亮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只有人们在看它的时候它才存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宏观问题,始终驱动人们寻找对于自然界更深入的理解。■(文 / 苗千) 科学科普物理量子力学哪里爱因斯坦月亮究竟